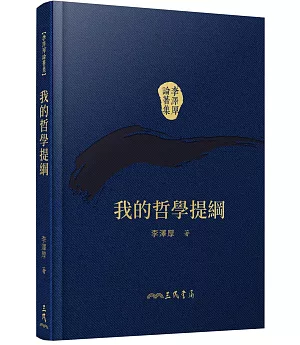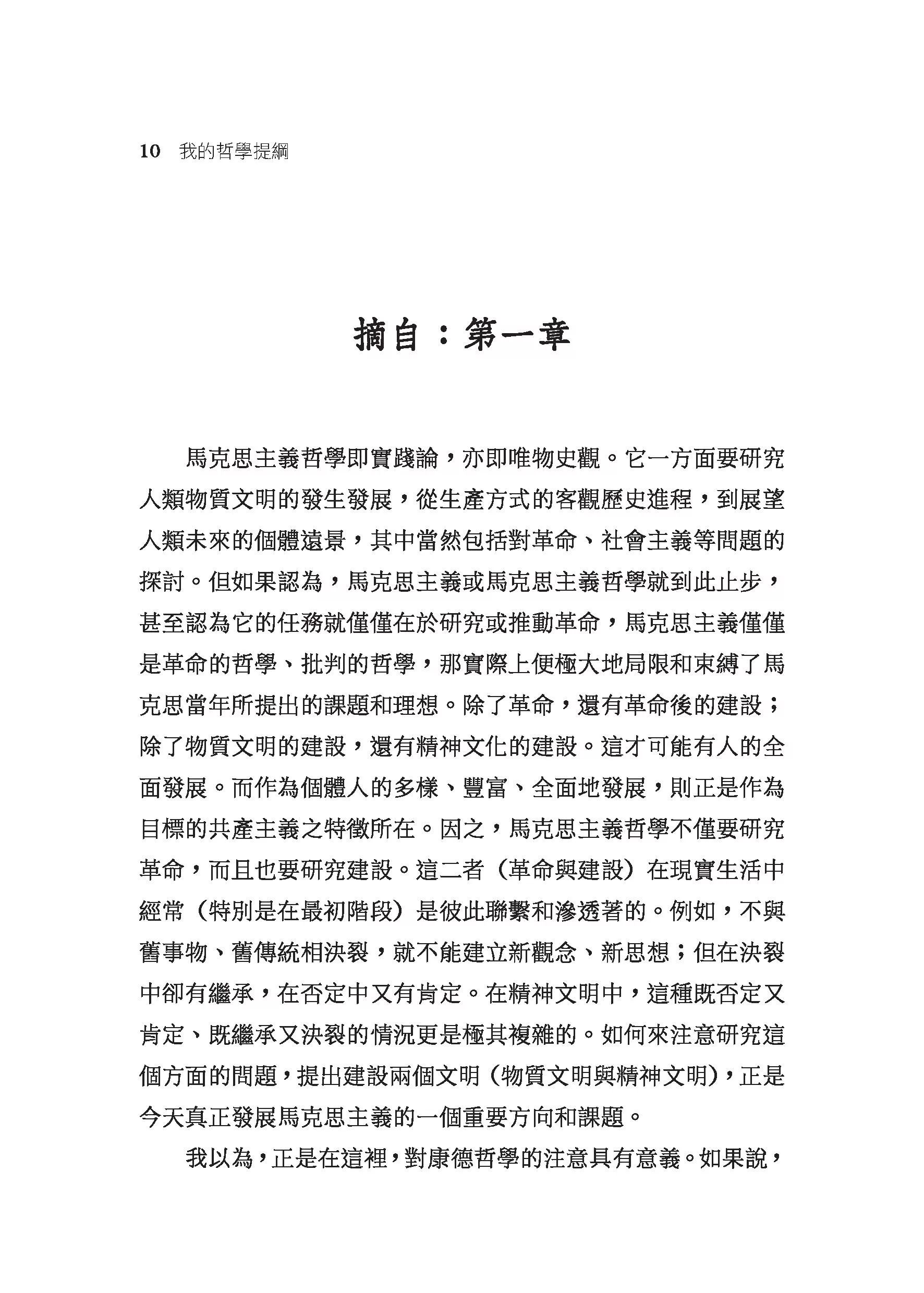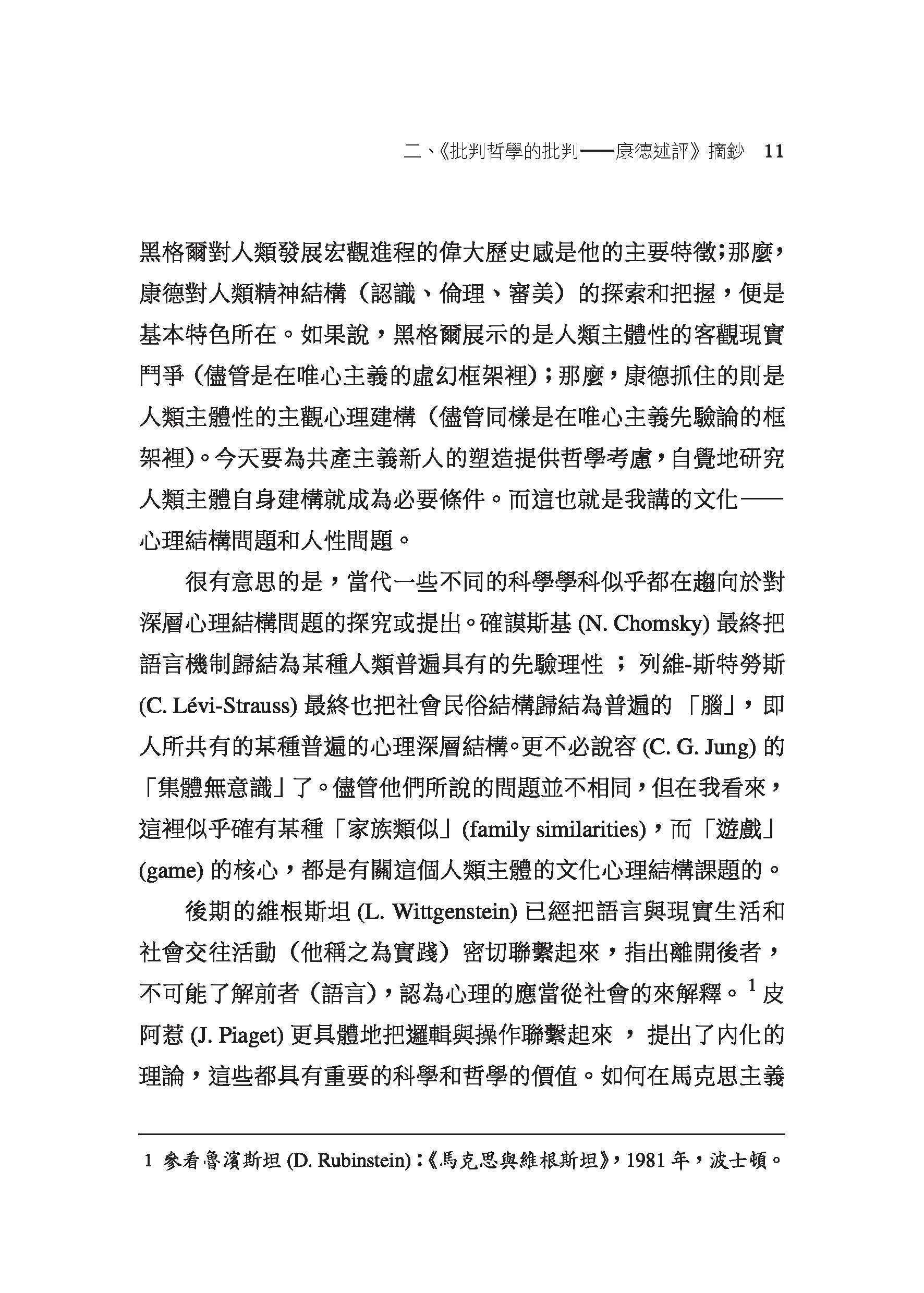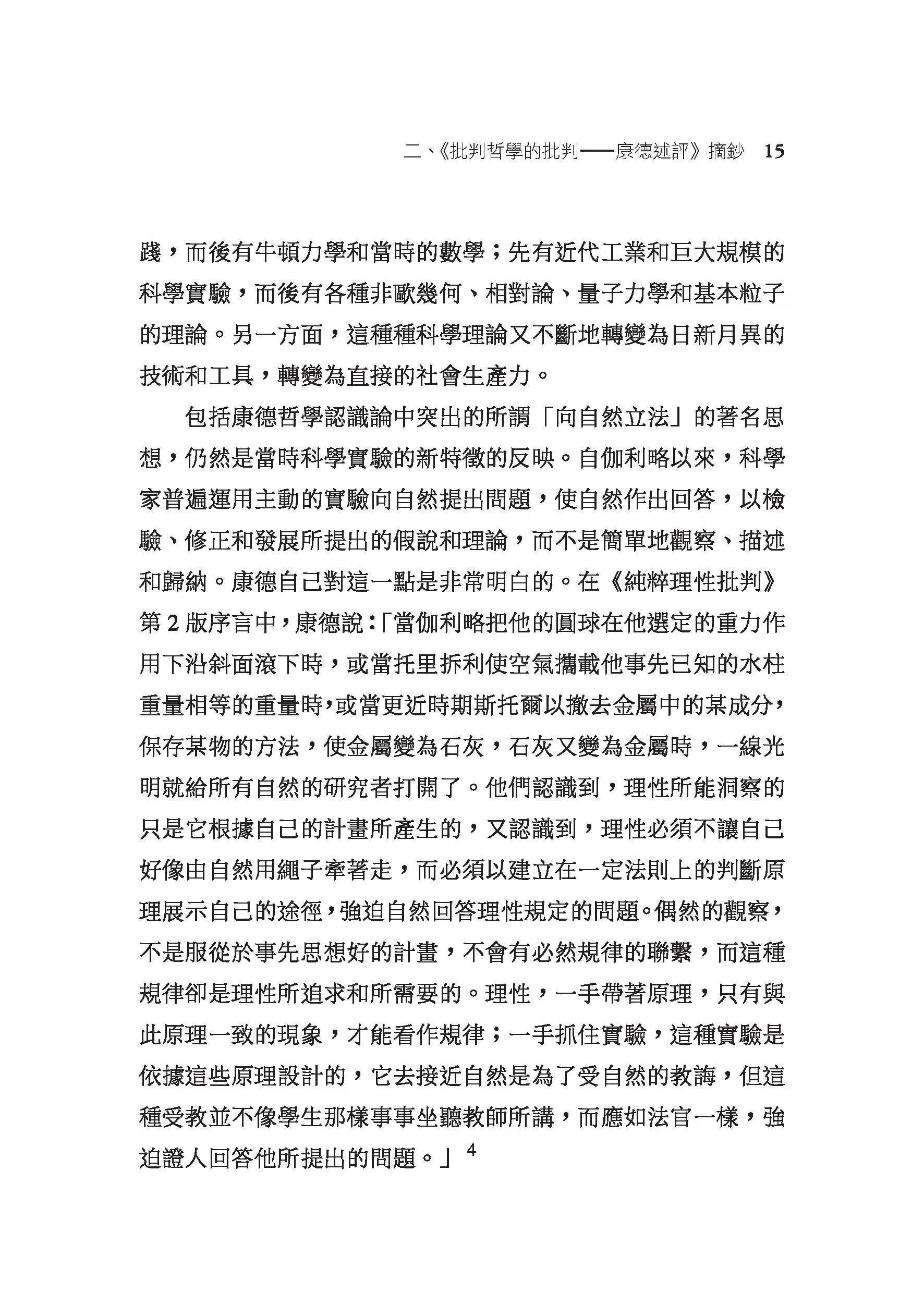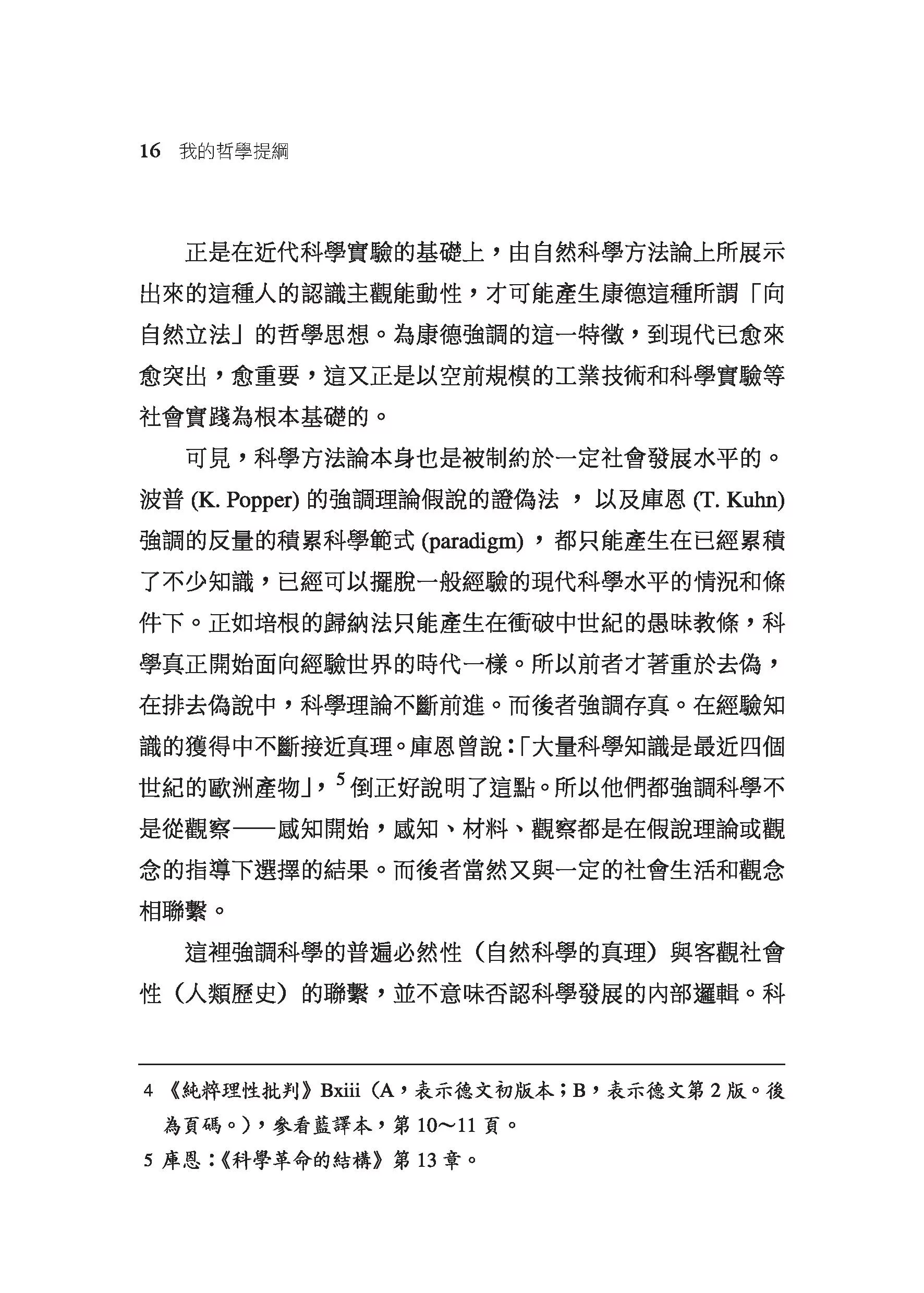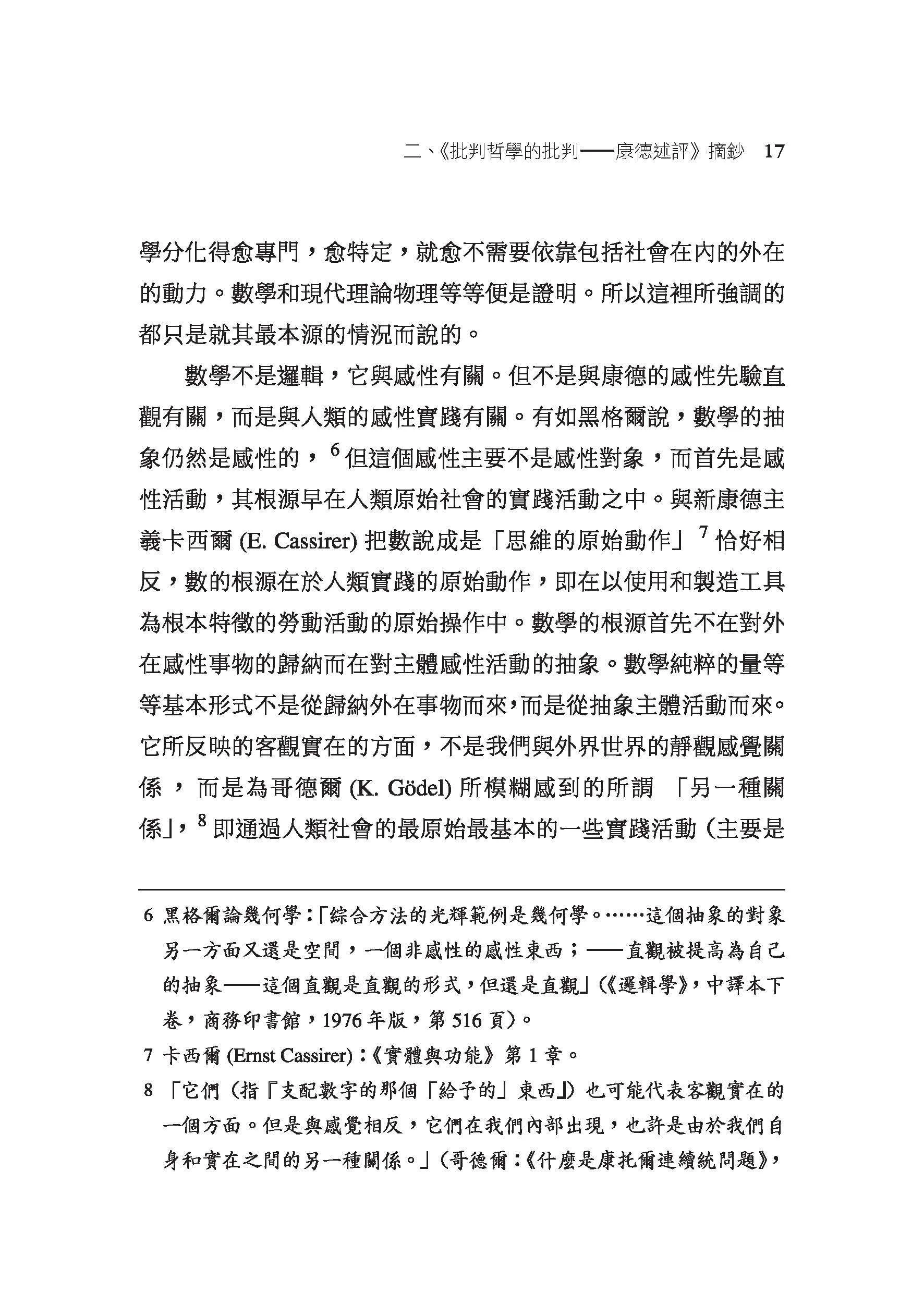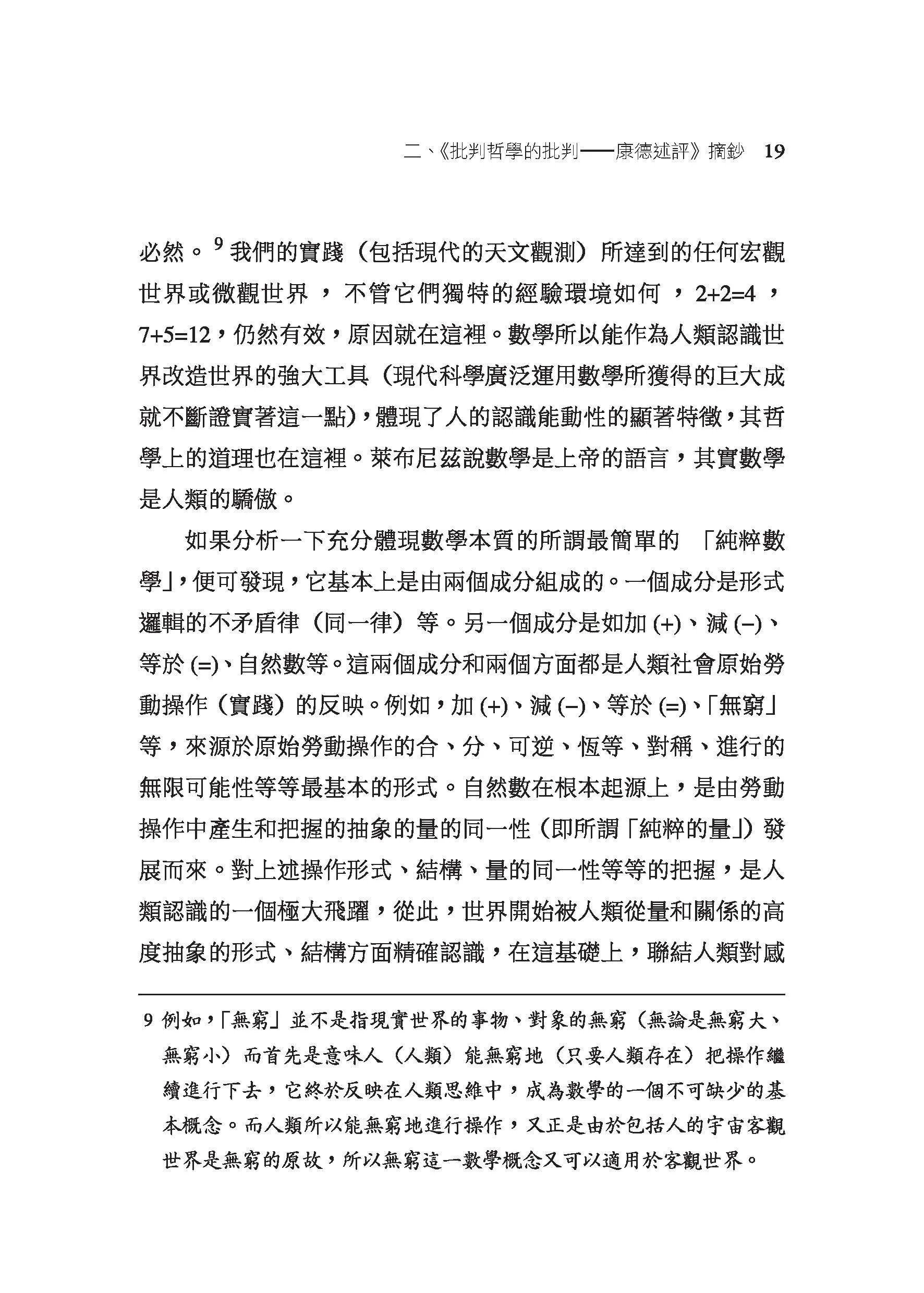序
哲學部分收《批判哲學的批判》(初版於1979年,下簡稱《批判》)、《我的哲學提綱》(初版於1990年,下簡稱《提綱》)兩書。關於康德,兩書中有某些重複的部分。
較之他卷,本卷篇幅最小。特別是那些「提綱」,加起來字數可能才抵得上他卷的一篇長文章。但是,恰恰是這些提綱以及《批判》一書各章的最後評議部分(即收入《提綱》一書中的),卻是我全部著作中最為重要的方面。也許,自己是哲學系出身,仍然更重視別人和自己的哲學思想。
說來也有意思,我從小雖對人生即有某種可笑的感傷和疑問情緒(見《走我自己的路》),但讀人文書刊的興趣卻大抵限於歷史與文學。從孔孟經書到宋明語錄,從墨學到名家,我始終是望而生畏,卻步不前,不敢多所問津的。我當年之所以以第一志願報考大學哲學系,除了想繼續思考一些人生問題之外,主要是受了時代的影響。
一九四○年代後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嚴格被禁的白色恐怖下,對我反而更有吸引力。當時傾心革命,想窮究原理,於是由毛澤東而馬克思,由馬克思而黑格爾,而希臘,而其他。也記得五○年代初在北大讀書時,我曾鄙夷名重一時的蘇聯著作及哲學專家,卻潛心於西哲原典,因而大遭歧視之情景似猶如昨日事。當時閉關自大的國策使現代西方著作極少進口,自己的探索歷程止步在、也流連忘返在康德哲學之中。
事有湊巧,恰好碰上「文革」,於是有論述康德的《批判》一書的寫作,詳情見該書的兩個後記。
此書出版之後很受歡迎,似有洛城紙貴之勢,初版就印了三萬冊,很快賣光。當時的年輕人至今還對我說,他們知道什麼是哲學,是自讀這本書始。說法似頗誇張,查來倒也平實。只要稍事翻閱1949年以來大陸出版的所謂哲學和哲學史著作,便可知曉。哲學在那裡不是「愛智」而是「毀智」,不是「聞道」而是「罵道」(罵人之道),也就是嚇人、打人的理論—政治棍棒。唯心唯物是欽定標簽,辯證法成了變戲法。毛澤東提倡普及哲學,於是「賣西瓜的哲學」「打乒乓球的哲學」,風行不絕。這不是笑談,而是有白紙黑字為證的「哲學論著」,真是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於是《批判》一書,從內容到形式,從觀念到結構,不但大有異於常規,而且還有「離經叛道」之走勢,從而也就被人(主要是青年一代)刮目相看了。其實,此書寫於「文化大革命」之中,交稿於1976年,當時雖心懷異數,卻不能大事聲張,只字裡行間略顯消息;而章章節節均大引馬列,以為護符。今日看來,必覺奇怪;但於當時,乃理所當然。此次重印,我不想多作改動;存其舊貌,以見因緣,為上上好。
同時,事情還有另一方面。即我通過《批判》所表達的自己的哲學觀念,以及後來概括、發展為《提綱》中的基本想法,都自以為至今尚不過時。其中如《第四提綱》、《哲學探尋錄》雖很簡略,卻自以為重要。我以為,本世紀不管是歐陸或英美,不管是世紀前期或世紀末,大都是語言哲學的天下。維特根斯坦無論矣,海德格爾、伽德默、德里達等人也無不以語言為指歸。更不用說分析哲學這種技術學了。這個世紀是科學技術空前發展的時代,語言之占有哲學中心地位也,固宜。但下個世紀呢?我以為是該走出語言的時候了,語言並非人生—生活之根本或家園。
我在《批判》《提綱》兩書中提出了工具本體與心理本體,特別是所謂「情本體」,以為後現代將主要是文化—心理問題。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經濟乃社會存在、發展的動力這一基本原理仍然正確,但隨著自由時間的增大,物質生產之受制約於精神生產也愈趨明確。從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理論便太簡單了。社會心理、精神意識從來就有其相對獨立性質,在今日特別是在未來世界,它們將躍居人類本體之首位。這即是說,工藝(科技)社會結構的工具本體雖然從人類歷史長河上產生和決定了人們的文化—心理結構,但以此為歷史背景的後者,卻將日益取代前者,而成為人類發展和關注的中心。這就是我所認為的:「歷史終結日,教育開始時」。教育不再是成為其他事務(如培育資本社會所需要各種專家,培育封建社會所需的士大夫),而將以自身亦即以塑造人性本身、以充分實現個體潛能和身心健康本身為目標、為鵠的,並由之而規範、而制約、而主宰工藝(科技)—社會結構和工具本體。這樣,自啟蒙時代起到馬克思主義止的理性主義的基本線索,亦即作為今日資本世界最高準則的科學主義、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等等,便將規範在一定限度內而不再任其無限膨脹,從而也避免激起其反面之非理性主義、神祕主義、縱慾主義等等的惡性回應。這就是我結合中國傳統所提出的「新的內聖外王之道」,也就是我所謂「經過馬克思而超越馬克思」的「西體中用」的「後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因此,如果今日有人硬要問我,你是否仍為馬克思主義者?其答覆自然是肯定的。我在青年時代白色恐怖中經過思考接受的東西,大概這一輩子也不會丟掉;但在壯年時代的紅色恐怖下,也是經過思考,被接受了的東西又有了長足的變化、修正和發展,這也大概是確定無疑的了。其實,馬克思主義早已多元化,多種多樣,各異其趣。我的馬克思主義在於仍然肯定製造、使用工具為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這一唯物史觀的根本觀點;而我所強調的「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的未來卻指向心理和情感,這是以前或其他的馬克思主義所未曾談到或未曾強調的,此之謂「後」或「新」。這裡也還想說一下,一提馬克思主義,我便被扣上「歷史必然論」「經濟決定論」的帽子。我明明強調的是個體、感性與偶然,卻硬說我是「死守」著集體、理性和必然。的確,我是講了必然。什麼是必然?人要活,人要吃飯,這就是必然。從而追求物質生活(衣、食、住、行及壽命)的改善和延伸,從而社會在物質生產上(以製造、使用工具為標誌)取得進展,這就是必然。這是人類生活的基礎。當然,歷史也有倒退甚至毀滅的時期,但從人類總體千萬年歷史看,這方面是向前發展、進步的。我就是在這意義上講必然、理性和集體,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完全否認這一點,認為人吃飯(從而社會物質生產)不重要,不是「必然」;認為今天和千百年前一樣,物質生活(衣、食、住、行及壽命)並無進步或這種進步沒有意義;認為社會歷史無理性可言,個人的當下「存在」、感性情欲才是「真實」;如此等等,我是明確不贊同的。至於在社會物質生產、生活中,在各種歷史事件、政治體制、精神生活、意識形態、文學藝術以及個人生存中,都具有極大的多樣性、偶然性、不可規定性等等,則正是我所反覆強調的。
所有這些看法和想法雖均略見於《批判》和《提綱》,但遠未充分展開。因此,這篇序文也就以提示這些尚待繼續探究的哲學課題作為結尾吧。
李澤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