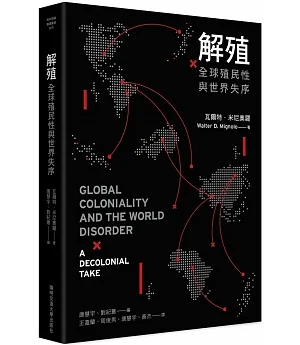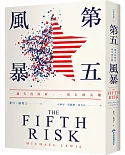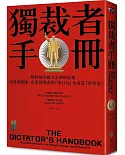推薦序
陳春燕(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台灣學界曾熱切追過一波的後殖民研究,係八○年代晚期至九○年代建制化於美國學院的版本,以殖民論述分析、後結構主義派理論化工作為主軸;稍後,若干學者關注觸角擴至第三世界的解殖哲學、從屬階級研究(subaltern studies)及馬克思派文化理論。這些研究支線的考察對象以大英帝國為主,兼及法語語系地區——換言之,其檢視的歷史區段基本上自18世紀起跳。
米尼奧羅(Walter D. Mignolo)代表的是國內人文領域甚少留意的來自拉丁美洲的聲音,而他的貢獻之一正在於堅持創發屬於拉美的殖民與解殖研究:這對他而言,不僅包括更適切地擺放拉美在世界殖民圖誌的時空座標,亦表示他總是自覺地在著述中提倡(各個時期)中南美洲思想家的能見度,做導介與延伸。
1995年出版的《文藝復興的隱暗面:識字教育、地域性與殖民化》(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 Literacy, Territoriality, and
Colonization),可謂米尼奧羅的成名之作。此時,雖然也有其他學者翻新對於歐洲現代性的理解,將其時間軸線提前至15世紀末的發現新世界,米尼奧羅在書中以更有效的方式整合表述,融會歷史語言學(philology)與文化人類學方法,提出認識論批判。他放棄一般的線性脈絡,改以雙面性架構陳述拉丁美洲如何是西班牙文藝復興乃至於歐洲現代性的關鍵現場,以「文藝復興/文藝復興之隱暗面」、「早期現代/殖民時期」、「啟蒙時期/啟蒙時期之隱暗面」、「現代/殖民時期」等組別,梳理出幾大文化事件。所謂的現代性,其內容即一套由科學論述與哲學思辨所領頭的知識系統,意即形式上自我打造為現代思維的知識產製過程:此時,法、英、德文強勢突出己身理性質地,成為現代性順理成章的代言人;而被視為較適合文化、文學軟調表達的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相對而言便在歐洲內部遭到邊緣化,其生命力必須到海外續延。而稍早在15、16世紀之交,歐洲各地出現了對於語言統一的渴望,幾部西班牙語(Castilian)文法及語言哲學書的出版,鞏固了西語的正當性;隨後,此一效應並擴大成為對於字母式語言的肯定,而當擴張中的帝國在遠方遭逢陌生的語言系統,對於拼寫式語言的認定即成為海外語言傳教(及其隱含的人本主義教育)的理論根基。
現代性與殖民性的斜槓組構,到了他下一本代表作《地方歷史/全球設計:殖民性、底層知識與邊界思考》(Local Histories / Global Designs: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Border Thinking,
2000)會得到更多的驗證。米尼奧羅會指出,假使拉丁美洲的獨立建國多半發生於19世紀初期,這正表示當時的論辯所成就的乃是現代思維,而非殖民思維;這也是他所看見的拉美模式與其他帝國模式(例如後殖民研究中著名的「混種」之說)不同之處。
及至後來幾部專書,《建構拉丁美洲》(The Idea of Latin America, 2005)、《西方現代性的隱暗面:全球性的未來,解殖的選項》(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Futures, Decolonial Options,
2011),米尼奧羅會回應其時已百花齊放的幾大後殖民、解殖、帝國批判論述,並大膽主張,若沒有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就沒有東方主義(Orientalism)——若沒有拉丁美洲在15、16世紀協助形構出歐洲的自我想像,後來也不會出現歐洲對於東方他者的論述建造工程。此外,他並不以為「他者」是描述殖民地的唯一意象:拉丁美洲便不能算是歐洲的他者,而是歐洲範圍極端放大之後的新邊界,是同一之中的差異。
米尼奧羅從不諱言,他如何受到出身拉美世界的思想家的啟發,尤其是杜塞爾(Enrique Dussel)對歐洲現代性必須納入拉丁美洲的主張,以及基哈諾(Anibal Quijano)所提出的「權力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事實是,他總在著述中積極回應這些前行者的說法,試圖匯聚出具備拉美歷史體質的在地化理論。
後殖民研究因為大量地彼此重複,以致一些關鍵詞——例如「跨界」、「差異」——早已出現彈性疲乏態勢。米尼奧羅也提出過「殖民差異」(colonial difference)、「邊界思考」(border
thinking)等看來大同小異的詞語,不過當時這些概念並非為理論而理論的設計。「邊界思考」立基於他對歐洲現代性、拉丁美洲歷史的解讀,是他觀察拉美如何在歐洲內部、外部製造了錯綜的中心-邊緣關係而得,並非一般跨界說的「身處兩個世界」修辭可以替換——這些論法裡的「世界」往往只是不證自明的虛構文化框架,而所謂的「身處」多半僅止於個人情感訴求,但米尼奧羅所重視的是不同知識系統交會之下所模造出的思維結構,沒有「知識主體」(knower)與「知識客體」(the
known)之間的區別,邊界兩端對於邊界之描述都來自於自己的外部。「殖民差異」之說同樣根源於歷史思考,用以說明權力殖民性的行使以及從屬族群之抵抗實踐如何都在「差異性」此一場域發生。不僅如此,他的歷史判讀也讓他相信,殖民差異直至今日仍以不同變體繼續繁衍,權力也持續以認識論與文化符號機制施行其影響力——也因此,更新的邊界思考刻不容緩。
回到此時此刻的台灣。殖民命題在二○○○年代初期於社會學科被併入全球化現象論辯,議題性很快被資本主義問題所取代;於人文領域則被稀釋為關於時序斷代的指涉意或淪為文學文本分析的關鍵詞詞庫,已失去創新量能。近幾年,或因南向政策效應,或因文化與高教政策的資源換手,關於殖民題材的興趣在文化研究乃至藝術實踐皆有復興的跡象,目光則多聚定於東南亞或台灣內部。然而新世代論者是否多以當前現實裡的「弱勢」、「受壓迫者」為絕對符碼,用意在於肯定式描述,而非批判意識的鋪陳、測試(對於壓迫者提出常理式的控訴,並非此處意指的「批判」),且回看的歷史軌跡又是否僅限於狹義的殖民暴力,都還有待觀察。確實,若閱讀米尼奧羅可以學習他挖掘自本土的思想原創以及對於殖民特殊性的強調,我們便未必會在屬於台灣的物質及知識條件下導出與他同步的結論,未必需要挪借他所提示的立論路徑——他的確不認為亞洲、非洲的解殖選項與拉丁美洲一致。只不過,身為讀者,眼見現下文化、藝術評述中蔚為主流的以受壓迫者生活經驗、感受為首要參考值的論法,確有理由懷念殖民研究開拓者——例如米尼奧羅——所示範的觀念建構方法學與宏觀省思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