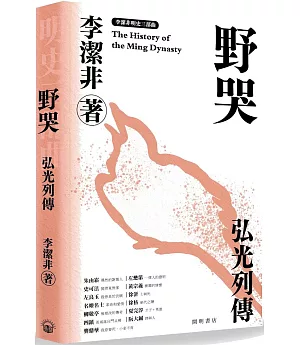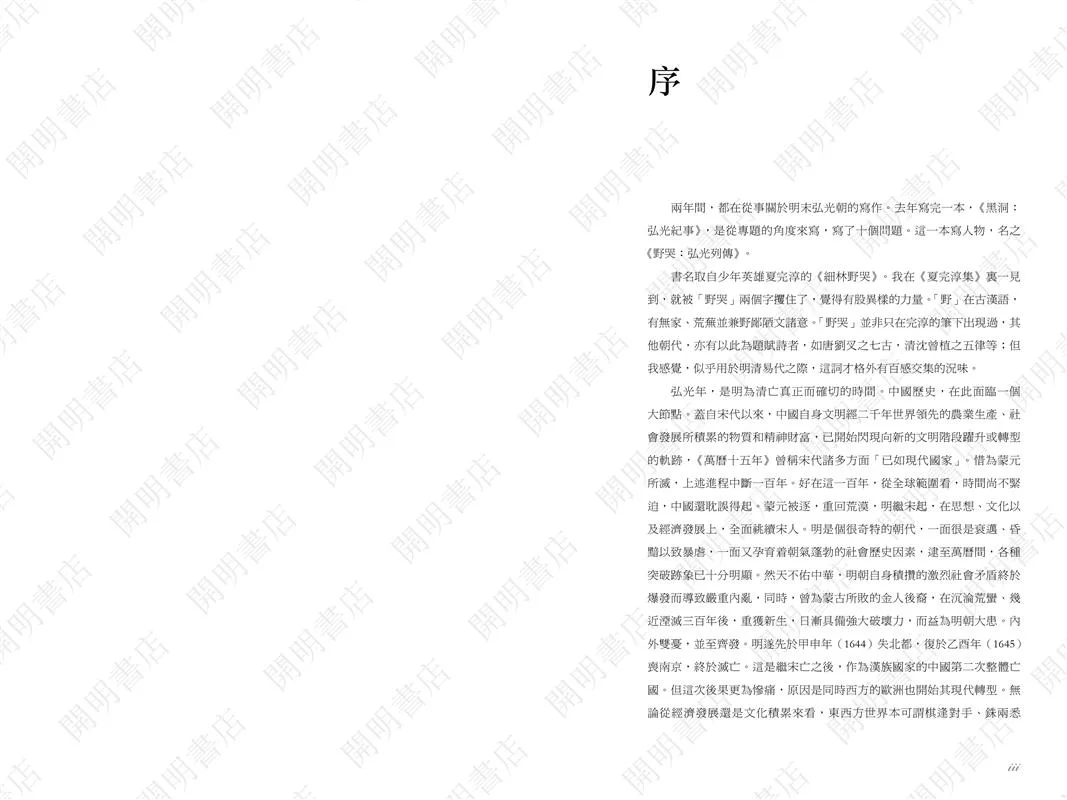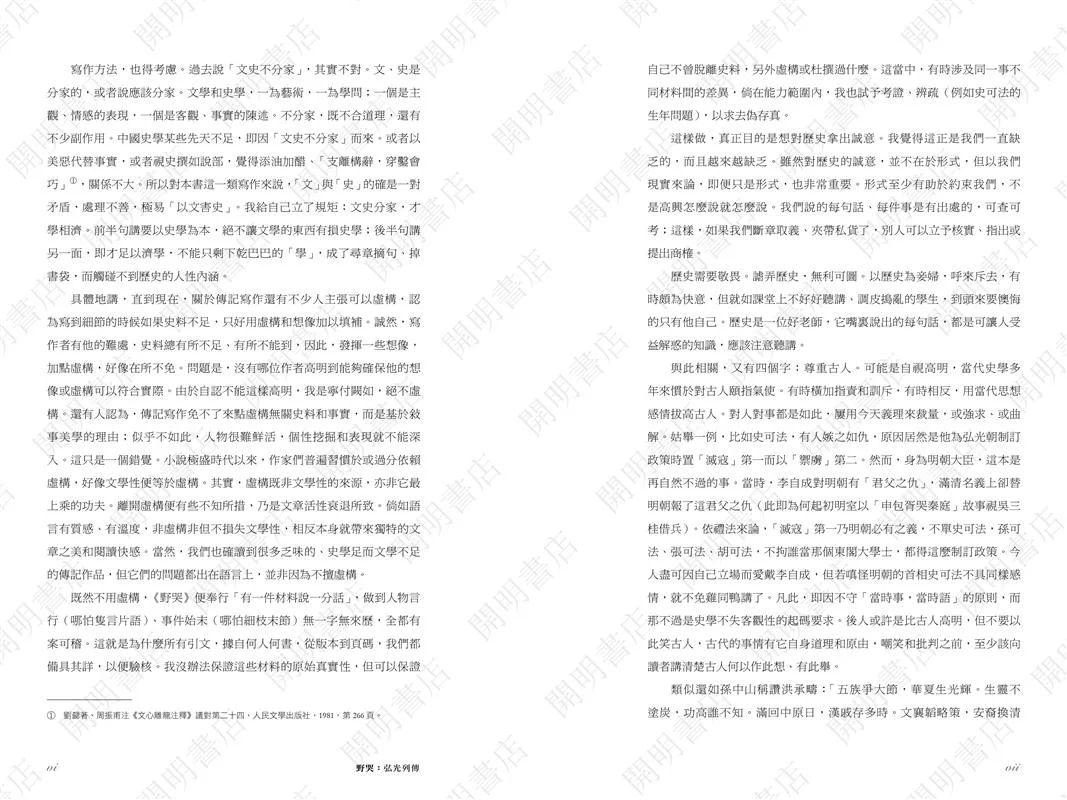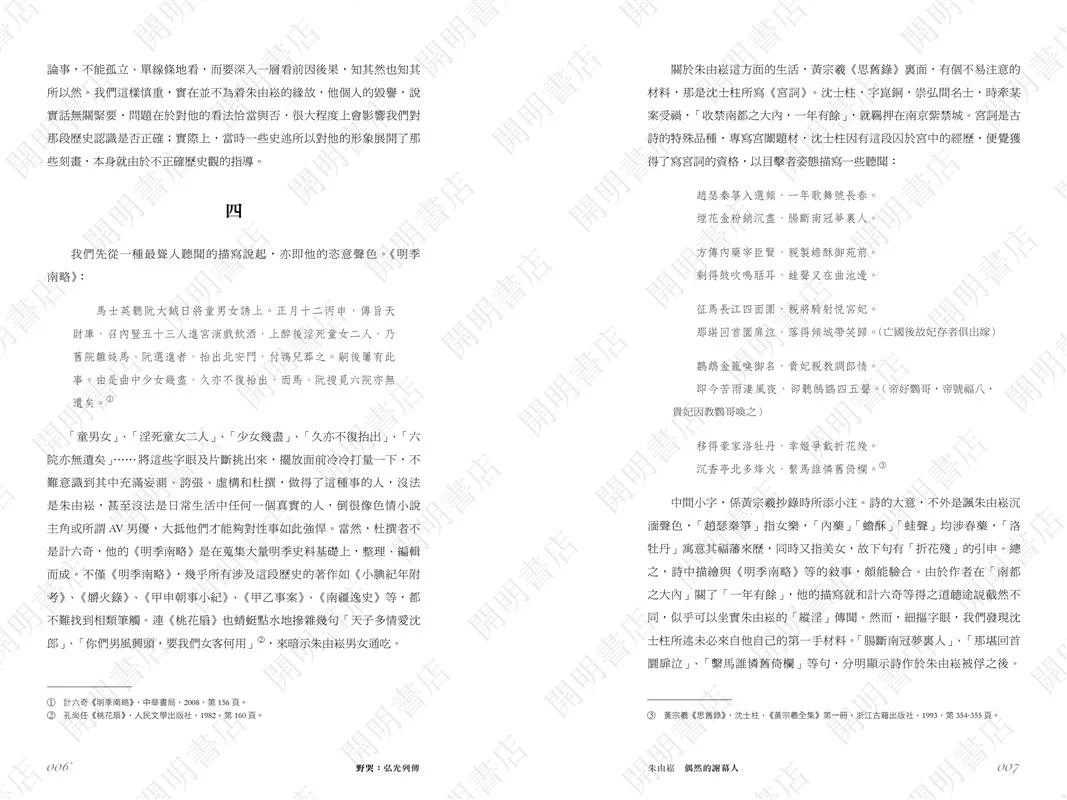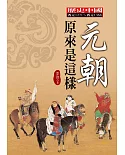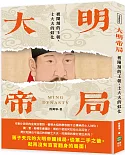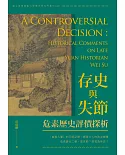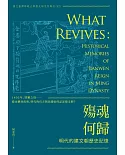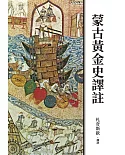內容簡介
本書借十餘位在不同側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來呈現弘光朝那一段歷史。被安排於書中露面的,有朱明王朝確切的末代皇帝朱由崧,有弘光樞臣和關鍵人物史可法,有稱為“明代蘇武”的左懋第,有以兵變致南明解體的左良玉,有普遍目為南京禍根的阮大鋮,有秦淮河畔苦悶的青春叛逆群體,有時代思想高度的體現者黃宗羲,有以十七齡慷慨赴死的少年天才夏完淳,有傳奇說書家柳敬亭,有“遺民現象”的典型徐枋,有入清後的“貳臣”龔鼎孳……他們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學生、妓女、藝人、學者、隱士、起義者,還算廣泛,覆蓋了社會多個層面。
目錄
序
朱由崧 偶然的謝幕人
左懋第 一個人的證明
史可法 拋骨竟無家
四鎮 孤城落日鬥兵稀
名姬名士 革命和愛情
黃宗羲 裸葬的情懷
阮大鋮 詩與人
夏完淳 才子+英雄
柳敬亭 被刪改的傳奇
龔鼎孳 我原要死,小妾不肯
徐汧 士與死
左良玉 殺掠甚於流賊
徐枋 絕代之隱
附 辛巳、壬午開封之圍
後記
朱由崧 偶然的謝幕人
左懋第 一個人的證明
史可法 拋骨竟無家
四鎮 孤城落日鬥兵稀
名姬名士 革命和愛情
黃宗羲 裸葬的情懷
阮大鋮 詩與人
夏完淳 才子+英雄
柳敬亭 被刪改的傳奇
龔鼎孳 我原要死,小妾不肯
徐汧 士與死
左良玉 殺掠甚於流賊
徐枋 絕代之隱
附 辛巳、壬午開封之圍
後記
序
序
兩年間,都在從事關於明末弘光朝的寫作。去年寫完一本,《黑洞:弘光紀事》,是從專題的角度來寫,寫了十個問題。這一本寫人物,名之《野哭:弘光列傳》。
書名取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細林野哭》。我在《夏完淳集》裏一見到,就被「野哭」兩個字攫住了,覺得有股異樣的力量。「野」在古漢語,有無家、荒蕪並兼野鄙陋文諸意。「野哭」並非只在完淳的筆下出現過,其他朝代,亦有以此為題賦詩者,如唐劉叉之七古,清沈曾植之五律等;但我感覺,似乎用於明清易代之際,這詞才格外有百感交集的況味。
弘光年,是明為清亡真正而確切的時間。中國歷史,在此面臨一個大節點。蓋自宋代以來,中國自身文明經二千年世界領先的農業生產、社會發展所積累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已開始閃現向新的文明階段躍升或轉型的軌跡,《萬曆十五年》曾稱宋代諸多方面「已如現代國家」。惜為蒙元所滅,上述進程中斷一百年。好在這一百年,從全球範圍看,時間尚不緊迫,中國還耽誤得起。蒙元被逐,重回荒漠,明繼宋起,在思想、文化以及經濟發展上,全面祧續宋人。明是個很奇特的朝代,一面很是衰邁、昏黯以致暴虐,一面又孕育着朝氣蓬勃的社會歷史因素,逮至萬曆間,各種突破跡象已十分明顯。然天不佑中華,明朝自身積攢的激烈社會矛盾終於爆發而導致嚴重內亂,同時,曾為蒙古所敗的金人後裔,在沉淪荒蠻、幾近湮滅三百年後,重獲新生,日漸具備強大破壞力,而益為明朝大患。內外雙憂,並至齊發。明遂先於甲申年(1644)失北都,復於乙酉年(1645)喪南京,終於滅亡。這是繼宋亡之後,作為漢族國家的中國第二次整體亡國。但這次後果更為慘痛,原因是同時西方的歐洲也開始其現代轉型。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文化積累來看,東西方世界本可謂棋逢對手、銖兩悉稱,正待好好比試一番。可惜,中國卻因一個意外情形,從競賽中退出了—好比奧運會選手在起跑時卻突然退賽。
我們於中國因被滿清所主所遭受真正損失的解讀,不在民族主義方面或感情。這當中,過去不太注意或很少談論的,是新統治者與中國文明之間有很大的落差。隨之,帶來兩個後果,一是本身創新能力已然不足,次而,作為異族入主者又勢必採取精神思想的高壓與箍束。兩個因素交織,造成各種羈絆,令中國活力頓失,而嚴重拖了歷史後腿。事實證明,有清一代,中國雖能秉其發達農業之優勢,以及在東方暫無敵手之地利,續其強盛國勢至康雍乾時期,但在思想、制度和經濟上,卻無變革跡象。滿清的好處是,總算比蒙元能識良莠,虛心接受、學習和融入高等的文化;而它的問題是,受制於自身高度,只能亦步亦趨,照搬照抄前朝,論創新的能力,實在不足觀。這對中國,無形中是多大拖累,後人很難設身處地體會到。實際以明代最後五十年思想、政治、社會的情形來看,若非這一干擾,中國經過當時業已啟動的思想啟蒙,得以進入制度變革、完成歷史蛻變,可能性相當大。然而,異族統治尤其是文化落差,突然間扭轉了歷史方向。中國落在西方後頭,關鍵就在這二百餘年。我對滿人這民族不抱偏見,但從歷史角度說,滿清統治在攪擾中國歷史進程這一點上,實難辭其咎。此事若發生在中世紀,猶可另當別論。晉以後北中國有五胡之亂,唐以後五代也曾短暫如此,後來金滅北宋、蒙古亡南宋,每一次都對文明造成破壞與羈絆,情況也越來越嚴重,但我們覺得基本可以僅作為民族衝突來看,還談不上扭轉中國的歷史方向。那是因為,第一,整個人類文明尚未到打開一扇新門的時候,世界歷史還處在舊的格局當中;第二,中國自身也沒有真正的新萌芽發育和生長,社會生產力以及配套的制度還算適合、夠用,變革與突破的要求實際並未如何感受到。可十七世紀全然不同,人類近代化已肇其端始,中國在舊制度下的苦悶也忍無可忍、正待噴薄欲發,偏偏這個當口,滿清來這麼一下子,真的令人扼腕。
故而明亡時刻,主要在這一層,才是中國歷史值得高度關注的重大節點。對於它的歷史與文化後果,當時中國不少傑出人物,便有明白的認識或強烈預感,後來反而認識不如當時清楚。鴉片戰爭以迄日本侵華,中國有將近百年處在生死存亡之間,故明季這段歷史,因此被「觸景生情」,更多從亡國之痛、民族衝突意義上,被近世奪為酒杯,澆「愛國」之塊壘,這也沒有什麼不對抑或不可,問題在於這段歷史本身所含問題及所達深度,實際遠踰乎此。我覺得,黃宗羲、呂留良、徐枋等人思想裏都隱約有這樣的看法:明亡本身無甚可「痛」;可「痛」者,乃是明為清亡,亦即先進文明被落後文明所毀。那意味着,中國從一個已經達到的歷史高度,大幅跌落並裹足不前。這才是明清鼎革無限悲涼處,不知此,對於「野哭」二字只怕難會其意。
不能從文明的損失着眼,矻矻於民族情緒,會使我們錯失這段歷史的真正教益。對各國歷史來說,民族問題其實都是動態的,古代中國講「夷夏之辨」,但這字眼簡直無法作歷史的推求,不要說滿清、蒙古、西域諸族,如果推到商代,連周人也算「外夷」。何況沿着狹隘民族主義觀點朝前走,往往還將去往反方向,實用主義地模糊一些是非。即以清朝來論,當它作為入侵者、亡中國者時,固然是被痛恨的,但當它為中國帶來大片疆土之後,好多人又破涕為笑,榮耀地認作一個偉大朝代。將近四百年來,明清易代這件事的真正意義,就這樣被模糊、被遺忘、被丟棄,而彼時一代甚至幾代中國人的苦痛酸辛,都成了過眼雲煙。
我對短命僅一載的弘光朝感到不能放下,蓋出於不忍以上況味就這樣付諸流水,而想把它重新喚回於人們記憶,於是,鈎故索舊、大書特書。《黑洞》把對弘光朝的所感所思,提煉為十個問題。《野哭》則換換方式和角度,借十餘位在不同側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來加呈現。我希望,借助於選材,加上我初淺的研究與表現,讓這有轉折點意義的時刻,得還鮮明。
被安排於書中露面的,有朱明王朝確切的末代皇帝朱由崧,有弘光樞臣和關鍵人物史可法,有稱為「明代蘇武」的左懋第,有以兵變致南明解體的左良玉,有普遍目為南京禍根的阮大鋮,有秦淮河畔苦悶的青春叛逆群體,有時代思想高度的體現者黃宗羲,有以十七齡慷慨赴死的少年天才夏完淳,有傳奇說書家柳敬亭,有「遺民現象」的典型徐枋等…… 他們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學生、妓女、藝人、學者、隱士、起義者,還算廣泛,覆蓋了社會多個層面。
寫作方法,也得考慮。過去說「文史不分家」,其實不對。文、史是分家的,或者說應該分家。文學和史學,一為藝術,一為學問;一個是主觀、情感的表現,一個是客觀、事實的陳述。不分家,既不合道理,還有不少副作用。中國史學某些先天不足,即因「文史不分家」而來。或者以美惡代替事實,或者視史撰如說部,覺得添油加醋、「支離構辭,穿鑿會巧」,關係不大。所以對本書這一類寫作來說,「文」與「史」的確是一對矛盾,處理不善,極易「以文害史」。我給自己立了規矩:文史分家,才學相濟。前半句講要以史學為本,絕不讓文學的東西有損史學;後半句講另一面,即才足以濟學,不能只剩下乾巴巴的「學」,成了尋章摘句、掉書袋,而觸碰不到歷史的人性內涵。
具體地講,直到現在,關於傳記寫作還有不少人主張可以虛構,認為寫到細節的時候如果史料不足,只好用虛構和想像加以填補。誠然,寫作者有他的難處,史料總有所不足、有所不能到,因此,發揮一些想像,加點虛構,好像在所不免。問題是,沒有哪位作者高明到能夠確保他的想像或虛構可以符合實際。由於自認不能這樣高明,我是寧付闕如,絕不虛構。還有人認為,傳記寫作免不了來點虛構無關史料和事實,而是基於敍事美學的理由;似乎不如此,人物很難鮮活,個性挖掘和表現就不能深入。這只是一個錯覺。小說極盛時代以來,作家們普遍習慣於或過分依賴虛構,好像文學性便等於虛構。其實,虛構既非文學性的來源,亦非它最上乘的功夫。離開虛構便有些不知所措,乃是文章活性衰退所致。倘如語言有質感、有溫度,非虛構非但不損失文學性,相反本身就帶來獨特的文章之美和閱讀快感。當然,我們也確讀到很多乏味的、史學足而文學不足的傳記作品,但它們的問題都出在語言上,並非因為不擅虛構。
既然不用虛構,《野哭》便奉行「有一件材料說一分話」,做到人物言行(哪怕隻言片語)、事件始末(哪怕細枝末節)無一字無來歷,全都有案可稽。這就是為什麼所有引文,據自何人何書,從版本到頁碼,我們都備具其詳,以便驗核。我沒辦法保證這些材料的原始真實性,但可以保證自己不曾脫離史料,另外虛構或杜撰過什麼。這當中,有時涉及同一事不同材料間的差異,倘在能力範圍內,我也試予考證、辨疏(例如史可法的生年問題),以求去偽存真。
這樣做,真正目的是想對歷史拿出誠意。我覺得這正是我們一直缺乏的,而且越來越缺乏。雖然對歷史的誠意,並不在於形式,但以我們現實來論,即便只是形式,也非常重要。形式至少有助於約束我們,不是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我們說的每句話、每件事是有出處的,可查可考;這樣,如果我們斷章取義、夾帶私貨了,別人可以立予核實、指出或提出商榷。
歷史需要敬畏。謔弄歷史,無利可圖。以歷史為妾婦,呼來斥去,有時頗為快意,但就如課堂上不好好聽講、調皮搗亂的學生,到頭來要懊悔的只有他自己。歷史是一位好老師,它嘴裏說出的每句話,都是可讓人受益解惑的知識,應該注意聽講。
與此相關,又有四個字:尊重古人。可能是自視高明,當代史學多年來慣於對古人頤指氣使。有時橫加指責和訓斥,有時相反,用當代思想感情拔高古人。對人對事都是如此,屢用今天義理來裁量,或強求、或曲解。姑舉一例,比如史可法,有人嫉之如仇,原因居然是他為弘光朝制訂政策時置「滅寇」第一而以「禦虜」第二。然而,身為明朝大臣,這本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當時,李自成對明朝有「君父之仇」,滿清名義上卻替明朝報了這君父之仇(此即為何起初明室以「申包胥哭秦庭」故事視吳三桂借兵)。依禮法來論,「滅寇」第一乃明朝必有之義,不單史可法,孫可法、張可法、胡可法,不拘誰當那個東閣大學士,都得這麼制訂政策。今人盡可因自己立場而愛戴李自成,但若嗔怪明朝的首相史可法不具同樣感情,就不免雞同鴨講了。凡此,即因不守「當時事,當時語」的原則,而那不過是史學不失客觀性的起碼要求。後人或許是比古人高明,但不要以此笑古人,古代的事情有它自身道理和原由,嘲笑和批判之前,至少該向讀者講清楚古人何以作此想、有此舉。
類似還如孫中山稱讚洪承疇:「五族爭大節,華夏生光輝。生靈不塗炭,功高誰不知。滿回中原日,漢戚存多時。文襄韜略策,安裔換清衣。」較之當年,竟是南轅北轍了。關於「生靈不塗炭」,以我們知道的論,洪承疇降清實在不能說起到這種作用。清兵入關後,北方基本未聞屠戮,只因各地望風而降、未加抵抗,後來到了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發生大屠殺。故爾,非得稱讚洪承疇「功高」,只能落在「力促中華一統」、「滿回中原日」這層意思上。俗白地講,洪承疇投降,好就好在讓中國版圖擴大了。這,一是結果論,二是實利論—因有如此的結果和實利,便對事情另抱一種觀點。但依同樣邏輯,吳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該變一下呢?看不出為何厚此薄彼。莫非因為吳三桂後又反清,洪承疇卻只對大清忠心耿耿?古時有古時的語境和是非,因而比較穩妥的辦法是,一面可以就古今的不同做出說明,一面對過往歷史還是堅持「當時事,當時語」,不妄自改易,否則就會人為造成很多混亂,終至於無法收拾。
略事申陳,權為引子。
兩年間,都在從事關於明末弘光朝的寫作。去年寫完一本,《黑洞:弘光紀事》,是從專題的角度來寫,寫了十個問題。這一本寫人物,名之《野哭:弘光列傳》。
書名取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細林野哭》。我在《夏完淳集》裏一見到,就被「野哭」兩個字攫住了,覺得有股異樣的力量。「野」在古漢語,有無家、荒蕪並兼野鄙陋文諸意。「野哭」並非只在完淳的筆下出現過,其他朝代,亦有以此為題賦詩者,如唐劉叉之七古,清沈曾植之五律等;但我感覺,似乎用於明清易代之際,這詞才格外有百感交集的況味。
弘光年,是明為清亡真正而確切的時間。中國歷史,在此面臨一個大節點。蓋自宋代以來,中國自身文明經二千年世界領先的農業生產、社會發展所積累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已開始閃現向新的文明階段躍升或轉型的軌跡,《萬曆十五年》曾稱宋代諸多方面「已如現代國家」。惜為蒙元所滅,上述進程中斷一百年。好在這一百年,從全球範圍看,時間尚不緊迫,中國還耽誤得起。蒙元被逐,重回荒漠,明繼宋起,在思想、文化以及經濟發展上,全面祧續宋人。明是個很奇特的朝代,一面很是衰邁、昏黯以致暴虐,一面又孕育着朝氣蓬勃的社會歷史因素,逮至萬曆間,各種突破跡象已十分明顯。然天不佑中華,明朝自身積攢的激烈社會矛盾終於爆發而導致嚴重內亂,同時,曾為蒙古所敗的金人後裔,在沉淪荒蠻、幾近湮滅三百年後,重獲新生,日漸具備強大破壞力,而益為明朝大患。內外雙憂,並至齊發。明遂先於甲申年(1644)失北都,復於乙酉年(1645)喪南京,終於滅亡。這是繼宋亡之後,作為漢族國家的中國第二次整體亡國。但這次後果更為慘痛,原因是同時西方的歐洲也開始其現代轉型。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文化積累來看,東西方世界本可謂棋逢對手、銖兩悉稱,正待好好比試一番。可惜,中國卻因一個意外情形,從競賽中退出了—好比奧運會選手在起跑時卻突然退賽。
我們於中國因被滿清所主所遭受真正損失的解讀,不在民族主義方面或感情。這當中,過去不太注意或很少談論的,是新統治者與中國文明之間有很大的落差。隨之,帶來兩個後果,一是本身創新能力已然不足,次而,作為異族入主者又勢必採取精神思想的高壓與箍束。兩個因素交織,造成各種羈絆,令中國活力頓失,而嚴重拖了歷史後腿。事實證明,有清一代,中國雖能秉其發達農業之優勢,以及在東方暫無敵手之地利,續其強盛國勢至康雍乾時期,但在思想、制度和經濟上,卻無變革跡象。滿清的好處是,總算比蒙元能識良莠,虛心接受、學習和融入高等的文化;而它的問題是,受制於自身高度,只能亦步亦趨,照搬照抄前朝,論創新的能力,實在不足觀。這對中國,無形中是多大拖累,後人很難設身處地體會到。實際以明代最後五十年思想、政治、社會的情形來看,若非這一干擾,中國經過當時業已啟動的思想啟蒙,得以進入制度變革、完成歷史蛻變,可能性相當大。然而,異族統治尤其是文化落差,突然間扭轉了歷史方向。中國落在西方後頭,關鍵就在這二百餘年。我對滿人這民族不抱偏見,但從歷史角度說,滿清統治在攪擾中國歷史進程這一點上,實難辭其咎。此事若發生在中世紀,猶可另當別論。晉以後北中國有五胡之亂,唐以後五代也曾短暫如此,後來金滅北宋、蒙古亡南宋,每一次都對文明造成破壞與羈絆,情況也越來越嚴重,但我們覺得基本可以僅作為民族衝突來看,還談不上扭轉中國的歷史方向。那是因為,第一,整個人類文明尚未到打開一扇新門的時候,世界歷史還處在舊的格局當中;第二,中國自身也沒有真正的新萌芽發育和生長,社會生產力以及配套的制度還算適合、夠用,變革與突破的要求實際並未如何感受到。可十七世紀全然不同,人類近代化已肇其端始,中國在舊制度下的苦悶也忍無可忍、正待噴薄欲發,偏偏這個當口,滿清來這麼一下子,真的令人扼腕。
故而明亡時刻,主要在這一層,才是中國歷史值得高度關注的重大節點。對於它的歷史與文化後果,當時中國不少傑出人物,便有明白的認識或強烈預感,後來反而認識不如當時清楚。鴉片戰爭以迄日本侵華,中國有將近百年處在生死存亡之間,故明季這段歷史,因此被「觸景生情」,更多從亡國之痛、民族衝突意義上,被近世奪為酒杯,澆「愛國」之塊壘,這也沒有什麼不對抑或不可,問題在於這段歷史本身所含問題及所達深度,實際遠踰乎此。我覺得,黃宗羲、呂留良、徐枋等人思想裏都隱約有這樣的看法:明亡本身無甚可「痛」;可「痛」者,乃是明為清亡,亦即先進文明被落後文明所毀。那意味着,中國從一個已經達到的歷史高度,大幅跌落並裹足不前。這才是明清鼎革無限悲涼處,不知此,對於「野哭」二字只怕難會其意。
不能從文明的損失着眼,矻矻於民族情緒,會使我們錯失這段歷史的真正教益。對各國歷史來說,民族問題其實都是動態的,古代中國講「夷夏之辨」,但這字眼簡直無法作歷史的推求,不要說滿清、蒙古、西域諸族,如果推到商代,連周人也算「外夷」。何況沿着狹隘民族主義觀點朝前走,往往還將去往反方向,實用主義地模糊一些是非。即以清朝來論,當它作為入侵者、亡中國者時,固然是被痛恨的,但當它為中國帶來大片疆土之後,好多人又破涕為笑,榮耀地認作一個偉大朝代。將近四百年來,明清易代這件事的真正意義,就這樣被模糊、被遺忘、被丟棄,而彼時一代甚至幾代中國人的苦痛酸辛,都成了過眼雲煙。
我對短命僅一載的弘光朝感到不能放下,蓋出於不忍以上況味就這樣付諸流水,而想把它重新喚回於人們記憶,於是,鈎故索舊、大書特書。《黑洞》把對弘光朝的所感所思,提煉為十個問題。《野哭》則換換方式和角度,借十餘位在不同側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來加呈現。我希望,借助於選材,加上我初淺的研究與表現,讓這有轉折點意義的時刻,得還鮮明。
被安排於書中露面的,有朱明王朝確切的末代皇帝朱由崧,有弘光樞臣和關鍵人物史可法,有稱為「明代蘇武」的左懋第,有以兵變致南明解體的左良玉,有普遍目為南京禍根的阮大鋮,有秦淮河畔苦悶的青春叛逆群體,有時代思想高度的體現者黃宗羲,有以十七齡慷慨赴死的少年天才夏完淳,有傳奇說書家柳敬亭,有「遺民現象」的典型徐枋等…… 他們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學生、妓女、藝人、學者、隱士、起義者,還算廣泛,覆蓋了社會多個層面。
寫作方法,也得考慮。過去說「文史不分家」,其實不對。文、史是分家的,或者說應該分家。文學和史學,一為藝術,一為學問;一個是主觀、情感的表現,一個是客觀、事實的陳述。不分家,既不合道理,還有不少副作用。中國史學某些先天不足,即因「文史不分家」而來。或者以美惡代替事實,或者視史撰如說部,覺得添油加醋、「支離構辭,穿鑿會巧」,關係不大。所以對本書這一類寫作來說,「文」與「史」的確是一對矛盾,處理不善,極易「以文害史」。我給自己立了規矩:文史分家,才學相濟。前半句講要以史學為本,絕不讓文學的東西有損史學;後半句講另一面,即才足以濟學,不能只剩下乾巴巴的「學」,成了尋章摘句、掉書袋,而觸碰不到歷史的人性內涵。
具體地講,直到現在,關於傳記寫作還有不少人主張可以虛構,認為寫到細節的時候如果史料不足,只好用虛構和想像加以填補。誠然,寫作者有他的難處,史料總有所不足、有所不能到,因此,發揮一些想像,加點虛構,好像在所不免。問題是,沒有哪位作者高明到能夠確保他的想像或虛構可以符合實際。由於自認不能這樣高明,我是寧付闕如,絕不虛構。還有人認為,傳記寫作免不了來點虛構無關史料和事實,而是基於敍事美學的理由;似乎不如此,人物很難鮮活,個性挖掘和表現就不能深入。這只是一個錯覺。小說極盛時代以來,作家們普遍習慣於或過分依賴虛構,好像文學性便等於虛構。其實,虛構既非文學性的來源,亦非它最上乘的功夫。離開虛構便有些不知所措,乃是文章活性衰退所致。倘如語言有質感、有溫度,非虛構非但不損失文學性,相反本身就帶來獨特的文章之美和閱讀快感。當然,我們也確讀到很多乏味的、史學足而文學不足的傳記作品,但它們的問題都出在語言上,並非因為不擅虛構。
既然不用虛構,《野哭》便奉行「有一件材料說一分話」,做到人物言行(哪怕隻言片語)、事件始末(哪怕細枝末節)無一字無來歷,全都有案可稽。這就是為什麼所有引文,據自何人何書,從版本到頁碼,我們都備具其詳,以便驗核。我沒辦法保證這些材料的原始真實性,但可以保證自己不曾脫離史料,另外虛構或杜撰過什麼。這當中,有時涉及同一事不同材料間的差異,倘在能力範圍內,我也試予考證、辨疏(例如史可法的生年問題),以求去偽存真。
這樣做,真正目的是想對歷史拿出誠意。我覺得這正是我們一直缺乏的,而且越來越缺乏。雖然對歷史的誠意,並不在於形式,但以我們現實來論,即便只是形式,也非常重要。形式至少有助於約束我們,不是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我們說的每句話、每件事是有出處的,可查可考;這樣,如果我們斷章取義、夾帶私貨了,別人可以立予核實、指出或提出商榷。
歷史需要敬畏。謔弄歷史,無利可圖。以歷史為妾婦,呼來斥去,有時頗為快意,但就如課堂上不好好聽講、調皮搗亂的學生,到頭來要懊悔的只有他自己。歷史是一位好老師,它嘴裏說出的每句話,都是可讓人受益解惑的知識,應該注意聽講。
與此相關,又有四個字:尊重古人。可能是自視高明,當代史學多年來慣於對古人頤指氣使。有時橫加指責和訓斥,有時相反,用當代思想感情拔高古人。對人對事都是如此,屢用今天義理來裁量,或強求、或曲解。姑舉一例,比如史可法,有人嫉之如仇,原因居然是他為弘光朝制訂政策時置「滅寇」第一而以「禦虜」第二。然而,身為明朝大臣,這本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當時,李自成對明朝有「君父之仇」,滿清名義上卻替明朝報了這君父之仇(此即為何起初明室以「申包胥哭秦庭」故事視吳三桂借兵)。依禮法來論,「滅寇」第一乃明朝必有之義,不單史可法,孫可法、張可法、胡可法,不拘誰當那個東閣大學士,都得這麼制訂政策。今人盡可因自己立場而愛戴李自成,但若嗔怪明朝的首相史可法不具同樣感情,就不免雞同鴨講了。凡此,即因不守「當時事,當時語」的原則,而那不過是史學不失客觀性的起碼要求。後人或許是比古人高明,但不要以此笑古人,古代的事情有它自身道理和原由,嘲笑和批判之前,至少該向讀者講清楚古人何以作此想、有此舉。
類似還如孫中山稱讚洪承疇:「五族爭大節,華夏生光輝。生靈不塗炭,功高誰不知。滿回中原日,漢戚存多時。文襄韜略策,安裔換清衣。」較之當年,竟是南轅北轍了。關於「生靈不塗炭」,以我們知道的論,洪承疇降清實在不能說起到這種作用。清兵入關後,北方基本未聞屠戮,只因各地望風而降、未加抵抗,後來到了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發生大屠殺。故爾,非得稱讚洪承疇「功高」,只能落在「力促中華一統」、「滿回中原日」這層意思上。俗白地講,洪承疇投降,好就好在讓中國版圖擴大了。這,一是結果論,二是實利論—因有如此的結果和實利,便對事情另抱一種觀點。但依同樣邏輯,吳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該變一下呢?看不出為何厚此薄彼。莫非因為吳三桂後又反清,洪承疇卻只對大清忠心耿耿?古時有古時的語境和是非,因而比較穩妥的辦法是,一面可以就古今的不同做出說明,一面對過往歷史還是堅持「當時事,當時語」,不妄自改易,否則就會人為造成很多混亂,終至於無法收拾。
略事申陳,權為引子。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9折$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