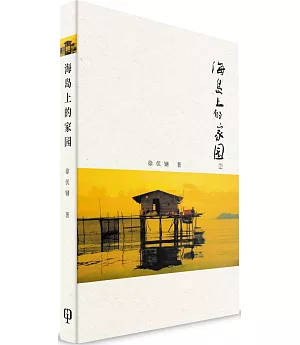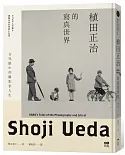序一
伏鋼的兩隻眼睛
嚴孟達 新加坡著名時事評論家、《聯合早報》前副總編輯
伏鋼的兩隻眼睛,一只是作家之眼,另一只是攝影家之眼。他以作家的細膩眼光看人看事皆文章,以攝影家的敏銳眼光觀人觀景皆世態繽紛。
這是一個性格鮮明、天不怕地不怕的傢伙。兩年前,他跟我說要去沙巴仙本那一個外島上,重訪一位嫁給島上土著難民的日本女子,我的第一個反是,這就是“百分百的伏鋼”。
幾年前在他的一次新書發佈會上,聽到他的朋友圈戲稱他這個人“一根筋”,覺得形容得太妙太貼切了。
他決定了要做的事,很難改變。
這是他在寫作、在攝影兩個領域都大有所成的動力。
他不講究衣著裝扮,卻很有生活品味。品味來自他博覽的群書,來自他對藝術的欣賞和追求。
他的文章有濃郁人情味,並非為文造情,而是出自他天生對人對事的同理心,訴諸筆下,人情味自然流露,沒有多餘的矯情。
本書幾乎每篇文章都有故事性,有情節,是報導文學,是散文,有的也像短篇小說。
他以日本女作家川崎朋子為“專業楷模”,落實了實地考察的精神。
他愛旅遊,但不是觀光,他不在意食住條件,哪裡有故事有歷史的地方,他都有一股衝動,要去為讀者作記錄,為後世留傳可資借鑒的人與事。
他老家在成都,標準的四川漢子,他的筆下和攝影機鏡頭下卻是飽含對南洋風土的熱愛。他在南洋的足跡不是一般人跟得上,因為他有一顆年輕的心,以及對城市以外的世界抱著非一般人的嚮往。
如果他不是作家,他會是一個探險家。
他不會耽於城市生活的逸樂,他的心總是在遠方,他總在尋找一個詩人的境界,一個小說家的天堂,攝影家的幻境。
他對所到之處都產生一份感情,對幸福與不幸的人與事有自己敏銳而深刻的注解。
讀他的作品,就如進入多姿多彩的塵世,人與事都那麼真實,又那麼引人遐思。
《荒島上的家園》,把讀者帶到沙巴的山打根和小鎮仙本那,去走一段奇異的旅程。
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的報告文學《望鄉》和同名電影,想必給了伏鋼很大的震撼。一個在20世紀初被賣身淪落南洋的可憐日本女子,在山打根遭受的屈辱生活,是那一個時代的悲劇。
阿崎的命運與山打根結合在一起,為這個老城注入許多感人的色彩。一個日本妓女不會給山打根留下什麼紀念性的足跡,卻牽引著伏鋼攜著一本《望鄉》,帶著一種朝聖的心情,去感受那一段早已遠去不留絲毫痕跡的悲情。
然而,此行卻引發出仙本那外島上另一段有別於世俗的幸福故事。來自日本古都柰良的大學畢業女子順子因熱愛潛水,到沙巴外島當潛水教練,姻緣註定,愛上一位難民身份的巴夭族男人,並在島上結婚生子,建立了自己的家。
那是她的異鄉,也是她的天堂。
別人以迷惑不解的眼光看待她驚世駭俗的舉動,放棄日本現代城市文明,投入一個與她的教養與成長背景格格不入的陌生環境,她卻始終沒有反悔,甚至厭倦日本遊客同情的眼光。
大海深處是順子理想中的美麗世界,她的選擇是那麼堅定,感動了起初還反對這段婚姻的父母,年老的父母後來幾乎每年都來探望她。我想,為人父者始終是放心不下自己的骨肉,須要見證與分享她的幸福。
伏鋼著墨不多的順子父母,卻突出了一對偉大父母的身影。順子的故事,平淡中帶著淡淡的哀愁,哀愁中又透露絲絲的喜悅,讀了這篇《海島上的家園》,我也要向順子獻上一份祝福!
感謝伏鋼舟車勞頓,冒著一定的風險,帶給我們如此美麗的篇章。
東馬沙撈越有一條著名的拉讓江,江畔一位憤怒詩人,對於熱帶雨林多年來不斷地被“合法”砍伐給當地生態造成的嚴重破壞,無能為力,只能借助詩歌表達心中的怒火。
我不知道伏鋼是因為讀了這位“拉讓江詩人”吳岸的詩才去探訪他,還是去了才目睹拉讓江正在“淌血”,才聽到詩人訴諸詩歌的怒吼。
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伏鋼對當地人的同情心與對詩人的敬仰都在《詩人,我聽到了你的怒吼》篇中表達出來。
在《我的兩位本地攝影老朋友》中,伏鋼向兩位業餘的老攝影家致敬。他們兩位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普通受薪階級,一位是廚師何國堅,一位是清潔工雷福勝,兩人都對攝影藝術抱著一輩子的執著,他們都年過80,到老都沒有放棄他們很專業的“業餘”愛好,幾十年來累積的黑白佳作,記錄了新加坡不同時期的社會面貌。
他這兩位“攝影老朋友”年輕時純粹是“喜歡拍照”,但卻“無心插柳柳成蔭”,豐富了本地攝影藝術的成果。
伏鋼的書房牆壁上掛著一幅珍貴的圖片,上世紀50年代南洋大學校園內草創時期的行政樓,原本就已是古色古香的建築,定格在那個已遠去的舊時代,以現代眼光來看,構圖的氣氛更顯滄桑。
伏鋼知道這張照片的歷史價值,更佩服捕捉這個歷史鏡頭的雷福勝的攝影功力。
多年前,當伏鋼還在《聯合早報》當編輯的時候,從同事口中知道報社裡一位清潔工竟然跟自己仰慕的攝影大師葉暢芬有深厚交情,因此主動去結識他。
這位80多歲直到今天還在做清潔工的雷福勝,清貧一輩子,卻不為金錢所動。他悄悄地把伏鋼在攝影展上購買他作品的錢歸還,算是報答伏鋼這位熱心朋友的知遇之恩。伏鋼與兩位老藝術家感人的忘年之交,讓人讀之如飲一杯暖入心脾的好茶。
我也有幸在伏鋼家中認識他們。
在《萬里漂流歸程中——高纓老師逝世周年祭》和《我對流沙河先生的一點回憶》兩篇文章中,字裡行間處處流露出伏鋼對家鄉兩位作家的欽佩與懷念,流沙河與高纓兩人是超過一甲子的朋友,對伏鋼亦師亦友,兩人不只是詩人作家更是學問家,身上都有太多的精彩故事。高纓為伏鋼悼念父親的文章《父親的遺產》修飾文字並重新謄寫,後來高纓夫人段傳琛對伏鋼說:“我家高老頭寫作一輩子,為別人謄稿的事,你是第一人!”簡單幾句話道出了高纓扶掖後輩的熱忱。
文中記述峨眉山一段橋樁漂流萬里,被日本良寬法師拾得,後來回到峨眉清音閣建立良寬詩碑的文壇佳話。當年在新潟縣海邊的宮川濱撿到這段橋樁的若是一個與漢學無緣的普通日本人,也就沒有了後來的曠世奇緣。
寫流沙河,伏鋼說:“在我心目中,他永遠是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山,是智慧可愛的現代莊子。”
這位“現代莊子”博古通今,他的閱讀範圍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野史民俗,無所不包。他對新加坡鳳山寺對聯中“鳳皇”的“皇”字和“鸚武”的“武”字的釋義,顯露他很深的文字學修養。
流沙河第一次帶伏鋼拜會高纓先生,偶然遇見一位鄉下老木匠,於是同木匠聊起過去自己“拉大鋸”的事來。詩人碰到木匠也可以交流甚歡,從一件小事,伏鋼把流沙河一種隨和不拘的形象生動地勾勒了出來。他說:“我能同沙河先生真誠交往幾十年,我想,也許他也把我當做了那位鄉下木匠吧。”伏鋼的自謙,是他文字可愛之處。
伏鋼寫高纓和流沙河兩位忘年之交,情節引人入勝,兩位詩人的高風亮節躍然紙上。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寫林青霞去他家拍照,給這位大明星素描了一個更貼近人間煙火的形象:“她從未自以為是端起大明星架子對我指手畫腳,而是完全把她自己交給了我,從場景到角度,完全服從我的調度安排。難得她那樣的信任我,只需上前告訴她大致的取景構想,以及我的鏡頭方位,餘下的便全交給她,由她自自然然發揮去了。”
《湯姆遜眼中的新加坡》是對一段攝影界歷史的補白,“被公認為19世紀攝影領域的一座豐碑”的蘇格蘭攝影家約翰•湯姆遜(John Thomson, 1837–1921)跟新加坡和中國都有淵源,他的社會寫實攝影作品捕捉了百多年前新加坡和中國的舊時代面貌。
其實,伏鋼補白的更是早期殖民地時代的一段新加坡歷史。
《心月櫻花喜共參——陳瑞獻在京都妙心寺講演揮毫紀實》是一篇饒富禪意的紀實文字,形象生動地記敘了我國多元藝術家陳瑞獻在日本京都世界經濟論壇上的精彩演講,以及大師隨後“風捲殘雲”、“龍飛蛇舞”揮毫作畫的氣勢和場景,讓我們感受到了現場的特殊氣場。
伏鋼的文字功力深厚,寫情寫景都是那麼自然順暢,如《穿越西伯利亞森林大草原》,沒有刻意修飾的華麗辭藻,卻讓讀者如置身在那一列車上,讓我們一路用心領略俄羅斯的異國情調。
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年後的春天,百花盛開的時候,伏鋼再次回到他的家鄉中國四川,身上背著全套照相器材,手中提著大包行李,只身來到震中映秀鎮住下,回訪當年曾在廢墟中採訪過的每一個人。《映秀:十年回訪震區人》回顧當年一件件難忘的往事,親身感受十年來那裡的真切變化。對他來說,眼前所見的人與物,已是另一個全新世界。
“經過十年重建和休養生息,映秀新鎮徹底浴火重生,舊貌換新顏。”然而,重建後的映秀鎮上“高度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同時也讓他感到迷惑和無奈。
伏鋼懷著記者的敏銳,作家的熱情,重訪映秀,有欣慰,也有遺憾。《父親的遺產》和《我的母親田素清》以幾件小事,追憶父母的養育之恩,寥寥幾筆,動人心弦。讀罷,不禁想起歐陽修的《瀧岡阡表》。
伏鋼善於寫人物,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在他的筆下,很立體地站在讀者面前。
他帶著一顆稚子的心去探索世界,探索人生,自然形成他的作品特色。
期待他將來能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