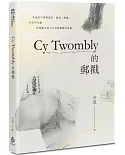序文選摘
詩的敘事與抒情
所有詩的書寫,都是一種靈魂的探險,只有挖得越深才會感受到生命的驚險。內心的起伏震盪,從來是深不可測。敢於挖得越深,看見的生命風景就越精彩。在一些文學獎的評審過程中,曾經也遇到解昆樺的作品。當時並不知道作者是誰,揭開謎底後,才發現是一位熟悉的學生。如果與他的年紀來看,他應該是屬於中生代的詩人。這個世代開始在文字中冒險前進之際,臺灣社會已經正式解嚴。解放以後的文學風景,確實比上個世代的創作者還更精彩。從他的詩齡來看,似乎已經不再受到任何的政治干涉。整個想像的水域,比起前行代還要遼闊。
這是解昆樺的第一本詩集,前後累積二十餘年的作品。在年輕族群的行列裡,這本詩集應該已經遲到。閱讀他的想像與情緒,果然不再像從前那樣緊繃著心情。因為處在較為從容的海島,凡是感情所能到達之處,他的詩行也可以到達同樣的境界。解昆樺不是多產的詩人,這本詩集似乎累積了前後二十年的勞作。如果從賦比興的觀點來看,他的作品比較偏愛賦的手法。他總是給予自己觀察所到之處,非常迅速就以一首詩來定義自己的心情。在一定程度上,詩集中所收的作品,都是他參加不同文學獎的成績。如果不要受到文學獎的限制,就無需受到地景的限制,也無需受到競爭的干擾,詩人也許更可以從許多框架中解放出來。
詩集中有兩首詩結合了爵士搖滾,反而產生豐富的想像:
每株草都領有爵士的音符
當我孤獨穿越後,便恢復原狀
迅速地 柔韌地 抹消我的足跡
彷彿我不曾走過 彷彿我不曾活過 幽靈似地
草地比我更有資格擁有我的耳朵
而我不能
詩人在聆聽爵士樂的演出時,顯然被那樣的音色與節奏所感動。坐在草地上享受音樂節奏的敲打,內心揚起了某種震顫,久久無法平服。這是一種反襯的書寫,野草被踩過後便立刻平服。但是詩人的心情,接受爵士樂的洗禮之後,卻久久無法恢復原狀。詩人帶著我們引申出另外一種心情,人是有情的動物,能夠接受音樂節奏的感動與影響。
另外一首動人的詩是〈最美的墨色是白色〉,非常接近童詩,整首詩看起來是那樣的潔白。那種潔白,其實是折疊紙飛機的白紙,暗示著他無邪的童年。詩人在作品中自問:
空白測驗紙上的塗鴉
吹起飛落
那年我開的紙飛機
迫降何方?
詩人刻意歌頌自己的年少歲月,似乎也寫出了許多人的共同記憶。他以紙飛機來暗示失去的童年,整首詩的最後如此顯示出來:
在昨日與來日的空隙裡
花美如雲
藍空如硯
最美的墨色是白色
正如詩題那樣,是一種矛盾語法。墨黑與潔白是一種感官的對立,兩種強烈的顏色並置在一起,立刻形成絕對的反差。顯然那是他過去美麗歲月的一種回想,也是他生命中毫無牽掛的年華。他對自己的童年,有著強烈的鄉愁。而那樣的鄉愁,卻殘酷地提醒他那是他永遠回不去的生命原鄉。
這部詩集,有許多作品都是參加文學獎而釀造出來。參加文學獎比賽,而刺激了自己的想像。而那樣的想像,卻又受到地區文學獎的限制。這說明了為什麼詩人往往受到議題的拘囿,從而也局限了他的情感抒發。有時候詩的命題為了配合既有的事件,不免規範了詩人自己的想像。〈告別那些暴力者—記太陽花學運〉描述臺灣公民運動的重大轉折,這也是他所擅長賦的書寫:
星光有時微弱如燭火
像權力者這麼踐踏過我們
心中的那份意志,星光如此微弱如此閃爍
但聚集後也能燎原
也能開綻如太陽花
以詩行來定義重大的歷史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精神昇華的技巧。太過於貼近事件本身,卻使詩人的想像難以展開。把「微弱」與「閃爍」並置在一起,就產生強烈的對比,從而也拉高了詩的精神。敘事詩必須保持若即若離的高度,才有可能避開事件本身的牽制。這是一首危險的詩,幸好在最後兩行有及時挽回:「我們需要的/只是以星光給他們標上十字架。」
詩是一種危險的心靈探索,總是在絕境找到精神出口。解昆樺的詩齡已經超過二十年,慢慢進入中年。生活是一種探險,生命也是一種探險。前者是肉體的歷練,後者是精神的歷練。解昆樺在這兩種探險過程中,已經慢慢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在臺灣詩史的系譜裡,他逐漸進入中生代的階段。這個世代不再接受任何的權力干涉,也不再受到前輩詩人的干擾。他正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也正要開闢一個全新的領域。對於這個世代的創作者,我一直有很高的期待,新的語言,新的技巧,新的形式,都將豐富臺灣文學長流的未來。解昆樺所帶來的聲音,值得我繼續期待。
陳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