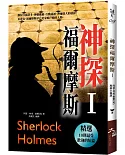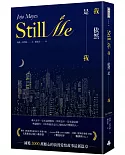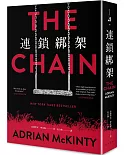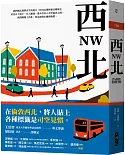導讀1
詩人王爾德:反骨的英國性
台大外文系教授/高維泓
在二十一世紀談王爾德(1854-1900),閃過眾人腦海無非是他的兩個身分,一是文學家,以刻劃英國上流社會虛偽的劇作與小說出名,二是同/雙性戀的身分。前者的成就無庸置疑,後者卻讓王爾德萬劫不復,從當紅文學才子變成過街老鼠。一八九五年,正當王爾德名望如日中天,同時有兩齣戲在倫敦劇院熱鬧上演(1),他的同性愛人道格拉斯(Lord Alfred
Douglas)的父親控訴他違反「性悖軌法(2)」(Sodomylaw)。在媒體喧騰與法官濫權下,王爾德被視為異端,判監禁並服苦役兩年,所有財物遭拍賣一空。出獄後的王爾德已是社會棄兒,只得靠朋友接濟,隱姓埋名移居巴黎,三年後孤獨地於某旅館與世長辭。直到一九五四年,亦是王爾德受審的六十年後,曾參與當年審判的英國法官亨福芮斯爵士(Sir Travers
Humphreys)才為他平反:「當年根本就不應該起訴王爾德。(3)」同年倫敦郡議會為了紀念他的百歲冥誕,於他住過的泰德街故居設了一個紀念牌。然而,當年的「恐同」早已摧毀一個超凡拔俗的作家。
這遲來的平反為同性戀平權運動史畫下新的一頁,但在文學史上,王爾德的詩藝直到今天都尚未獲得公允的評價。很少人關注當年猶是文青時期的他,踏入文壇的「起手式」是詩,離世前也是以長詩〈瑞丁監獄之歌〉(The Balladof Reading
Gaol)向糟蹋他的凡夫俗子告別。他甚至認為一八九三年發表的詩劇《莎樂美》(Salomé)比觀眾喜愛的其他舞台劇都好。他曾要求詩集出版社在合約及廣告裡,只能以「詩人」來稱呼他,而非「作者」。可見他十分嚴肅看待詩人這個身分。
要評價王爾德的詩,不能不提原生家庭的影響。他的父親是位外科醫生,母親珍.王爾德(Lady Jane Wilde, 1821-1896)除了熱中蒐集與翻譯本土民間故事,也是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及維護女權的詩人。她所發表的激進政論〈木已成舟〉(The Die is
Cast),因鼓吹顛覆英國統治,導致雜誌遭政府查禁。王爾德在這樣的家庭長大,比一般愛爾蘭人更直接地接觸反英國統治的種種訊息。母親的詩人及女性主義者身分,除了啟發他在文學與美學的品味與愛好,也使他習於用批判性的觀點戲謔偽善或不公義的社會現象。
王爾德在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及牛津大學就讀期間,所寫的英語詩即散見於愛爾蘭刊物。在他一八八一年出版第一本詩選《Poems》之前,他已經發表至少四十首詩,包括一八七八年獲得牛津大學紐帝蓋特獎(Newdigate Prize)的詩作〈拉溫納〉(Ravenna)在此之前,詩情洋溢的他已有四首作品被收入愛爾蘭詩選《LyraHibernica
Sacra》中(4)。值得玩味的是,即使已經負笈英國念書,大多數收錄在《Poems》裡的詩作,反而是先刊登於愛爾蘭本地的刊物,可見文青王爾德當時對於獲得出生地讀者肯定的渴望,似乎遠高於獲得英國本地讀者的認同。不幸的是,《Poems》出版後,在英國多招致負評:「王爾德先生的詩也許很美,但缺乏原創性,可以看到許多作家的影子。」批評家甚至不願意給王爾德任何讚賞,一方面批評他的詩「薄弱」,同時又說他的詩有六十幾位名作家的影子,例如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希尼(Philip Sidney)、東恩(John Donne)、拜倫(Lord
Byron)、莫里斯(WilliamMorris)等等(5)。持平而論,即便這些詩是王爾德年輕時學習寫詩的仿作,能被批評家指出有經典作家的影子,很難說不是貶中帶褒,或是要挫挫這位來自愛爾蘭年輕新秀的銳氣。然而,批評家當年把還是詩壇小咖的王爾德與前輩大咖相比,似乎沒能預見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與這些文壇經典作家平起平坐(6)。(內容為節錄,完整導讀請見本書)
(1)這兩部戲分別是《理想丈夫》與《不可兒戲》。在此之前,王爾德已發表兩齣喜劇《溫夫人的扇子》與《無足輕重的女人》,都十分受觀眾歡迎。
(2)當時尚未有同性戀這個概念。
(3)詳見Holland, Vyvan. Oscar Wilde and His Worl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0. 126. Holland 為王爾德的次子。王爾德入獄之後,妻子和兩個兒子都改姓Holland。王爾德出獄後以Sebastian Melmoth 為名隱居法國。
(4)這四首詩分別是〈O Well for him〉、〈The Unvintageable Sea〉、〈Onto One Dead〉、〈Day, Come not
Thus〉。經更訂後即為〈哭泣吧,慟,願善戰勝〉、〈新生〉、〈真知〉,及收錄於《王爾德詩選II》的〈西斯汀教堂響起的最後審判讚美詩〉。該詩集由愛爾蘭出版社M'Caw發行。有趣的是,其中也收錄了王爾德母親的詩作〈BrokenChorus〉及〈Aspirations for Death〉。母子作品同在一個詩選裡,頗有傳承的意味。
(5)詳見Kohl, Norbert. Oscar Wilde: The Works of a Conformist Reb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5-18.
(6)倒是當時美國的文藝批評家十分欣賞王爾德詩作,不像英國人如此刻薄。這可能是因為脫離了殖民統治的社會氛圍,能更持平地欣賞詩人欲傳達的美學。
導讀2
在一些線條的弧度裡,在某些色彩的美好與幽微中……──詩人藝術家王爾德
清大英語教學系副教授/鄧宜菁
王爾德不僅是個詩人,更常自詡為藝術家。他的生平和作品,都再再展現他對美與藝術的愛好,對美與藝術真諦的追尋。對他而言,「只有詩人是第一等的藝術家,因為他是色彩與形式的大師」。以此觀之,若果我們將王爾德稱為詩人藝術家,當非溢美之詞。
世人所熟知的王爾德是一名才華洋溢的劇作家。在《不可兒戲》、《溫夫人的扇子》等劇作中,他透過筆下的人物極盡嬉笑怒罵、嘲笑諷刺之能事。然而,除了劇作外,王爾德同時也創作詩歌、評論、童話與小說。他一生中所涉獵的文類堪稱廣泛。較少為人所注意的是,王爾德一直與藝術圈維持著緊密的關係,不僅十分關注當時藝壇的動靜與發展,也與不少藝術家有所往來,甚至交往密切,充分浸淫在其時代特有的文化氛圍中。從他早期的書信可以發現,此位愛爾蘭裔的英語文豪時常駐足於美術館與藝廊,觀看並冥思畫作。不論古典還是前衛的作品都能激發其想像力,源源不絕地供輸創作活動的能量。
在王爾德的時代,文學與繪畫相濡以沫,不僅相互啟發,更提供彼此重要的創作養分。王爾德在牛津求學時,對他影響甚鉅的兩位老師──華特.佩特(Walter Pater)與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皆兼具文學家與藝評家兩種身分。除了畫作之外,包括藝術理論、藝術思潮、藝術史,乃至於種種的藝術實踐,對形塑王爾德觀看的方式以及書寫的風格,影響皆不容小覷。由此看來,當我們閱讀其詩作時,若從繪畫的視角切入,或許會發現不少有趣的圖像元素。能言善道的王爾德不僅用文字傳遞了幽微的哲思與情感,更創造出華麗的印象與色彩。
王爾德在〈濟慈之墳〉一詩中悼念並稱頌濟慈為「詩人畫家」。然而,其實在他自己的詩作中,王爾德也頻頻展露詩人畫家之姿。不僅憑藉景象來喻情,更透過語言符號來創造色彩、鑲嵌印象,猶如用文字在作畫。在他眾多色彩繽紛、充滿光影對照的詩作中,有一系列冠有「印象」一詞的作品,如〈清晨印象〉、〈印象:花園〉、〈印象:大海〉等。看到「印象」二字,有人可能會在腦海中閃過生活片段與畫面,但只要對藝術史略有涉獵的讀者,或許馬上就會聯想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印象派繪畫。在解析王爾德筆下的「印象」前,我們不妨先了解一下其語言與書寫特色。王爾德偏好借助慣用語詞來創造新義,從而顛覆原有意義。他尤其鍾愛挪用藝術思潮的流行語彙。王爾德選擇與使用語詞的方式往往導致他的語言表達呈現極富爭議性的多音與多義特性。印象一詞,在王爾德筆下,也因而常衍生出超越大眾認知的意義,會隨著情境變化,從而發展出諸多不同的意涵。印象既可以表述外在感官印象,也可以指涉內在印象,也就是王爾德反覆提及的「心境」(moods,
états
d’âme)。王爾德在他的作品中經常有意無意將「印象」與「心境」混淆使用。對他而言,不論是創作或評論,其目的皆在記錄自己的印象,而記錄的同時,也是在重溫及抒發自己的心境。印象也好,心境也好,主要都還是回歸、指向個人的情感,甚或激情。因而在閱讀他的「印象」詩作時,我們既可將其視為種種印象的抒發,也可解讀為詩人隱藏在語言、意象堆砌後的心境甚或情感。職是之故,我們不妨可將他的詩作(不論有無冠上印象一詞)看成詩人種種心情的剪影與印象。如〈聖米尼亞托〉、〈亞諾河畔〉及〈蓮葉〉等寫景、詠物之詩。在色彩運用及意象生成中,交織、突顯的是詩人淒涼、甚或絕望的心境。在塵世的寂寞中,景色的描繪似乎不再流洩出對崇高、浪漫的天真想望或寧靜冥想,而是對未知的世界,對看不見的彼岸,對死亡的想像與嚮往之情。
身為一名作家,王爾德最早嘗試、且將其創作成果集結成書的文類,即是詩歌。然而,他的詩作卻是其作品中,一般讀者較少有機會接觸到的,或較容易忽略的類別。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批評傳統的影響。王爾德的《詩集》(Poems)雖是他第一部問世的作品,但自一八八一年出版後,就一直未得到評論者普遍的青睞。王爾德雖然曾在盛名時期加以修改並重新出版,但似乎並未徹底翻轉既定看法。在早期的詮釋模態中,缺乏原創性乃至於剽竊,是最常看到的負評。有評論者甚至聲稱在他的詩集中可偵測到六十來位詩人的聲音。然而,若將他的詩作置放於西方藝術發展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中來看,王爾德作品中的前衛特質以及其中暗藏的反思,可能就比較容易彰顯出來。(內容為節錄,完整導讀請見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