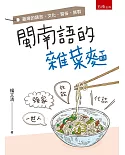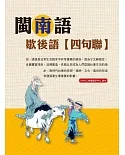導讀
拋棄的阮故鄉 總是也無惜
流浪來再流浪 風雨吹滿身
啼哭也不回來 青春彼當時
目屎若會流落 叫阮要怎樣
---愁人(文夏)〈流浪之歌〉第二拍
一、陳明仁---流浪的詩人,台語文界的武士
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的台語文(母語復振)運動中,不認識阿仁的很少,連國外來台灣的記者、觀察家或研究台灣問題的專家學者,內行人都會指名找他訪問、聊兩句,甚至跟他學台語。雖然如此,在台灣主流的文學圈,阿仁還是屬於邊緣分子,就連他自己家鄉彰化的文學史中排不上榜,編選的文學讀本也看不到他的詩文作品。因此,我們還是有需要來簡單介紹他的一些背景。
阿仁,本名陳明仁,使用過的筆名有a仁(a-jîn)、Babuza A.Sidaia、Asia
Jilimpo等等,1954年出生在彰化縣二林鎮的竹圍村,父親只是普通的台灣農夫,阿仁稱他是一個種作土地的藝術者。國小畢業前,阿仁沒離開過二林家鄉。國校畢業以後,阿仁就離開故鄉到外地求學流浪,初中還在中部,讀完初中就放棄省高中的學業到台北,打工賺錢,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學校、公司、工廠、行號、......不斷地換,高中讀過四個學校,從事的行業超過二十種,也因此對社會問題有敏銳的觀察,累積了豐富的社會經驗,對他後來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助益。
阿仁隻身從鄉下流浪到台北,「一直希望能找到一個讓他感覺值得花一輩子的時間去投入的工作」。阿仁寫作出道很早,少年時代就立志要做一個有名的文學家,可是稍長,讀到Russia作家大部份有名的作品都是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控訴統治者的不是,回頭看到台灣人當時的處境,那麼不堪,體認到所有的苦難都來自統治者的惡質,省思到做為台灣作家的使命,不能只是抒發一己的心思意念而已,而是應該效法Russia作家,為人民發聲,也深知文學必須是政治問題解決之後才有可能存在。於是,決定中斷文學創作,全心投入台灣的民主運動,希望先透過政治改造讓人民獲得解放,再回過頭來創作文學,結果從一個文學少年轉變成政治人。
那正是台灣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有將近十年的時間,在台灣每一場街頭運動都可以看到阿仁的身影。阿仁隨著反對運動,深入各基層人民的生活中,與他們同甘共苦,將歷史的哀愁當成精神上的安慰,也因此更堅信文學不只是用文字堆疊出一己的憂悶與無緣無故的情緒,而是人民身苦病痛的病歷表。在親自參與政治運動,嚴肅思考過台灣前途的種種問題以後,阿仁發現台灣的精神內涵與台灣人的價值觀有很嚴重的危機,於是逐漸找到自己創作的方向與主題。
阿仁於1985年就開始改用母語寫作,先從形式較短、用字較少的台語詩嘗試寫起,在所主編的黨外雜誌上零散發表。1988年在獄中,從獄友政治犯蔡有全那裏學白話字,1989年回到社會,1990年參加笠詩社,做一個流浪詩人,在《笠詩刊》繼續發表台語詩作。
除了參加文學活動之外,阿仁開始積極投入台語文運動。深入台灣各高中、大學擔任台文社團的指導老師,教台語、介紹台語文學,也擔任社區大學的台語教師,開設台語文基礎班/寫作班/播音班/歌謠班;在在當時所謂的地下電台,像寶島新聲、淡水河、華語台等電台製作及主持台語廣播節目。阿仁除了寫台語詩、散文之外,還翻譯日本卡通宮崎駿系列、叮噹貓系列錄影帶為台語發音;為台中民主電視台編寫台語答嘴鼓短劇劇本,策畫台語文學有聲叢刊每個月做發行。總之,就是希望透過各種管道、各種形式去推動台語白話文,使台語文能夠走入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
1990年尾,前衛出版社林文欽接編《台灣文藝》雜誌,聘請阿仁擔任編輯企劃,開闢台語文園地。1992年參加台灣筆會擔任理事,同年又與林宗源、黃勁連等人共同發起以母語寫詩的「蕃薯詩社」,在前衛出版第一本台語詩集《走找流浪的台灣》。1995年出版《流浪記事》、1996年出版《陳明仁台語歌詩》,後面這2本都是書與錄音帶一起出版上市。
1992、1994、1996年阿仁曾三度到北美洲美加各地巡迴演講,介紹台語文學、吟台語詩,結合當時在海外已經展開的台語文運動。1996年那一次回台灣以後,阿仁在台語文運動方面,有一個大躍進,除了與台語文有志合力創辦一份台語文學專業雜誌《台文Bong報》,提供台語文作品發表的園地外;由匹玆堡的台灣鄉親林皙陽籌組成立「李江卻台語文教基金會」為台語文運動提供穩定的經濟來源與固定的行政中心;更浪漫的是,阿仁在台電大樓旁邊的小巷內,開一家以台語歌與講台語為特殊風格的「巢窟咖啡館」,讓民主運動、社會運動及台語文運動的兄弟朋友在都市叢林裡有個聚會落腳的場所,《拋荒的故事》就是在「巢窟」裡寫出來的。
《台文Bong報》創刊後,阿仁開始在上面發表台語小說作品。1998年先是將在《Bong報》上發表過的小說作品集結成冊,以筆名Babuza A.Sidaia出版了第一本台語小說集《A-chhûn》,2000年再以筆名Asia
Jilimpo出版《拋荒的故事》。《拋荒的故事》出版後沒多久,台灣改朝換代,政治上有一個大轉變;阿仁個人也遇到人生的大關卡,就索性把「巢窟」收掉,離開台北,開始在台灣各地流浪做運動,他的生命與文學也從此進入另一個階段。
二、在世紀末回顧五、六○年代的那些人、那些事
在經營「巢窟咖啡店」的時候,阿仁一天差不多有10小時的時間都在店裡,有熟客人來,就跟客人喝咖啡、聊天、撞球,其餘大部份的時間,都在筆記電腦前寫作工作,「拋荒的故事」系列就是這時候的產物,第一篇「大崙的阿太和砂鼊」就是用「巢窟散文」的名稱在台文罔報發表。寫到第5篇「沿路尋找童年時」,當時跟阿仁在中廣電台做「尋找台灣」的雅玲建議在節目中唸讀播出,讓聽眾有機會從聲音感受台語文學之美。當時,每週由阿仁在節目中唸讀一篇「拋荒的故事」,雅玲負責為故事配背景音樂,以及和作者阿仁討論作品內涵和價值觀。就這樣開始很規律地,每個禮拜寫一篇,每天都維持生產差不多字數,每一篇故事的架構和字數也都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創造一種說故事又兼有散文詩氣味的文體。表面上雖是小說的形式,卻將人物對白的部份降低,盡量突出聽覺的效果,一方面適合廣播,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強調台語文學的特色。
阿仁寫《拋荒的故事》這個系列,在文體上,是很想為台語文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散文小說風格,有別於中文的文學語的表達方式,用口語式的書面語製造一種文學情境,專門寫境、寫情,讓口語也可以有美的境界,以此作地基,為台語文創造更多的書面語可以利用,建立我們自己的書面語文學。
在結構上,則是朝向以短篇連環故事構成長篇小說的形式,去再現台灣即將消失的那些人、那些事,最重要的是那些價值觀。所以,《拋荒的故事》分開看是一篇一篇各自獨立的散文故事,不過,如果把它們合起來看,可以發現當中有一些若有似無的牽連。首先,故事的場景大部份都是作者阿仁的故鄉彰化二林,所描述的景象都是五、六○年代台灣農村社會熟悉的事物與情節,包括鄉下的人情世故、風俗習慣、農村光景及漸漸消失去的傳統產業,譬如:竹筒厝、乞丐的行頭、訂婚的禮數、尪姨收驚、照相、生活情趣、牛車、腳踏車、vespa...等等;對於傳統行業的細節有非常精細地描述,像「修指甲的」這個行業使用的器具、修指甲的過程,不但是一種歷史的記錄,描述本身就具有文學的趣味。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大部份是台灣社會底層的人物,有乞丐、農夫農婦、漁夫、街市各行業的小百姓…等等,這些人物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都一定是講台語,用台語稱呼每一項事物,描述情景,及表達感情。將這些元素集合起來,正好就是五、六○年代台灣農村社會的原始面貌,台灣人的生存圖像,那個時代、社會的縮影。這樣的圖像不但提供今日讀者懷舊的情趣,也提供我們重新思考臺灣人尊嚴與價值觀的歷史素材。所以,把寄託那個時代的語言與文化的《拋荒的故事》看成是另類形式的台灣歷史大河小說也不為過。
三、用拋荒的故事再現台灣「殖民前的在地文化價值觀」
台灣歷史最大的特徵是---她是一個被多重殖民的移墾社會。
一個被殖民的民族,最大的悲哀是---沒有自信,每件事情都習慣用殖民者的價值觀做標準,自己不敢做選擇、下判斷。好不容易,殖民體制結束了,甚至殖民者離開殖民地,那些被殖民的悲哀卻不會跟著殖民者離開,而是繼續殘存在人民心中及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甚至成為殖民遺孽反撲、復辟的因子。因此,原本被殖民的民族,在後殖民時代首要的文化工程就是---找回我族的價值觀與做主人的自信。
前面說過,阿仁很年輕的時候就體認到台灣人被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長期蹧躂的悲哀,又認為生命是無奈、苦澀的,心靈與肉體的苦澀只有透過文學才能獲得解放,因此,他做文學家的初衷,就是立志要讓台灣人從統治者的苦難中獲得解放。他決志投入台語文運動,表面上是要復振台灣人的母語,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希望透過文學活動,鼓舞台灣人,將我們自己的價值觀找回來,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台灣人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解放。我們可以把《拋荒的故事》系列看成是阿仁這種文學觀的具體實踐,希望以文學承載母語,用故事再現台灣「殖民前的在地文化價值觀」。
台灣農村社會曾經發展出自己的價值,但是當社會結構、經濟環境、生活條件都改變後,價值觀(像婚姻觀、土地觀、金錢觀、道德觀、宗教觀……)自然跟著改變,甚至消失了,農業社會的老人們,因為語言的限制,無法接受現代社會的價值觀,以致他們的價值觀在現今社會環境中,常常變成笑話。在寫《拋荒的故事》系列作品之前,阿仁就曾經寫過一齣舞台劇〈老歲仔人〉,呈現這種荒謬的現象,例如:坐車要坐慢車,省錢又可以坐很久當成觀光旅遊;同樣是拔牙,付同樣的價錢,要拔久一點比較合算。這種現代都市人認為不可思議的價值觀,其實就是阿仁要說的「拋荒」的價值觀。
價值觀是相對的、經過比較的,不是絕對的,在那個荒蕪的時代,物資欠缺、生活困難,很多情況是我們今天很難想像得到的,也因此讓很多遙遠的價值觀在今天會產生距離的美感。阿仁很能掌握這種因為時空變換所產生的戲劇張力,所寫的每一篇拋荒的故事都是從現代話題開其端,才導入一個50、60年代台灣農業社會的故事,透過不同時代的故事,讓我們感受到時代社會的變遷,比較不同時代的台灣人所堅持的價值觀有什麼差異?思考臺灣人的心靈與精神面貌有什麼改變?進一步思考當時代改變後,有什麼價值是值得我們保留的?還有什麼價值觀是需要改革的?而寄託這些價值觀的人物是講台語的,自然必須要用台語才能記錄下那些故事。
過去,我們凡事都會捧出中國讀書人那套儒家傳統的生活準則與態度,老一輩的人連講一句母語,都會覺得粗俗、羞恥,從來都不曾認真去尊重他們的想法與做法,更不可能會去思考他們的生活價值觀。《拋荒的故事》系列創作,重現了那個已經消失的年代、那個被改變了的社會文化價值觀,更重要的是,同時也保存了幾乎要消失的那個年代的母語。阿仁想要達到兩項效果:一、重新找回台灣人的舊價值,擺脫腐朽的中國封建文化;二、重溫台灣人母語的趣味與智慧,發現生動的母語敘事模式。所以,《拋荒的故事》在那些浪漫懷舊、荒謬有趣的故事中,阿仁其實是暗藏了後殖民台灣文化改造工程的企圖。
《拋荒的故事》中「拋荒」,華語翻成「荒蕪」會比較貼切,仔細思量,它可以有很多重的意義;一方面代表「貧乏」,那是一個物資貧乏、生活艱苦的時代,一方面表示「遺忘」,抗議那個時代已經漸漸被台灣人給遺忘了,很多百姓的生活從未被書寫出來而拋荒。農民把有田不耕作放任雜草叢生叫做「拋荒」;台語歌「思念故鄉」裡面有一句歌詞說「為何愛情會拋荒」,把田園耕作拿來比喻愛情的經營,就像土地田園久不耕作,就會荒蕪;愛情如果疏於經營也會疏離。
阿仁是天生的詩人,很喜歡把具體的用詞意念化的文字技巧,「拋荒」的意涵,就被阿仁從農村土地耕作的意象發展出來,引用到台語文學寫作來。台語文本來講的都是具體、寫實的,如果要提升作文學用語,必須從具體用語提煉出一些書面語詞,於是就用這種概念開發另外一種母語文學的寫作風格。用文學的角度來看,《拋荒的故事》所敘述的是鄉下耕作方式的拋荒、台灣過往善良民風的拋荒、工業化帶來的污染土地無法復育的拋荒以及母語消失的拋荒,總體來看,它是描繪出一幅回不去的農村社會風貌、心靈底層的記憶與永遠的故鄉。
總之,阿仁在中年之後,回想故鄉、兒時點滴,希望從寫作中找回那些被揚棄的本地傳統價值,提供現代社會思考,企圖從記憶瑣事中,進行更深的文化內涵的挖掘與詮釋,建構被殖民統治者扭曲的價值觀。
四、懷念平埔族的母系社會,翻轉漢人社會的父權價值觀
《拋荒的故事》這次重新出版,經過分類,每一輯呈現不同的主題。
第一輯「田庄傳奇紀事」,收錄了〈地理囡仔先〉、〈新婦仔變尪姨〉、〈改運的故事〉、〈大崙的阿太佮砂鼊〉、〈指甲花〉、〈牽尪姨〉等6篇,記錄了50、60年代台灣庄腳社會情景。這6篇都屬於「鄉野傳奇」,有民俗、宗教、傳奇的趣味,主要的話題放在台灣平埔族的母系社會的傳奇故事與價值觀。
阿仁生長的背景是一個閉塞偏僻的農村,一個已經在現代社會消失的農村平埔族社會,這個社會的價值觀與漢人社會是格格不入的。兒時的平埔族農村經歷是他寫作最大的養分,這些經歷不僅提供他故事題材,更挑戰他的思維,挑戰漢人社會的價值觀,例如:「揖仔伯」訂婚之後才得知未婚妻懷有他人的小孩,居然不以為忤,還樂得賺到一個兒子,這種反漢人的貞操觀念,阿仁稱之為「古典的價值觀」,是他很迫切想要去探究的一種「殖民前的在地文化價值觀」。因此,阿仁選擇書寫五、六O年代的台灣農村社會,不僅因為它很有趣,更大的原因應該是他想要為一個消逝的族群立下墓誌銘,也為這個傳統價值觀消失的社會提出警訊。
阿仁用「尪姨」這個職業串聯4個故事:〈新婦仔變尪姨〉、〈大崙的阿太佮砂鼊〉、〈指甲花〉、〈牽尪姨〉。
根據林媽利的研究,台灣人有超過85%的人有平埔族的血液基因,台灣原來就是一個道地的平埔族母系社會,早期的民間信仰也大部份屬平埔族的信仰,〈大崙的阿太佮砂鼊〉裡面的主角回想他「做gín-á 的時代,góan 庄--nih無廟,連土地公廟仔都才 1 間á-kiá° niâ,庄內無人leh 做童乩,顛倒是平埔留--落-來的尪姨人khah知影」,那篇故事主角的阿太就是平埔族的尪姨。
〈新婦仔變尪姨〉是講一個叫「缺(khoeh)--á」的人變成尪姨的故事。
「新婦仔」是去領養別人家的女兒,等到適婚年齡再和自己的兒子結婚。傳統上「飼查某子別人的,飼新婦仔做大家」的觀念中,總認為女孩子辛苦養大也是別人家的媳婦,不如自己抱個新婦仔回來養比較實在。大部分的新婦仔都是因為窮人家無力養,為了女兒能得到更好的生活、減輕家庭重擔的心理,父母必須割捨兒女親情。〈新婦仔變尪姨〉提到:「古早t„拋荒的時代,物資欠缺,生活困難,飼1個gín-á大hàn
ài khai真chë,cha-p¬ gín-á大hàn會tàng留t„厝--nih tàu趁,飼kiá°所khai ê費用算投資,cha-b¯ kiá°大hàn ài嫁去別人tau,若無換1kóa聘金t¡g--來,就加了番藷á米--ê。有kóa人根本無châi-tiäu kä cha-b¯ kiá°飼gah大,就先kä送人做「新婦á」,h⊃3;未來ê ta-ke
koa°先飼。…做人ê新婦á講khah白--leh就是換3頓飽的cha-b¯長工。」新婦仔被領養後,若夫家運勢順利,通常會認為是新婦仔帶來好運而倍受關愛;若是相反,則會受到「新婦á精」、「新婦á體」、「新婦á栽」等惡毒的責備,新婦仔的日子就會變得非常辛苦、不好過。
但是阿仁在〈新婦仔變尪姨〉中,塑造一個變作尪姨的「新婦á」,缺仔八歲時被送去作「媳婦á」,缺仔從小常常會一個人自言自語,好像在跟別人講話,問她是跟誰講話,她有時候回答,是在跟祖先講話。村裡的人說她有陰陽眼,是個通靈人,又兼有預言的本事,後來無論是田園買賣,男女嫁娶,大家都會來拜託缺仔先將祖先叫出來問一下。一直到缺仔20歲,主人要將她完婚之前,缺仔變成「落跑新娘」逃走了。後來缺仔向養父母道歉,說她無論如何
都不能跟那個小她5歲的弟弟結婚,而且她事先有感應,這個婚姻會給家裡帶來不幸,因此她才會逃走。後來家裡的人都原諒她,她就變成一位農村會通靈兼收驚的尪姨。
在傳統觀念上,「新婦仔」原是一種苦命的代表,阿仁卻以「新婦仔變尪姨」這種不一樣的「新婦仔」發展,來突破這種刻板的觀念,表示傳統台灣人也有疼惜「新婦仔」的好人家。
〈牽尪姨〉為〈新婦仔變尪姨〉故事的延續,描述「缺(khoeh)--á」當了尪姨之後,把通靈的工作傳給「A-chiáng」,而「A-chiáng」是〈指甲花〉的主角。另一方面,〈牽尪姨〉也可以說是〈指甲花〉故事的續集,描述「勇--á」娶了「A-chiáng」之後,「A-chiáng」因為懷念那個跟她無緣的、在結婚前因車禍死去的農會職員,去找「缺(khoeh)--á」牽亡魂,後來卻真的變成了「尪姨」。
〈指甲花〉是描述一個「鄉村美容師」的故事。故事的主角A-chiang是在農村裡幫人修指甲、擦指甲油的專業美容師,跟一般農婦比較起來,應該有更好的歸宿,無奈「紅顏薄命」,眼看就要嫁給一個不錯的對象---騎vespa機車的農會職員,男方卻在結婚前因車禍過世,好姻緣破碎。三年後,回頭嫁給原來自己沒有選擇的一個農夫阿勇。
〈牽尪姨〉中的主角A-chiang雖然嫁給一個不是自己最理想的對象,但是她並沒有妥協,而是用巧妙的手段,維持了女性的主導權,選擇接續缺仔「尪姨」的職缺。雖然到了故事中的年代,母系社會的女權已經式微,但是,阿仁仍然借機會突現平埔族母系社會的價值觀。
〈大崙的阿太佮砂鼊〉是用主角的阿太托夢抾骨的方式傳達往生者冤親債主的意願,表達台灣人惜福的環保觀念。透過民間傳說、神話傳奇增加故事的神祕性與趣味性,順便介紹早期台灣農村社會「尪姨」這種服務業。
阿仁在故事中借機拿傳統與現代做比較,提出自己對尪姨的看法。站在現代醫學的觀點,收驚可以算是一種精神安慰療法,把它歸屬醫師公會,也不無道理。把「通靈人」比喻作後現代資訊業的觀點,認為是現代科技都無法達到的前衛行業,帶來幽默的效果,也帶來一種「肯定傳統方法」的價值判斷。現代科技雖然進步,「通靈」與「收驚」兩種行業仍然可以並行存在,表示傳統民俗方法還是有它的社會功能在。
此外,這篇故事還有個很嚴肅的主題是在講,平埔族與漢人、基督教與傳統民間信仰兩種文化的差異以及共存的經驗。小說是用魔幻寫實的手法來書寫,製造一種「你無法肯定他是假,也不能證明他是真」的效果。探究平埔族尪姨透過玄孫找到阿太深埋百年的怨懟,也在基督教和本地信仰中找到平衡點,誠懇透露身為平埔族後裔的惶恐與驕傲。另外,這篇作品對故鄉景物的描寫,投入深情,是一篇足為經典的自然書寫。
五、改運與風水的命運觀
在這6篇鄉野傳奇中,除了4篇在講「尪姨」外,其他2篇〈地理囡仔先〉、、〈改運的故事〉就是在討論另一個主題---「命運觀」。
在傳統民間的價值觀裡面,命運是上天意志的安排,台灣俗語說:「運命天註定」,人一生下來,每一個人都有他不同的命格,一切生死、禍福、苦樂、貧賤、富貴,上天都已經決安排好了。「命」是一種人力無法度對抗的定數,人受到一種神秘力量的牽引,無可奈何,只有自覺生命渺小,生存機會受到限制。「運」則是指一種動態的時間之流、機緣或是機會:
運kap命無käng款,運是1時,命是根本,1世人ê經歷。命運是講1時ê氣運,運命是1世人ê命底生成。命若bái,講真oh解,運若bái,暫時會sái khah忍耐,˜-koh mä有khah無耐性--ê,kui-khì就想辦法改運。(〈改運ê 故事〉)
這種「運」的價值觀,加上天理報應的因果信仰,相信人可以借由修善修福,累積陰德,在天的庇蔭下,利人又利己,改造自身的命運,或是得到更多的機運與好運。命相學等等神秘理論的流行,培養出一種民間生命宗教觀,影響到民眾的生活價值認知。比如〈改運的故事〉中,自從阿川的爸爸發生車禍後,他的母親開始相信命運,就想出各種辦法要改運,無論什麼神明、看面相、安太歲都去作。阿川被懷疑偷錢以後,他媽媽還是相信自己的兒子,只是不甘願命運這麼差,又去請法師來改運,這個法師說需要用改運的人的衣服,蓋在他的法器上,再將金子放在底下,七七四十九天以後,就可以改運。他媽媽照作,想要改阿川的運,結果那個法師沒有再出現過,金子就被他給偷天換日掉了。
命運是面對變化的人生,一種很奇妙的解答方式。當台灣人在理性世界找不到答案;或是對不合理的事件,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時,就都把它歸到「命」。例如:〈指甲花〉的主角A-chiá¤g在下聘一個月後,那個新郎卻騎機車跟一台貨車相撞,還不到醫院就斷氣了。A-chiáng自己在屋裡哭了好幾天。那個男的要出殯的時候,她穿那一套原本做新娘才要穿的衣服,擦紅指甲花,跟無緣的公公要求要用「未亡人」的身份送上山頭,公婆都不肯。後來聽說是對方牽拖A-chiáng的命太硬去剋到他兒子,才會連兒子死後都不讓她入門,可見台灣人碰到不好的事情時很容易相信命運。
比起〈改運的故事〉中講的人本身的生辰八字決定生死禍福,〈地理囡仔先〉講外在自然空間與個人禍福的關連,要更為玄虛。
陽宅風水稱作「地理」,陰宅風水則稱作「風水」。「地理」是人居住的環境、生存空間、自然生態環境與陽宅風水的宗教觀。這種宗教觀結合神秘理論的信仰觀,認為「地理」會影響人存在的情境與事象。這種「地理」觀,其實是功利心態作祟,想藉著改造「地理」,祈求富貴或是生活順遂。
「地理風水」原本是一種具有理性思維的平衡概念,只是冠上神秘色彩後,加上民眾「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理,就會形成一種盲目的追求與崇拜。阿仁在〈地理囡仔先〉故事中對這種神秘理論是有提出懷疑的:「若福氣的人就有福運,無福的人占好位mā無效,án-ni看風水、地理有siáⁿ意義?」
借「風水」祈求祖先庇蔭,原本是人之常情,但是過度相信「風水」會給人富貴或子孫興旺,則是一種瘋狂的行為。「穿山龍,萬世窮」就是在譴責風水師如果為了賺錢,要人時常遷葬墓地,是一種敗德的職業,會遭天譴並會禍延子孫,永遠不得翻身。但〈地理囡仔先〉裡面風水師自己解釋是因為「洩漏天機」才受天譴。
〈地理囡仔先〉的主角阿龍是一個風水地理師傅的小孩,因此在日常行為與談話中間都用風水地理師的眼光來看事物,有趣的是,風水原是屬迷信的事物,阿龍卻有一顆理性思考的頭腦。阿仁想借這個故事諷刺風水的「迷信」,因為阿龍的父親教他如果遇到難回答的問題,就回答:「天機不可洩漏!」。有一次,又講到寶斗剪刀穴的故事,當里長問到,如果寶斗的風水那麼好,怎麼會比田中更沒有發展?阿龍的爸爸說:「雖bóng寶斗比人khah無鬧熱,˜-koh
mä為著無鐵支路的交通利便,khah無大工廠來thún,保持khah好的環境,寶斗人生活了khah清氣、sù-s„,˜是講鬧熱、發達就上好-ah。」居然是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思考,清新的環境確實比工商繁榮更重要,一方面是顯示風水師父的見風轉舵,另方面阿仁也要借機說明,風水地理如果能夠從理性科學的角度分析,一定可以找到理性與迷信的平衡點。
六、用母語喚回拋荒的價值,再見台灣文學的青春
文夏〈流浪之歌〉的第二拍歌詞說「啼哭也不回來/青春彼當時/目屎若會流落/叫阮要怎樣」。對我與阿仁這一個年代的人來說,台灣50、60年代的光景如同哭不回來的青春,讀《拋荒的故事》所描述的每一個情節畫面,就如同在呼喚我們的青春。阿仁還趕得上見證那個殘留台灣平埔族母系社會價值觀的農村景象,而且用幾近於留聲機真實的母語為我們記錄下來,把她放在台灣文學史上來看,更是珍貴,因為世紀之交這些年裡,當主流文壇只剩都會型的漢語文學時,我們慶幸《拋荒的故事》還看得到、聽得到「台灣」。
《拋荒的故事》展現了台語文學的特色,不僅真實記錄了台灣人的生活面貌、文化價值,也保存了台灣人的母語心聲請愛台灣的人們,不要再說我們台語文學者是不倫不類,不要再說台語文學「只有語言,沒有文學」。
相隔12年,看到《拋荒的故事》以這麼盛大的面貌重新出版,內心不由得有些波動,浮出一連串的省思:台語文運動進步到什麼階段?台灣文學發展到什麼情形?台灣歷史走到什麼地步?《拋荒的故事》這本書放在這樣的脈絡裡又是居於什麼位置?
《拋荒的故事》的重新出版至少見證了堅持用台語創作文學這件事情是對的。我們沒有傻傻地等那些語言文字學家研究確定一套文字,就大膽地進行文學創作也是對的。
《拋荒的故事》這次重新以紙本與CD有聲書的方式出版,是要讓台灣人的文學能夠以立體、多元的形式傳播出去。所以,讀者可以用任何的方式來親近台語文學。在此,誠懇建議大家將《拋荒的故事》當做文學讀物、台灣文化知識、散文範本、廣播節目、台語口語教材......,不管哪一種用途,都可以喚回那已經拋荒的價值,再見台灣文學傳統的青春。
廖瑞銘/前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