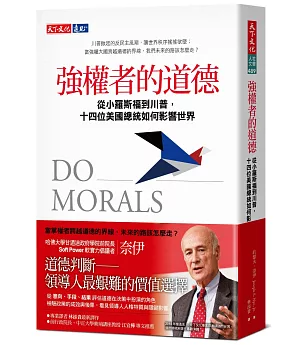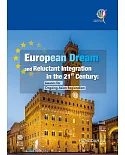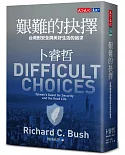前言
和一群友人聚餐時,有人問起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我正在寫一本有關總統、道德和外交政策的書,她笑說,那一定不會太長。另一位朋友則比較嚴肅地說:「我不以為倫理道德有多大的作用。」這種一般見解不僅充斥在餐桌上的討論,也充斥在政治分析之中。在網路上搜尋,意外發現沒有太多書籍討論總統的道德觀點如何影響他們的外交政策,以及這如何影響大眾對他們的評斷。華爾澤(Michael
Walzer)是個重要的例外人士,他形容一九四五年以後美國研究院的訓練為:「雖然有少數作家捍衛利益是一種新道德,但是道德論證仍與通常所遵循的學科規則背道而馳。」針對美國三大國際關係重要期刊過去十五年的文章進行調查,發現涉及此一主題的文章只有四篇。有位作者指出:「重量級學者……並未認真注意,研究道德價值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對年輕的學者而言,它不是有助於專業晉升的主題,但對於我這樣一個從事實務工作、又鑽研美國外交政策多年的學術工作者而言,它長久以來一直吸引著我。
對許多人而言,懷疑的理由很明顯。固然歷史學者大書特書美國例外論和道德主義,像肯楠(George
Kennan)這些外交官和理論派,早就對美國重道德、講法理的傳統帶來的惡劣結果提出警告。國際關係是一片無政府之地,沒有一個世界政府提供秩序。各個國家必須自力捍衛,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時,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在毫無有意義的選擇之下,就不會有倫理道德可言。哲學家說:「應該,意謂著可以。」沒有人會因為你沒去做不可能的事而責備你。本於此一邏輯,把倫理道德和外交政策結合在一起,是一種歸類錯誤,彷彿問刀好不好而不問它是否切得利,或是問掃把能否舞動而不是它能否掃地。本於這個邏輯,在評斷一個總統的外交政策時,我們應該只問它是否奏效,而不是也問它是否合乎道德。
這個觀點固然有理,它卻過分簡化、回避了艱巨的問題。沒有世界政府並不代表完全沒有秩序。某些外交政策涉及到我們國家的生存,但是大多數外交政策則不然。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介入好幾次戰爭,但沒有一次是出自我們生存所必需。而且許多涉及到人權、氣候變遷或網際網路自由的重要外交政策選擇,根本沒有涉及到戰爭。大多數外交政策議題涉及到多項價值的權衡取捨,需要做出選擇,並不是僵硬地採用「國家利益」(raison
d’etat)的公式。有位激憤的法國官員曾經告訴我:「只要合乎法國的利益,就是我所界定的好。與道德毫不相干。」他似乎沒有察覺,他這句話就是一種道德評斷。再談所有的國家都試圖基於其國家利益行動,根本就是多此一舉的廢話。重要的問題是,領導人在不同情境下如何選擇去界定和追求國家利益。
猶有甚者,不論我們是否喜歡,美國人不斷地對歷任總統及外交政策做出道德評斷。川普政府上台,使得各界重新點燃何謂道德的外交政策之興趣,把它從理論上的問題提升到新聞頭版版面。譬如,沙烏地阿拉伯異議份子、記者哈紹吉(Jamal
Khashoggi)於二○一八年在沙烏地駐伊斯坦堡領事館被殺害之後,川普總統被批評為對殘酷罪行的明顯證據視若無睹,以便與沙烏地王儲維持良好關係。自由派指責川普有關哈紹吉遇害的聲明是「無情的交易,罔顧事實」。保守派也發表社論批評:「我們知道,沒有一位總統——即使像尼克森或詹森這樣冷酷的務實主義者——會寫出這樣的公開聲明,完全不顧美國遵守的價值和原則。」取得石油資源、販售軍火武器,以及區域穩定,都是國家利益,但是吸引別人的價值和原則也是國家利益。它們要如何結合在一起呢?
不幸的是,許多關於倫理道德和外交政策的評斷都是隨興而發,並未經過深思熟慮,而且目前的論辯太過集中於川普的性格。觀察敏銳的資深記者哈珀曼(Maggie
Haberman)曾對我表示:「川普並不獨特,他只是過於極端。」當我們檢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有美國總統的紀錄時,就會發現,他所採取的某些行動並非沒有先例。甚至更重要的是,美國人很少搞清楚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標準去評斷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我們讚揚雷根(Ronald
Reagan)這樣的總統,認為他的發言具道德上的明確性,彷彿言詞上的善良意圖就足以做出道德的評斷。然而,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小布希(George W.
Bush)兩位總統卻顯示出,徒有善良的意圖,卻沒有妥當的方法去達成它們,將導致道德上的不良後果,譬如威爾遜在《凡爾賽條約》上,或是小布希進軍伊拉克,結果都淪於失敗。或者說,讓我們單純就結果來評斷一位總統。有些觀察家讚揚尼克森(Richard Nixon)結束越戰,但是他犧牲了兩萬一千名美軍士兵的性命,來創造一個聲譽不錯的「體面的間隔」(decent
interval),最後卻證明它是走向失敗之路的暫停。
我在下面會提出論據,善良的道德推理,應該有三個面向:權衡總統決策的意圖、手段與結果。道德的外交政策不是意圖和結果相互對比的一樁事,而是必須涉及到這兩者,以及我們所使用的方法。甚且,良好的道德推理必須考量到一般行動的後果,譬如維持體制性的秩序,鼓勵道德利益,以及特別有新聞價值的行動,如協助在其他國家的人權異議份子或遭受迫害的團體。還有一點很重要,必須包括「不作為」的道德結果,譬如杜魯門總統在韓戰期間願意接受戰局僵持和國內政治挫敗,不肯接受麥克阿瑟將軍動用核子武器的建議。福爾摩斯有句名言:從一隻不叫的狗身上,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本書不是歷史書。我沒有刻意求全、求完整,或是舉出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歷任總統外交政策道德面向的一切文獻來源。我也沒有試圖涵蓋前幾世紀的美國外交政策。我在本書只是提出規範性的思考,運用到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時期——這是美國居於世界最強大國家的時期,有時被稱為大美盛世(Pax Americana),或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許多評論家臆測這個時期即將終結,需要有新的外交政策來迎接新挑戰,這我將在最後一章提到。在辯論這些政策時,倫理道德將是我們會採用的論據之一。假裝倫理道德沒有任何作用,就和認為太陽明天不會升起一樣盲目。由於我們將對外交政策採用道德推理,我們應該學習做得更好。這本書分析和開發出來的計分卡,是朝這個方向邁進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