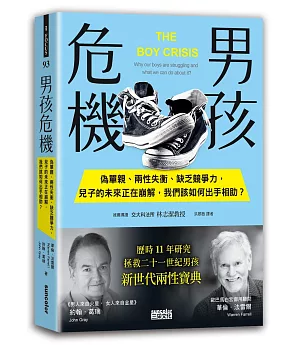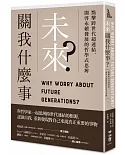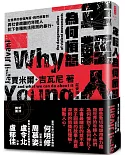作者序
什麼是「男孩危機」?
在一場氣氛活絡的聚會上, 在場者有政府官員、企業老闆、作家及柏克萊加大的教授(3 位男士、3 位女士,其中2 位是立場強烈的女權主義者),主人之一的作家山姆.金恩(Sam Keen)問:「如果能重新投胎,你會選擇當男生還是女生?」
所有男士都回答:「女生。」另一場晚宴上,好友的女兒梅莉莎告訴妻子莉茲和我懷孕的消息。我問她丈夫安迪,如果生了兒子最期待什麼。安迪雙眼發亮地說:「我要把他舉高高;等他長大,要帶他玩、踢球。小時候我爸都會故意放水讓我得分。如果可以,我也想為兒子這麼做。」當晚稍後我又問他:「你比較喜歡男生還是女生?」他以認真的語氣回答:「我選女生。現在的女生想做什麼都可以,男生卻不行。我也擔心男生書讀不好或是沉溺於電玩。」
女生當然得面對各種內在與外在的文化偏見。但令我驚訝的是,即使安迪想像和兒子一起玩耍的畫面如此明確,他渴望孩子擁有美好未來的欲望,卻壓過這些想像,最後選擇想要女兒。
過往,多數爸爸都希望先生兒子,現在已經不再如此。安迪心裡的「父親本能」—希望孩子過得好勝過他自己想要的東西—正是現在多數爸爸的寫照:準爸爸想要女兒的比例,幾乎是想要兒子的2 倍。
至於準媽媽,她們想要先生女兒的比例,比想要先生兒子高出24%。以前,大家都認為女兒比兒子更有可能在成年後與父母同住,但現在此景不再:25 ∼ 31 歲的年輕男性與父母同住的可能性,比同齡女性高了66%。
凱文的爸爸威廉告訴我:「凱文在他30 歲生日派對不久後就搬回來了,我覺得自己是個『失敗的爸爸』,這個想法一直困擾我。」
凱文則有另一件事煩惱:「我和一個女生在派對上看上眼,我想邀她續攤,但總不能回我爸媽家吧。後來她提議想換個地方,很挑逗地對我說:去你家吧?你住附近嗎?」
「我說我和爸媽住一起。原本我是想問她有沒有適合的地方,但我發現她僵住了。她找了個藉口說去化妝室後就回到朋友身邊,兩人偷瞄著我笑。我人生中從未感到如此羞辱過。」
另一個不同於凱文的活潑男孩,也同樣有著敏感及羞愧的共通點。在比爾.寇司比(Bill Cosby)、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等名人醜聞風暴的影響下,媒體每報導一個性騷擾犯、強暴犯或連續殺人犯的新聞,就讓一位敏感的男孩因為身為男性而感到羞愧。從羅伊斯.曼恩(Royce
Mann)在2017年為「孕育」(HATCH)—以「孕育創意」為宗旨的全球性社團—朗誦的散文詩,可以感受到15 歲的他承受的羞愧感:
我變成男人了。第一次有女子在路上閃過我,這位離我3公尺遠的女性回頭看我一眼便立刻改變方向走到對街⋯⋯她的腳步聲讓我明白我雙手的危險,讓我明白身為男人真正的意義,或許我永遠無法了解她為何要懼怕男人。但在那一刻,我終於明白彼得.潘的感受—想當個男孩,永遠都不要成為男人;因為,作為男人便是父親、兄弟、攻擊者的綜合體,但主要是後者。
羅伊斯感受到的愧疚感,讓他明白「自己的危險性」;大眾對於男性的恐懼,讓他下了個結論「我想永遠當個男孩」—最好能像彼得.潘那樣—因為男人是「攻擊者」。
所幸,羅伊斯不太可能成為性罪犯。在他的發言中,始終未提到自己多想將男性的優點部分貢獻給家人、奉獻給全世界;但是被當成攻擊者所引發的罪惡感,限制住了他。
無論你的兒子像凱文還是羅伊斯,這就是現今男孩生長的時代。《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曾有一篇文章〈男人末日〉(The End of Men),因為讀者的熱烈反應而出版成書—你能想像在女兒的成長過程中,有人預言「女人末日」(The End of
Women)嗎?過往,從來沒有這種預言自己的性別將步向末日的言論出現;但前述「男人末日」的預言,對兒子的人生可沒什麼重要啟發。
現今男孩遇到的情況真的就是危機嗎?或者,只是因為女孩的表現越來越好,男孩卻在原地踏步?我將提出諸多男孩在各種重要領域都走下坡的證明。男性每況愈下的情況,也將傷害所有女孩、婚姻、他們的小孩和全球的安全。
多數人對這問題都視而不見。2017 年9 月16 日,我在谷歌(Google)上以「男孩危機」(boy crisis)為關鍵字搜尋,搜尋結果一半是和樂團「男孩危機」有關;而搜尋文化上的男孩危機,有一半的文章都斥為迷思。
了解男孩危機這個問題,對心理絕對有益。假如你覺得兒子成了「賴家王老五」,你可能會像威廉那樣覺得自己是失敗的家長;但當你了解這現象是所有已開發國家正面臨的問題時,你會知道這不是你的錯,我們可以做些事避免兒子捲入危機中,幫助他將危機化為轉機。
我與男孩危機
1970 年代,女權運動領袖被冠上燒胸罩的人(bra burners)、醜八怪(ugly)、男人婆同性戀(dykes)、厭男者(men-haters)等稱號。我曾請羅格斯(Rutgers)大學的學生玩角色扮演,「親身體驗」女權運動領袖的角色,其他學生則扮演沉默的大眾或辱罵叫囂的人。在他們完全投入其中後,我要求他們角色互換。
學生的熱情回應,讓我因此修改博士論文方向,聚焦在女權運動上。紐約市的全國婦女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聽聞此事後,邀我成立「男性自覺團體」(men's 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s)—一個滲入女權主義者的男性團體。我獲選為全國婦女組織的董事會成員,在世界各地為女權主義者發聲,成立上百個男性與女性的支持團體。
70 年代末,離婚率大幅上升,我注意到許多離婚家庭的孩子都是與媽媽同住。爸爸的文化模因(cultural meme)都著重在他賺的錢,而非他對孩子的愛;當爸爸沒有支付贍養費時,就會被說是「賴帳者」。原本我也接受這樣的文化模因,直到我親耳聽到離婚爸爸的心聲。
他們為在家事法庭中遭到的不平等對待憤怒,對法條字字計較。但當我問起孩子的情況,爸爸們的眼淚奪眶而出。憤怒只是掩飾脆弱的面具,用來遮掩「探訪、監護權」這類讓他們覺得自己像個二等公民的用詞,也因為兩週才能見到孩子一次,爸爸們覺得自己的努力在每次探訪結束後化為烏有。
我看到好些爸爸一路墜入人生低谷;也有爸爸拚命賺錢支付訴訟費用,好讓自己能平等地參與孩子的生活。有些爸爸負擔不起打官司的錢;有些爸爸努力賺錢,最後卻沒時間陪伴子女。
與此同時,我在小學任教的姊妺蓋兒告訴我,很多成績突然一落千丈的學生,原因就是爸媽正在談離婚。
1986 年《為什麼男人應該是這個樣子?》(Why Men Are the Way they Are)出版,各國語文版本的問市,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爸爸向我傾訴這些挫折感與無奈。經歷70
年代早期離婚潮的孩子,現在已是上高中的年紀。在我的講座會後,眼中滿是失望的家長向我吐露,孩子遇上的挑戰讓他們深感悲傷。然而,身為研究者和女權主義者,我想知道這些問題是因為爸媽離婚、沒有父親陪伴或是其他原因所導致,這份研究最終收錄在我於2001 年出版的《父子重聚》(Father and Child
Reunion)。研究發現,沒有父親的陪伴是導致這些孩子遇到社會、學業、身心健康等問題的主因。
這份研究明確指出,不論男孩或女孩,父親缺席都會有影響。在我撰寫本書時,情況更明顯,父親不在身邊對男孩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大,傷害延續的時間也更長。原因是,離婚在高度開發國家是很普遍的事,女權運動為女孩打了強心針,但是卻沒有人為兒子這麼做。女兒們在經歷目標增長(育兒、賺錢或兩者都要)的同時,兒子卻感受到「目標感的失落」(purpose void)。
我越是深入發現男孩為何會如此,越是明白為何沒有爸爸在旁引導的男孩,會大大落後有爸爸陪伴的男孩。
簡單來說,我將「缺乏爸爸」(dad deprivation)和「目標感的失落」視為一種複合效應。
糟糕的是,我越來越常看到過往歷史的傳承—鼓勵男孩要當英雄的「英雄觀」(heroic intelligence),與維持身心健康的「健康觀」(healthy intelligence)正好大大衝突。想想對著球場上男孩大喊「衝啊!」的家長、啦啦隊,他們完全不覺得自己正把男孩推向腦震盪受傷的風險;等到男孩受傷時,大家又祝他早日康復「再上場奮戰吧!」準備迎接下一次的腦震盪。
在我開始尋找這些現象間的關聯時,我和莉茲搬到加州米爾谷(Mill Valley),遇見了《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男女大不同》(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的作者約翰.葛瑞(John Gray)。約翰和我一起健行超過400
趟了。約翰雖然以協助男女克服差異、建立同理心聞名,但他也致力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進行非醫學療法的研究,這種療法強調直接處理深層的病因。於是,我請約翰在Part 6 分享,提供家長與教育者新的解決之道:為了快速解決問題而使用藥物,可能帶來需要更多藥物解決的新問題。
2018 年4 月, 我接到來自白宮的電話。歐巴馬總統成立的白宮婦女暨女童委員會(White House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想邀我擔任顧問。我答應了,同時也反應別忘了成立白宮男性暨男童委員會(White House Council on Boys and Men),讓全國正視兒子正面臨的問題。
由於需要另外提案,我邀請國內多位專家組成多黨派聯盟,擬定提案。我們花了18 個月的時間辯論、整合各家觀點。雖然歐巴馬總統和川普總統都沒有成立男性暨男童委員會,但聯盟內的討論讓我接觸到許多男性相關議題。
接下來的9 年,我也將焦點從政府能做的事,轉移到家長、老師、社區能做的事上。當我在進行多黨派聯盟的提案時,我得考慮到每個人的感受;但我相信讀者應該會希望在書中看到我直言不諱、直指問題核心。我希望你閱讀本書,是要看清現實的生活、真實的問題。有些問題可能很棘手,但若不尋找解決之道,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無助感。
本書所提的每個問題,我都會提供解決方法,讓你能依個人需要調整。現代家庭在養育孩子時,都面臨了比以往更錯綜複雜的問題,但我們可以利用每週一或兩次的「家庭晚餐」(family dinner
night),為男孩提供解決之道。只是如果沒做好,很容易就變成噩夢。舉例來說,在同理兒子和希望他同理你之間取得平衡,不僅是藝術,也是紀律。這兩種面向都列在〈附錄:男孩危機清單:有爸爸陪伴的好處與缺乏爸爸的危險〉中。在男性可能壓抑情緒的地方,我也做了特別提醒。
關於書中的「兒子」
我特別在書中使用「兒子」一詞讓讀者感受整個過程。
這個兒子指的是「所有人」的兒子。如果你是老師,便是指你的男學生;如果你正帶領一群男孩,那就是當中的每個男孩。
男性會需要這樣的「自助書」嗎?當然,商管書就是男性的「自助書」。這些書讓男性在職場上有更出色的表現。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職業婦女分擔家計,讓爸爸有機會專注在家務上。既然「男孩危機」也是爸爸的「公事」,本書就是爸爸的商管書。雖然本書聚焦在男孩身上,但我和約翰也同樣關注男孩危機對女性的影響。男人和女人或許來自不同的星球,但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奮鬥。兩性之間,沒有所謂輸贏;單一方的「勝利」,其實是兩性的失敗。
別說男孩危機與你無關,就算你尚未養兒育女,你也得辛苦工作、支付稅金,為男孩危機付出代價。舉例來說,伊斯蘭國(ISIS)招募的男孩,都是因為缺乏父愛而失去生活目標的人。
伊斯蘭國的壯大,意味著我們需要花更多錢在國土安全、網路戰、國防與照顧新退伍的軍人上,還有犯罪與監獄等費用,以及政府的社會福利計畫中,為了照顧喪夫家庭所支付的撫卹金。若將失業男性無法支付的稅收也算進去,光是在美國,每年就得負擔1 兆美元以上的金額。
這些直接花費還不包括心理上的代價,像是擔心孩子可能成為下一個校園槍擊案的受害者,因為這些槍擊案的凶手通常是缺乏父親陪伴的男性;或是擔憂兒子對父親的渴望,可能讓他成為性罪犯的下手對象。
一言以蔽之,這是一本為所有人而寫的書。
在上個世代,「技客」2(geek)很容易被嘲笑,父母會要孩子去練舉重、玩摔角,以避免被同學欺負,讓孩子在不自覺中產生「我不被接受」的感覺。然而,當時若能有一本書帶領大眾討論,幫助父母放眼未來,例如技客的豐富知識,將使他成為億萬富翁。他們便能幫助兒子抱持樂觀態度面對未來,啟發孩子的天分,而不是帶著羞恥感去練舉重。
未來不一定完美,但本書的目標是在針對女性未來挑戰的討論中,加入同等詳細的男性討論。本書將探索這場危機的主因,更提供家長、老師和決策者能採用的解決方案。
每個男孩都是獨一無二的,請先閱讀本書再決定是否應用在兒子身上,你也可以直接把書交給兒子,讓他自行探索;也可以給女兒,讓她帶著這份知識去愛人,用同理心以身作則。
華倫.法雷爾博士於加州米爾谷
2017 年11 月1 日
www.warrenfarrell.com
推薦序
齊家治國的雙槳齊划─為所有人而寫的《男孩危機》
回顧我46
歲的人生經歷,我雖然在美國取得博士,也在許多校園讀書、短期訪學過(杜克大學、哈佛大學、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但是影響我最深最遠的,其實是北一女中。我的性別意識與人生的理念,幾乎可以說是一女中的奠基。擘畫一女中教育和建立一女中學風的江學珠校長,把她對這一代女性的期許,都寫在校歌裡:唯我女校、寶島名高、莘莘學子、志氣凌霄、公誠勤毅、校訓孔昭、齊家治國、一肩雙挑。為國家盡至忠、為民族盡大孝,繼往開來、為我女界增光耀。
我在閱讀《男孩危機》這本書時,腦中一直不斷自動播放一女中校歌的旋律「齊家治國、一肩雙挑」。然後想著:在這個充滿未知的AI 世代,國與家,都需要更多的肩膀,如果要教導當代的男孩這樣一肩雙挑的觀念,我們該怎麼著手呢?
在《男孩危機》這一本書中,作者指出了一個造成男孩危機的關鍵:過往的男性,可以依靠體力與勞動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自信,如果家庭是一艘船,那就是男性與女性各划一邊—男性負責工作賺錢、女性則在內扮演輔助男性的持家責任。然而,全球化接著數位經濟與AI
世代到來,許多男性因為產業外移、工作被機器取代,而喪失工作優勢。相反的,女性在過去數十年,受惠於女權運動的興起,不斷被灌輸可以去挑戰各種過往專屬男性的領域的想法,而事實上除了因為玻璃天花板的限制,女力崛起的成果確實斐然。因此,現代男孩們所看到的家庭形象變成了:堅毅智慧的母親,左右開弓雙槳齊划,父親則侷限於一邊划船,甚至有時候連把這一邊划好都不見得做得到,因此,家庭的船隻是失衡的;更糟糕的是,社會文化和性別刻板印象不斷頌揚男性英雄主義,想像與現實的落差,讓男孩的成長充滿挫折和壓抑。
我一邊看一邊覺得,本書其實更適合由一位現代的父親來寫導讀和推薦序,因為作者所訴求的對象,其實更多在於男孩的父親們,簡直可說是一本當代父親生存指南,作者希望的是打造一個雙親都能雙槳齊划的家庭船。但既然出版社找了我,我就嘗試從性別與一個母親的觀點來分享一些看法。
以我自己成長的經驗,我不得不承認作者在書中的觀察有其道理。我是一個11 歲男孩的母親,也是一位女性主義研究者和高等教育工作者,我有許多男性與女性的學生們,且我從20 歲開始工作,在職場26 年,在我奮力打破玻璃天花板、努力進行各種法治革新的同時,性別的敏感度,也使得我特別能感受得到我的男性同儕、我的男性學生和我自己的孩子,在時代中找到新定位的困難。
作者所說的「放大的女孩與縮小的男孩」,確實呈現在學校教育中。我還記得數年前,有一次交大科法所甄試,錄取12 位學生,大家並沒有特別注意性別問題,最後結果出來,12 位連同備取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是女同學,當下本所差點改名為交大女子科技法律研究所。
男子氣概的英雄觀,讓男性們在成長中,對分享和求助是卻步的,男性容易假裝有自信但內裡十分不安,最後導致極端的情緒,或者爆發憤怒、或者抑鬱寡歡。如作者所分析的,社會以英雄傳說來收買男性的體力和健康,讓男性被綑綁於形象中,難以脫身,最後影響身心健康,並且喪失對他人甚至對自己同理的能力。這樣的結果是男性容易因為衝動而抑鬱,鑄成大錯無法挽回。作者觀察美國的多起槍擊案例,更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美國近十年來發生多次重大校園槍擊案件,死傷無數,而所有行為人,清一色是男性學生或年輕男性。許多關於男性與暴力問題的統計數據,也呼應作者的觀察。
我所尊敬的女性主義政治學者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指出,當所謂「好的、成功的男性」被定位為「有能的保護者」時,女性也被套到刻板印象的位置—所謂好的、成功的女性,就是擁有一個保護她的男性,並對其忠貞和順從;反之,一個不好的、失敗的女性,就是欠缺保護她的男性,或是認為自己不需要保護而主張要「做自己。」
不論是《男孩危機》的作者,或者艾莉斯.楊的論述,他們都認為:生而為人的身心安頓(well-being),其實需要的是國家、社會與家庭的支持與培力,而非割裂式的區分強者和弱者、保護者與被保護者。
受創者傷害他人,唯有自己痊癒才能治癒他人。男孩危機的挽救,當從男孩的教育與成年男性的治癒著手。在性別的視角下,男性也是性別刻板印象下的受害者,任何對於性別的培力 ( empowerment)
,都應該給予支持。對於男孩,教會他學習聆聽,不因為身為男性而被貶抑,對於看著父執輩只划一邊的槳,卻眼見同儕和配偶雙槳齊划的成年男性,則要給予鼓勵與引導,讚美他們忠於自我的工作和生活,一步一步協助這些心裡住著無所適從、危機男孩的男人,拿起另一邊的槳。
我很幸運,我的11
歲男孩(小名包包),是一個暖男,我這一輩子受到別人的鼓舞和安慰最多的是來自我的包包。他幾乎不存在任何性別的刻板印象,最欣賞的是一個班上想要從軍的女孩。在這個充滿未知的年代,教養兒女是身為父母十分困難的學習歷程,因為我們不像我們的上一輩,可以想當然耳、單純地做些「我是為你好」的指令。但可以確定的是,包包性格裡的溫暖和開闊,定與他從小看多了雙槳齊划的父母與叔伯阿姨們有關。我期待他能順利度過男孩危機,長成一個有自信、樂在自己的生活、並對社會有貢獻的男人。
所有的經驗都是學習而來,何況當女性爭取權利時,我們也曾得到許多男性的支持和協力,所以,女性在男孩危機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我們不能協助文化轉變,幫忙男性在這個時代度過危機,同在家庭與社會的船上,最終受害的依然是我們的社會和我們自己。
作者在書中提出很多教育和文化轉換的方法,以學校、家庭、飲食、活動、情緒等各種調整,希望治癒受傷的男人、教育有危機的男孩,我自己看了很有啟發。因為深刻的理解、尊重個體的發展和差異、分享和指導他人雙槳齊划的經驗,將男性從英雄傳說中解放出來,同時打破女性的刻板印象,可謂是一種助人亦能助己的實踐。我樂意為之,但願你也是。
林志潔教授/交大科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