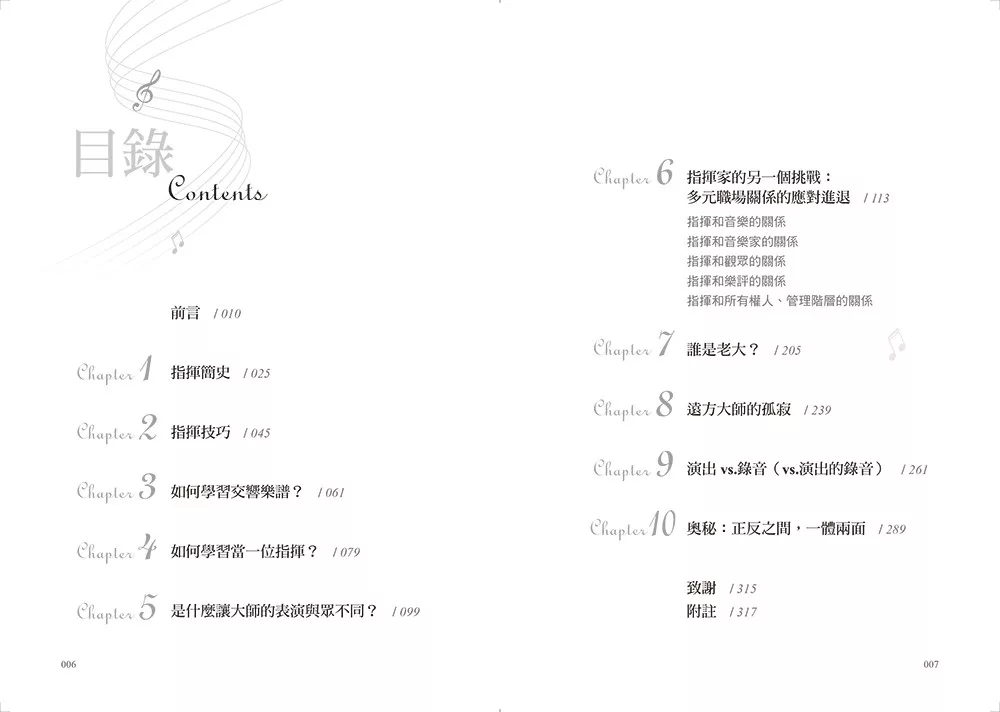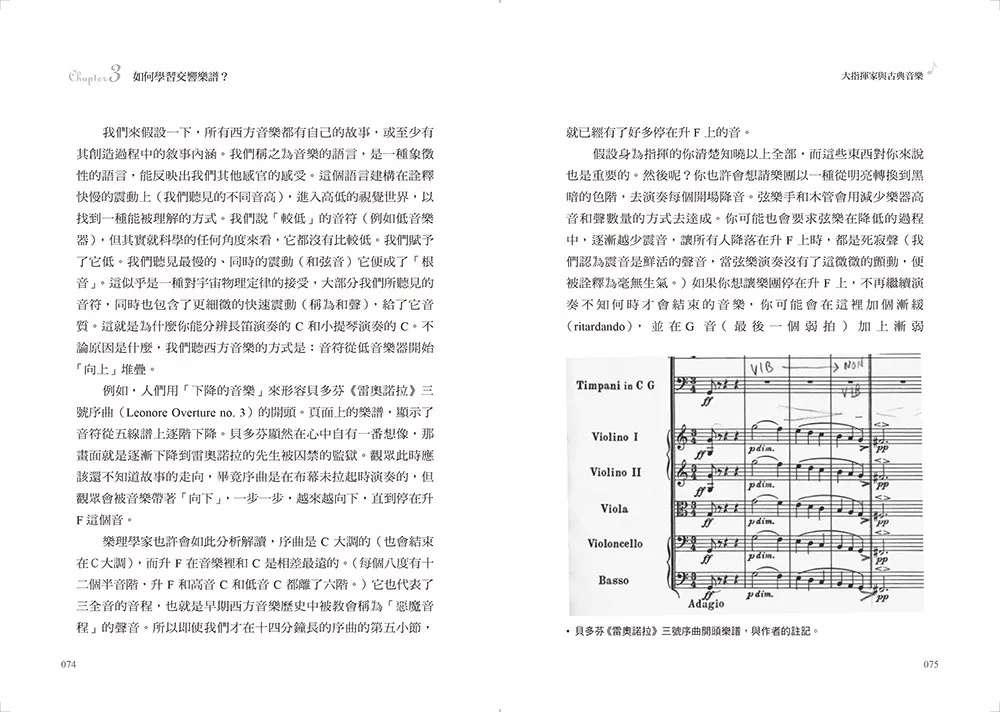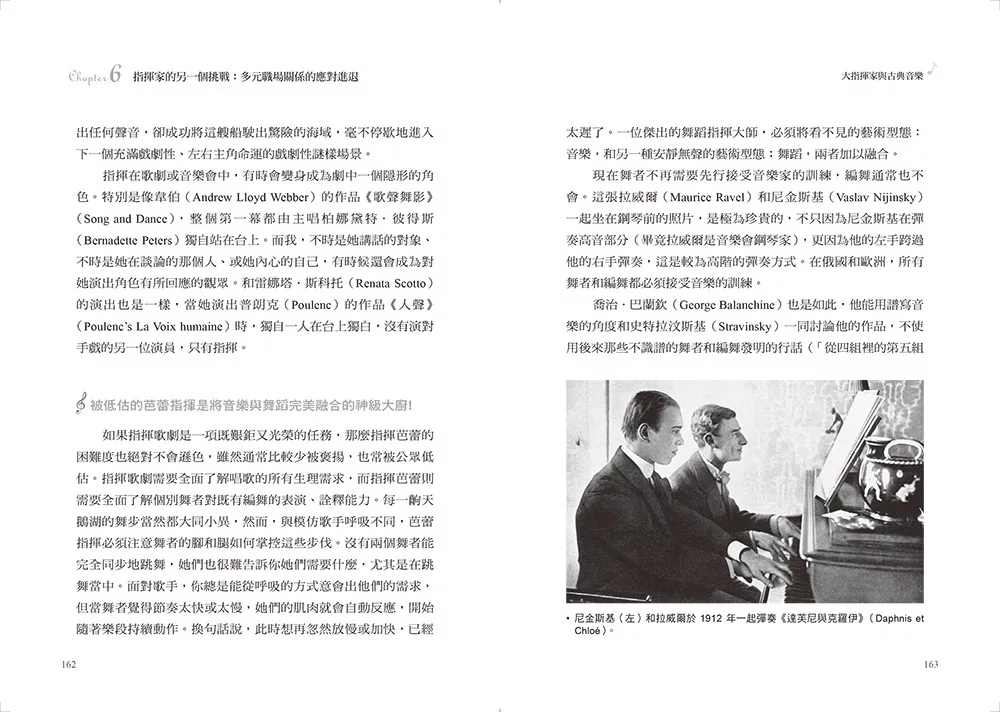前言
在1975年的薩爾茲堡音樂節(Salzburg Festival),伯恩斯坦指揮兩場音樂會,身為音樂節藝術總監的卡拉揚則指揮兩齣歌劇,其中一齣(威爾第(Verdi)《唐.卡洛》(Don
Carlo)的新版製作)他也身兼導演,同時監製另外三場音樂會。這兩位巨頭極為罕見地身在同一個城市、指揮同一個管弦樂團──維也納愛樂──進行演出。伯恩斯坦在音樂節是個新面孔,而卡拉揚,或他的妻子愛莉特(Eliette),認為請他來家裡共進午餐是個好主意。
一回到紐約,伯恩斯坦就邊喝著蘇格蘭威士忌,一邊告訴我所有的事。在此之前我應該先說明,伯恩斯坦幾乎沒有染上我們指揮家拿起指揮棒後都會有的毛病:忌妒。就像卡拉揚一度出現在古典音樂界的笑話中一樣,我們年輕指揮家也想去到所有地方,指揮所有東西。卡拉揚在照片中戴著太陽眼鏡、駕駛小飛機、在阿爾卑斯山滑雪、練習瑜珈,再再都展現了他歐洲人的魅力。然而,伯恩斯坦則很親民。他是「雷尼」。偶爾會有人對他的同僚有些微詞,但伯恩斯坦大部分很高興能做自己。他全心全意地做這份工作,對八卦和暗箭完全不感興趣,雖然我們指揮家都很怕這些東西。有次我談到麥可.提爾森.湯瑪斯(Michael
Tilson Thomas)的傳記讓他五年來都維持在二十三歲,伯恩斯坦表示:「這跟你完全無關。」然而,對卡拉揚來說,一切完全不同。
當我第一次問起伯恩斯坦關於這位奧地利大師的事時,他簡潔地用幾個字形容卡拉揚。「他比我大十歲,比我矮一公分。」他用一種冷靜甚至冷酷的方式說道。很顯然,那次的午餐對大家來說都是場試驗。伯恩斯坦的女兒潔米(Jamie)和她媽媽一起跟著出席,在她的日記裡寫道愛莉特「惡意地向她爸爸調情」,並刻意對卡拉揚不屑一顧,把氣氛弄得很不愉快。「HVK看起來矮小、脆弱、又緊繃。」
卡拉揚決定以講述偉大又機智的英國指揮湯瑪仕.畢勤爵士(Sir Thomas Beecham, 1879-1961)的故事來打開話題。戰後,畢勤爵士指揮一群特別的英國音樂家,在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倫敦進行演出。由身為希特勒支持者的卡拉揚本人來述說這個故事的那種尷尬,他自己也很明瞭。畢勤的首次排練,遇到英國最棒的雙簧管演奏家萊昂.古森斯(Léon
Goossens),他吹出A,讓樂團調音。古森斯因其獨特的樂音相當出名,有著頗為狂野的顫音,而非精確毫無偏差的聲調。當他吹出A之後,畢勤爵士從指揮台看向大家,以他英式的幽默說道:「先生們,自己選吧(拿起樂器吧)。」
如果這是本有聲書,你就會聽見我模仿伯恩斯坦模仿卡拉揚模仿畢勤爵士。指揮有很多面向,但我們絕對是很自我陶醉的、不但為自己的領域深深著迷、同時也對自己的感知控制感到心神不寧。就算在專業領域上已經相當頂尖,我們還是會到處說著彼此的故事。討論指揮家的趣事對樂團團員來說,也像流在他們血液中那麼自然。
「我不認為卡拉揚讀過任何書。」雷尼告訴我那頓午餐中他多麼困難地嘗試著和他進行有意義的對話。(我應該解釋一下,偉大的指揮家是有可能對書本完全沒興趣的,雖然聽起來似乎很奇怪。)伯恩斯坦可以討論很多事,他是個熱心的讀者,一個研究歷史的學生,一個老師,也是政治活動家,他能聊馬勒或威爾第的音樂、能聊任何作曲家或與作曲相關的事情、也能聊擔任音樂總監是多麼艱鉅的任務。但是,一邊吃午餐一邊交換指揮大師的軼事,很明顯並非他的風格。
「雷尼,我應該指揮你的哪部作品?」賀伯特一度這樣詢問。伯恩斯坦想了一下,決定給他一個瘋狂的答案,因為他知道卡拉揚不會懂他回答中的暗示或諷刺。「嗯⋯我想《彌撒》(Mass)應該可以。」他回答。《彌撒》這首伯恩斯坦在1971年完成的曲子,是他最大型也最複雜的作品。為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所作的《彌撒》,編入了羅馬天主教彌撒的禮儀,還有前台政治抗議者的流行音樂交錯穿插。伯恩斯坦認為在這場無意義的餐會中這樣做無傷大雅,竟唆使邀請他吃飯的主人,考慮表演一齣他永遠不會表演的作品。而且,這會是對伯恩斯坦的一種尊崇:卡拉揚必須去研究、製作一整個晚上的「伯恩斯坦式作品」,需要一個管弦樂團、一個樂隊、一組流行樂手、一個教會合唱團、和一個唱詩班。這大概是伯恩斯坦能給出的最微妙也最殘忍的建議,因為他知道卡拉揚對《彌撒》是什麼樣的作品毫無概念,而且肯定不會對自己的音樂有任何興趣。除了潛伏在那間飯廳裡的忌妒和猜疑之外,卡拉揚幾乎沒有對任何還在世的作曲家展現任何興趣。在預料之中,伯恩斯坦謙遜的提議換來一陣沉默,接著大家便開始享用餐後咖啡。
在告訴我這個故事的時候,伯恩斯坦一邊這樣說,就像在教我未來該如何得體應對。「我對參與戰爭(Dirigentenkrieg)一點興趣也沒有。」那是一個用德文發明的字,意為「指揮家的戰爭」。
伯恩斯坦開始回憶,他第一次見到卡拉揚是在米蘭,1955年。卡拉揚當時在斯卡拉大劇院指揮《卡門》,伯恩斯坦則在等待《波希米亞人》(La Bohème)因男高音史帝法諾(Giuseppe di
Stefano)身體不適而延遲的排練。看了一場《卡門》演出後,伯恩斯坦告訴卡拉揚他的指揮技巧「是我看過最棒的歌劇指揮⋯當然了,除了我自己之外。」這種典型的伯恩斯坦冷笑話,卡拉揚完全無法聽懂,他以德式的嚴肅搖搖頭,說道:「當然了。」卡拉揚建議伯恩斯坦等待斯卡拉大劇院排練《波希米亞人》演出的時候,可以去滑雪。伯恩斯坦說他沒帶滑雪裝備,卡拉揚表示可以借他。這就是為什麼伯恩斯坦知道他的奧地利同事「比他矮一公分」。伯恩斯坦接受了他的提議,以示友好。「畢竟,」他對我說著他的冷笑話,「他是我的第一個納粹朋友」。
這中間藏著指揮家、和指揮藝術的一個重點:這是一條會耗盡全副精神的道路。即使是最傑出的指揮家,都會在背後說著其他指揮家的八卦,大部分聚焦在已逝世的那些人身上,避免表現出敵意。指揮技巧被傳授、流傳的方式,就像中世紀的某種儀式一樣,由大師親自調教自己年輕的學徒。
然而,這其中的秘密,在別的領域被稱為行業訣竅的東西,通常被每個大師各自私藏。伯恩斯坦1979年帶領柏林愛樂演出大家期待已久的首演,曲子是馬勒第九號交響曲,他說是他「教導」樂團如何演奏。即使是最厲害的樂團,在第一次演奏這部作品時,都需要指引。(1979年當時,柏林人已經好幾十年沒有演奏這部交響樂,實際上對他們來說是全新的曲子。)樂團的第一次意味著指揮會說很多話,向樂手解釋曲子如何組成,哪裡有旋律、如何做出大量詮釋的抉擇,可能還要提供作曲家的背景資訊、和他的靈感來源。在樂團開始對一部作品有共同的認識之後(通常要和許多指揮家演奏過許多年後),樂手才不需要、或不想要指揮提供這些訊息。
小提琴的聲部、打擊樂器的樂譜、木管和低音樂器的資料夾──伯恩斯坦個人為馬勒這首交響樂曲打造的管弦樂分譜,充滿伯恩斯坦修訂的、你可以說是他的「小秘訣」,在他抵達家中時還沒被送回紐約。對自己經常演出的曲目,指揮通常有自己的一份樂譜。如果曲目是公有財產,例如貝多芬交響曲,指揮可以付費買到出版社印刷的樂譜。如果作品仍是私有財產,那麼曲子便不能在未付款給所有者或所有機構獲得授權之前進行任何演出。擁有所有權的音樂公司會為知名指揮大師保留一份樂譜,沒有其他人能使用、或改變被加上的記號。這麼做有兩個原因。首先,分譜會詳細描述指揮在編輯音樂上的決定,例如節拍模式(2或4),以及弓法(弦樂聲部如何將自己聲部的幾千個音符組成句子,根據向上或向下運弓的方式)。這兩樣東西都會大幅改變音樂聽起來的樣貌。例如史托科夫斯基便經常要求「自由弓法」,刻意讓不同組樂手的運弓方法不一致。雖然觀眾看來會有些凌亂,但卻能創造出一種極有控制力道的無縫樂音。
另一個原因是分譜藏有秘密。這些秘密包含讓特定音符演奏得比印刷指示的力度更大聲或更柔軟的修改;也可能包含重編,讓某些音符(聽者感覺不到)被其他樂器加強;或改變聲音演奏的方式(音符的音質與長度),去帶出指揮想強調的作品面向。既然馬勒生前沒機會指揮自己的第九號交響曲,那麼指揮就有更大的責任去更動(在他心裡可能認為是改進)樂譜上的東西,讓眼前的樂團能將作曲家原始意圖好好展現。伯恩斯坦是個馬勒專家,他指揮第九交響曲的次數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多,也擁有多年演出經驗,這些都能在他的樂團分譜上面找到。卡拉揚對這首曲子來說相對是個新手,對作曲家和他的九首交響樂都沒有展現太大的興趣。
伯恩斯坦的紐約辦公室打了電話、也寫了信,要求柏林寄回他的音樂素材。幾個月過去了,卡拉揚隨後和柏林人錄製了馬勒第九號交響曲,並藉此贏得留聲機音樂獎(Gramophone Award)。後來伯恩斯坦的樂譜被寄回,他相信卡拉揚使用了他的樂譜筆記進行演出和錄音,於是他將此事公開,讓所有人都知道這件事。
也許卡拉揚是在報復伯恩斯坦,因為他聲稱伯恩斯坦在1958年和紐約愛樂的演出,複製了他的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卡拉揚指揮紐約愛樂在卡內基音樂廳表演過四次,一周後伯恩斯坦便在電視上演出這部卡拉揚近期才排練並修飾過的作品。
忌妒和偷竊會對卡拉揚和伯恩斯坦造成傷害,因為每個人都能重複另一個人的表演。既然卡拉揚手上沒有伯恩斯坦的馬勒總譜、只有分譜,他只能理解伯恩斯坦編曲其中的一部分。他必須要排練時聽樂團演奏,因為他眼前的譜只有印刷內容。雖然他可以聽取伯恩斯坦演出的錄音檔案,但事實上卡拉揚的馬勒第九號交響曲,效果和伯恩斯坦的完全不同。同一部作品,由兩位不同指揮家,在幾個月內指揮同一個管弦樂團演奏,有可能、也一定會讓聽者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即使某些魔法咒語的成分是相同的。「給三位傑出的大廚同一份食譜,他們會做出三道不一樣的菜餚。」這一句有名的諺語,也能套用在樂譜和它的詮釋者身上。
伯恩斯坦版本的馬勒,節奏持續處在波動狀態:他經常慢下來,讓聽眾準備好去聽他想要你注意到的東西,他讓第一部分小小的、悲傷的雙音符旋律變成一種吸氣、吐氣的起伏。另一方面,卡拉揚演奏的交響樂開場,在節奏上則沒有太多改變。取而代之的是,他在每次進入新的高潮時,都會創造一種勢不可擋的感受,減少使用節奏波動技巧,將漸慢(也就是將節奏放寬)的效果拉長,製造一種較大型的弧線,而非小型互相串連的弧線。所有這些東西(以及它對後面整首交響曲產生的影響),都發生在這部曠世鉅作的第一分鐘。
所有偉大的指揮家都不相同;而平庸的則多多少少都很相似。
站在交響樂團前面的那個人,被賦予了一些不可能也不實際的東西。不可能的部分是聚集幾百位音樂家,讓他們同意所有細節;不實際的部分是這個人只能用在空中揮舞雙手的方式來達成這件事。畢竟,這整件事有點像在變魔術。音樂是一種隱形的藝術型態,它是被控制的聲音,在一連串的轉換中,透過時間來創造結構。也許,當隱形的東西需要被領導時,被指派的領導者必須以無聲的手勢來完成此事,也是很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