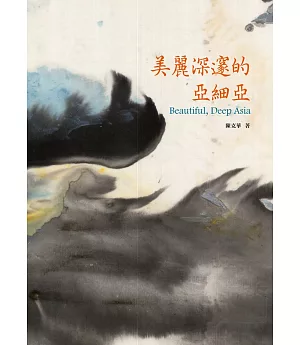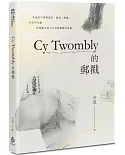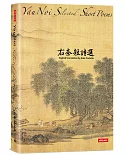改版新序
似乎只在轉眼間,《美麗深邃的亞細亞》的初版,已是廿多年前的事了。近日又翻了翻這本深色封面的小書,出版日期是一九九七年四月。那年香港回歸中國,我赴哈佛進修,好友Allen病逝於雞尾酒療法問世前。那一年如同你我生命中的每一年,生活中應該還有許多可供記述的大小事件,只是現在都不復記憶。
那年鄭問應該以他的水墨技法,也已在日本成名,開始創作他的「深邃美麗的亞細亞」。我單純長久以來喜愛他的漫畫,愛到每一格都凝視良久,久久翻不過一頁的程度。
其實每個時刻,每個人生命都在不間斷地進程,滙成了這個世界當下的面貌—但當下的我們總是懵然無知。
誰能知道九七年我無意間寫下一首〈美麗深邃的亞細亞〉,竟成為一本詩集的標題,繼而成為我和鄭問之間惟一的連繫,使得我在二○一八年再度和鄭問相遇。這期間因為這本詩集,一直有人向我詢問鄭問的近況,包括正在寫論文的學生,而我和鄭問素昧平生,緣恪一面,只能愛莫能助。
曾經《阿鼻劍》使得身為佛教徒的我驚喜連連,訝於武俠和佛道在鄭問手中可以如此無縫接軌,相得益彰;《刺客列傳》及《東周英雄傳》則召喚了中國人自秦漢以降就頹靡不已的孤狼式俠義精神,那文化裡一去不返的「士」,那種以「殉」呈現節操的人格高度。
從鄭問的漫畫我不但看到了活潑淋漓的人性,奇幻瑰麗的想像,更看到了一個亦儒亦俠的鄭問,以及自己。我們靈魂裡共通的心跳和呼吸。但再翻閱這本詩集,依然有許多不解之處。第一印象是有點「鬼氣森森」。因為就記憶所及,書中許多首詩是從夢境演繹出來的。也許那時期正呼應了榮格所謂的「前中年期」生命轉彎並重新定義生命的重大時刻,潛意識裡吹起除舊佈新的大風暴,那時的我「文青」之外,更是「憤青」。
但竟也有文友認為這是我「截至目前最好的一本詩集」。而我先天對「最」這個字過敏,當然否認。如羅智成所說,「詩人對自己的作品是毫不留情地喜新厭舊。」記得當年還和夏宇、孫維民在空前激烈的競爭中,共得「台北文學獎」。而「再拒」(Against
again)劇團也拿這本詩集改編,在「帳篷戲劇節」裡公演—我四處招兵買馬,自掏腰包為大家買了入場券,一起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搭起的帳篷裡,像看馬戲團表演似地看自己的詩被「表演」,更像個孩子一樣的興奮又茫然。
二○一八年故宮博物院舉辦鄭問個人回顧展,這本已經絕版多時的詩集再度被提起,因為一首〈美麗深邃的亞細亞〉(連同書名)原脫胎於鄭問的漫畫《深邃美麗的亞細亞》。也因為這本詩集,我得以結識鄭問的大弟子鐘孟舜。我們原有計劃出版一本以鄭問為主題的詩集,於是我嚐試以鄭問漫畫人物寫詩,如《阿鼻劍》裡的何勿生和地獄使者,《深邃美麗的亞細亞》裡的潰爛王和百兵衛等。這些詩如今收在輯七「致鄭問」,成為此版和初版最大的不同。且承蒙鍾兄惠賜大作,讓這本詩集封面有了原汁原味的「鄭問風」,也更「名符其實」了,特此致謝。
與書林出版公司合作多年,每回出書都是一次愉快的經驗,特別感謝蘇氏兄弟的知遇和提攜,也感謝張麗芳小姐高效率且專業的編輯。
當然還有鄭問—他以他不可思議的漫畫天份和近乎偏執的不懈努力,堅持創新,畫出了令我靈魂不致枯竭的作品。當年的我是多麼卑微與羞怯地以他作為自己的精神伴侶。此刻今朝,我才隱約明白,那是我回應了他的「殉道精神」。而那原也是一個詩人面對繆思時惟一的命運和選擇。
願此刻的鄭問,已經在一個更好的地方,繼續他驚世的創作。
陳克華
二○二○年一月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