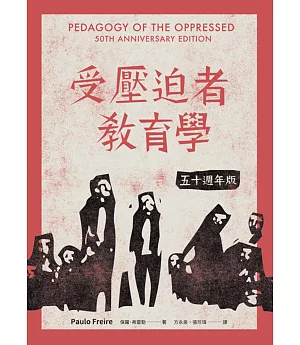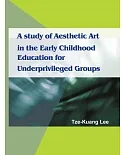前言
這篇介紹《受壓迫者教育學》的前言,源於我在這6年政治流亡過程中的觀察,透過這段時間的觀察,使我先前在巴西所進行的教育活動的意義更加豐富。
在分析覺醒(conscientização)角色的訓練課程及解放教育的實際實驗中,我遭遇到了本書第一章中所提之「恐懼自由」的問題。一些參與訓練課程者常常注意到「覺醒的危險」,這顯露出他們對於自由的恐懼。他們說,批判意識,即是無法無天。其他人則再加上,批判意識會導致社會脫序。不過有些人也承認:為何要否認它?我過去是害怕自由,但我現在不再害怕!
在這些討論中之一,人們所爭論的是:對於某一特定不公義情境的覺醒是否會使他們陷入「毀滅性的狂亂」或是導致「他們世界的全面崩潰」。在討論的過程中,有一位曾擔任過多年勞工的人說出:「或許我是此地唯一來自勞工階級的人。我不敢說我已完全瞭解你們剛才所說的,但我能告訴你們一件事─當我開始這個課程之時,我是天真的,而當我發現到自己是如何的天真時,我開始變得有些批判性。但這個發現並沒有使我成為狂熱分子,我也沒有感到任何的崩潰。」
對於覺醒可能後者的疑慮,隱含著一個疑慮者隱而未顯的前提:對於那些身為不公義的犧牲者來說,最好就是不要發現他們自己是犧牲者。然而事實上,覺醒並不會導致人們「毀滅性的狂亂」。相反地,它會使人們以負責任之主體的身分進入歷史過程中,覺醒可以幫助人們尋求自我的肯定而避免盲從。
批判意識的覺醒之所以會引致社會的不滿,原因即在於這些不滿其實正是構成壓迫性環境的一部分。
對於恐懼自由的感受,其擁有者不一定會察覺到,但會使得他處處戒慎恐懼。這樣的個人在現實中總想尋求避難所來保證自己的安全,他或她寧可將自由視為危險的。如同黑格爾(G. Hegel)所說的:
唯有藉著生命的冒險,才能獲得自由⋯⋯那些未將自己
生命做為賭注的人,也許仍然無疑地可以被認定為一個
人(a Person),但他並沒有獲得做為一個獨立自我意識
時所認定的真理。
人們很少公開承認自己對於自由有所恐懼,不過常常在無意中將其偽裝起來─以一種自由的捍衛者身分出現。他們將其疑慮用一種鄭重其事的態度掩飾起來,因為這種外表比較適合自由的守護者。但他們卻將自由與維持現狀混為一談;乃至於當覺醒可能會對現狀造成一些威脅時,似乎就會對於自由有所妨礙。
光只有思想或是研究,並不能創造出這本《受壓迫者教育學》;它植根於具體的情境,並且描述了勞工(農民或都市內的勞工)及中產階級人們的反應,這些都是我在教育工作中直接或間接觀察到的。由於不斷的觀察,使我能有機會修正或確認這本具導論性質作品中的論點。
對於許多讀者來說,本書中的論點或許會帶來負面的反應。有些讀者可能會認為我關於人類解放的論點,純粹只是理想;有些人可能甚至會認為關於存有志業、愛、對話、希望、謙卑、憐憫等問題的討論,只是「瞎說」而已。其他人則可能不會(或是不希望)接受我對於那些維持壓迫者之壓迫狀態的批判。因此,這篇具實驗性質的著作其實是為基進主義者(radicals)而寫的。我很確定,包括基督教徒或是馬克思主義者,容或他們是部分或是完全地不同意我,他們仍都會讀到最後。但是對於那些獨斷的、封閉的與「非理性」的讀者來說,他們將會拒斥我在本書中所欲開啟的對話。
源於狂熱心理的門戶之見者,總是自我設限;而受批判心靈所滋潤的基進化(radicalization)卻是充滿創造性的。那些劃地自限的門戶之見會造成神祕化與疏離化;而基進化則進行批判與解放。由於基進化會促進個人對於所選擇立場的投入程度,因而會使得他能更加努力去改變外在具體的現實。相反的,抱持門戶之見的看法者,由於神祕化及非理性的結果,他們會使得現實成為一種假的(也就是不可改變的)「現實」。
無論在任何時候,門戶之見對於人類的解放來說,都是一種阻礙。不幸的是,右派分子並不能招引出它真正的對立面:追求基進的革命分子。某些革命分子在回應時,常常墜入門戶之見中,而變得比較反動。儘管如此,此等可能性也不應使基進主義者變成菁英階級溫馴的爪牙。在從事解放的過程中,面對著壓迫者的暴力,他不能一直保持被動的狀態。
另一方面,基進主義者也不是一個主觀主義者。對他來說,主觀的層面僅只存在於與客觀層面有關的時候(具體的現實,正是他分析的客體或對象)。在一個辯證性的整體中,主觀性與客觀性共同參與,產生了與行動結合的知識。反之亦若是。
對於抱持門戶之見者來說,由於受到非理性的蒙蔽,他並未察覺到現實的動態性─要不然他也會曲解它。即使他能夠辯證地去思考,也是以一種「馴服式的辯證」去思考。右派的門戶之見者(我早先曾稱之為天生的門戶之見者)企圖減緩歷史的進程,以「控制」時間從而去馴服人。而由左派轉向門戶之見的人,當其嘗試辯證地去解釋現實與歷史時,完全地走叉了路,因而墮入了命定論的立場中。
右派的門戶之見者不同於左派的故步自封者之處在於:前者想要去馴服控制現在,如此可使得未來亦被再製為「馴服的現在」,而後者則是認為未來業已預定─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命運。對於右派的門戶之見者來說,「今日」與過去緊緊連接,是既定的、不可改變的;對於左派的門戶之見者來說,「明日」事先即已命定,也是不可更動的。無論左派或右派的門戶之見都是反動的,因為它們的基礎是源於錯誤的歷史觀點,這使得他們所發展出來的行動形式會否定了自由的存在。一位想像著「馴服的」現在的人與另一位想像著命定的未來的人在一起,並不表示他們就會袖手旁觀(前者期待現在將會繼續下去,後者則等待那「已知的」的未來經過);相反地,由於他們將自己封閉於不能逃脫的「確定性循環」(circle
of certainty)中,這些人「造就」了他們自己的真理。這種真理不是男人與女人經過奮鬥、遭遇危險時所建造的未來的真理;它也不是男人與女人並肩作戰、一起去學習如何建造未來的真理─它不是群眾接受的既有事物,而是人們所主動創造出來的事物。無論左派或右派的門戶之見都將歷史視為禁臠,其中並無任何群眾的參與─群眾是另一種反對他們的存有方式。
右派的門戶之見者,是將自己封閉於「他的」真理中,其目的僅在履行他天生的角色;左派的門戶之見者,則是固執地否定他生來的角色。因為他們一直在「他的」真理周遭打轉,所以當其真理受到質疑時,他們會感到受威脅;他們認定那些不屬他們真理的一切事物都只是謊言。如同一位記者艾夫斯(Marcio Moreira Alves)所告訴我的:「他們患有一種不疑的疾病。」
「確定性循環」會使得現實被囚禁起來,而致力於人類解放的基進主義者則並未成為封閉於「確定性循環」中的囚犯。相反地,當他愈基進的時候,他所進入的現實也就愈加完整,他會更清楚地認識現實,並且更能去改造它。他並不懼於迎向未知世界的挑戰,也不畏於聆聽、目睹這未知的世界。他並不害怕與人們相遇,也不恐懼與他們進行對話。他不會將自己視為歷史與群眾的領主,也不會將自己視為受壓迫者的救星;但在歷史中,他會與受壓迫者在一起進行戰鬥。
在下面篇幅中提出的「受壓迫者的教育學」,所要勾勒的正是基進主義者的工作大綱,這在門戶之見者的手中是無法實現的。
如果有些具足夠批判力的讀者能夠因著本書而改正自己原先的錯誤與誤解,加深對自己的肯定,並且指出我所未注意到的層面,筆者就心滿意足。雖然有些人可能會對我並沒有實際參與革命性文化行動的經驗,而對我的討論權利有所質疑,不過儘管我個人並無實際參與革命行動的經驗,但卻也不應因而否定我在此論題上進行反省的可能性。更進一步來說,以我做為一個運用對話式與提問式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來說,我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資料,這些資料對我形成了挑戰,並使我大膽地在本書中做出一些主張。
藉由本書,我至少希望下列的信念能一直持續下去:我對於群眾的信賴、對於所有人們的信念,以及對於創造新世界的信念。透過這個新世界可以使得人們在其中更容易去愛。
在此我要表達我對於我的妻子艾爾莎(Elza)的感激之意,她是本書的「第一個讀者」,感謝她對於我的作品的理解與鼓勵。我也想要感謝一群朋友對於我的手稿所提供的意見,冒著可能會遺漏掉某些名字的危險,我必須提出考汀荷(João da Veiga Coutinho)、索爾(Richard Shaull)、蘭姆(Jim Lamb)、拉穆斯夫婦(Myra and Jovelino
Ramos)、塔索(Paulo de Tarso)、阿方索(Almino Affonso)、山派歐(Plinio Sampaio)、艾納尼.菲歐利(Ernani Maria Fiori)、葛加多(Marcela Gajardo)、荷西.菲歐利(José Luis Fiori),與查卡利歐第(João
Zacarioti)等人的名字,對他們表達我的感謝。不過本書所做主張的責任,當然仍屬於作者個人。
保羅.弗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