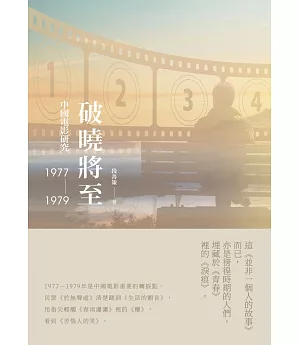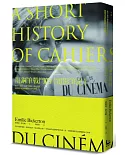1977-1979年是中國電影重要的轉捩點,民眾《於無聲處》清楚聽到《生活的顫音》,用指尖輕觸《春雨瀟瀟》裡的《櫻》,看到《苦惱人的笑》。這《並非一個人的故事》而已,亦是徬徨時期的人們,埋藏於《青春》裡的《淚痕》。
掙脫「樣板戲」的重重枷鎖,再現起心動念的創作初衷。
以破曉的光芒照亮黑夜,讓「恢復時期」回歸歷史本位。
普遍來說,電影為大眾提供了現實解釋與精神慰藉,是非常重要的大眾娛樂。在中國的文革時期,電影卻成為歌詠讚頌政府官員的工具,也就是俗稱的「樣板戲」。對於勇敢活躍於檯面上的中國電影創作家們而言,如何描述剛剛逝去的歷史,把握此刻上演的故事已不僅是藝術問題,而是關係到大時代下小人物們的個體命運。通過電影敘事上的諸多悖論與徵候,最終抵達話語與現實不相契合的社會真相。
本書探討中國1977-1979年期間約一百多部電影。此時期的電影嘗試跳脫「樣板戲」的固定套路,在明確的目的和模糊的歷史之間小心地閃轉挪移,對歷史進行選擇性記憶和重述,並在審判「他者」和自我神化的文字遊戲中放逐恐懼、救贖自我。作者用清晰的思緒配以精湛的文筆,從創作格局、語法表徵與意識型態出發,完整分析這些電影創作的時代背景與表達意涵。
本書特色
☑1977-1979的中國電影努力掙脫「樣板戲」的重重枷鎖,以破曉之光照亮黑夜!
☑讓時代洪流中的「恢復時期」重新回歸歷史本位,再現起心動念的創作初衷!
目錄
◇自序◇
【緒論】
第一節 後神話初年:一個歷史的「棄嬰」
第二節 研究現狀
第三節 電影藝術與意識形態
第四節 研究思路與方法
【第一章 風格與觀念:在懷鄉病與現代性想像之間】
第一節 創作格局及其語法表徵
第二節 鏡語風格及其「懷鄉病」
第三節 觀念解放與現代性想像
【第二章 政策與話語:在解凍與遮蔽之間】
第一節 政策:規訓與激勵之間
第二節 話語:繁複與遮蔽之間
【第三章 狂歡與傷痕:後神話的精神症候】
第一節 「戰爭」想像的狂歡化
第二節 「子承父志」的神話
第三節 「傷痕」敘事的易卜生主義
【第四章 沉重的肉身:知識份子的主體建構】
第一節 前世:罪與罰
第二節 「他者」:宿命與彷徨
第三節 準主體:從啟蒙者到被啟蒙者
【第五章 歷史與傳奇:戰火硝煙裡的國族想像】
第一節 英雄史詩:父輩指認與秩序回歸
第二節 戰地柔情:戀母情結與倫理焦慮
第三節 個人傳奇:冷戰餘緒與另類想像
【第六章 置換與虛無:嬉笑怒罵的政治無意識】
第一節 國家敘事的置換與延續
第二節 歷史虛無主義:「都是誤會,鮮有諷刺」
第三節 《小字輩》:互文下的烏托邦敘事
總結
參考文獻
附錄:中國劇情電影目錄(1977-1979)
後記
【緒論】
第一節 後神話初年:一個歷史的「棄嬰」
第二節 研究現狀
第三節 電影藝術與意識形態
第四節 研究思路與方法
【第一章 風格與觀念:在懷鄉病與現代性想像之間】
第一節 創作格局及其語法表徵
第二節 鏡語風格及其「懷鄉病」
第三節 觀念解放與現代性想像
【第二章 政策與話語:在解凍與遮蔽之間】
第一節 政策:規訓與激勵之間
第二節 話語:繁複與遮蔽之間
【第三章 狂歡與傷痕:後神話的精神症候】
第一節 「戰爭」想像的狂歡化
第二節 「子承父志」的神話
第三節 「傷痕」敘事的易卜生主義
【第四章 沉重的肉身:知識份子的主體建構】
第一節 前世:罪與罰
第二節 「他者」:宿命與彷徨
第三節 準主體:從啟蒙者到被啟蒙者
【第五章 歷史與傳奇:戰火硝煙裡的國族想像】
第一節 英雄史詩:父輩指認與秩序回歸
第二節 戰地柔情:戀母情結與倫理焦慮
第三節 個人傳奇:冷戰餘緒與另類想像
【第六章 置換與虛無:嬉笑怒罵的政治無意識】
第一節 國家敘事的置換與延續
第二節 歷史虛無主義:「都是誤會,鮮有諷刺」
第三節 《小字輩》:互文下的烏托邦敘事
總結
參考文獻
附錄:中國劇情電影目錄(1977-1979)
後記
序
自序
一直以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電影作為一段承上啟下的歷史被束之高閣。
對於後神話時代最初的這段時期,歷史未曾給予其一個明確的主體身分。
誠然,這一時期生產的大多數影片缺乏一般意義上的美學建樹,但依然可以「《於無聲處》」聽到「《生活的顫音》」,看到「《苦惱人的笑》」「《並非一個人的故事》」,觸到「《春雨瀟瀟》」裡「《櫻》」上綻放的「《小花》」,感受到「《青春》」裡的「《淚痕》」。
作為社會意義與價值再生產的公共文本和重要場域,這些影像向社會激流裹挾的普羅大眾提供了現實的解釋與精神的慰藉。對藝術家們而言,昔日詠頌的聖像紛紛崩塌,歷史的車輪走到了諸神退位的時代,如何描述剛剛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故事,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藝術問題,更關係後神話時代裡的自身命運。某種意義上,個人處境與集體想像形塑了電影生態的政治無意識―無論是審美與教化的功能之辨,還是精英與大眾的趣味之別,都與對個人/國族關係的想像方式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
1930年代,有關「硬性電影」與「軟性電影」的爭論,表徵著不同社會力量對於個人/國族關係的想像方式。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藝術服從政治論」終結了對上述關係不同想像的可能性。「文化大革命」時期,樣板戲在整個文藝界「獨領風騷」的畸形局面,正是貫徹「政治掛帥」文藝路線的典型症候。1978年底,一場自上而下的「撥亂反正」運動席捲神州。它宣告「文化大革命」落幕,與此同時,也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官方宣傳「解放思想」意味著政府對私人財產權給予部分承認。但是,由此引發民眾對個人/國族關係的再想像, 顯然超出基於啟動國民經濟目的的決策者預期。此後整個1980年代的文化熱點,都可視為以「實事求是」之名,就個人/國族關係再想像問題的闡發。山雨欲來風滿樓,要想釐清這段錯綜複雜歷史的脈絡,乃至理解今日中國之輪廓,需要回溯風雨生發的歷史現場, 即1977-1979年―社會轉型的劇烈震盪,也波及了原本鐵板一塊的思想場域。一場文化藝術領域的「解放思想」運動正在悄悄醞釀。
然而,倘若將歷史的時鐘撥回波譎雲詭的八、九十年代之交, 思想解放的理論來源的合法性其實是可疑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框架,無法解釋突如其來的回縮和逆流。這提醒我們需要重新評估政治對於社會強大的反作用力,尤其考慮到極權體制下政治運作的不透明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之牆在七十年代末的突然崩裂,與其說是生產方式改弦易張的副產品,毋寧說是權力集團內部自五十年代後期以來博弈與妥協的遺腹子。這種政治氣候的不可預測性,也直接導致了文藝政策及其規訓下文藝創作的舉棋不定。儘管有關個人的、欲望的、非革命的話語仍然受到諸多限制,但某些政治議題也開始尋求借助日常生活化的場景和民間話語來展現。因此,七十年代末的中國電影呈現一種政治敘事欲拒還迎、欲望敘事欲語還休的奇特景觀。
這種話語躊躇在回顧剛剛過去的歷史時表現得尤為明顯。一方面是歷史神聖性敘述的意識形態要求,一方面是傷痛的歷史記憶的切身感受。對此,敘述者唯有在國家的召喚和個人的訴求之間小心地閃轉騰挪,對歷史進行選擇性記憶和重述,並在審判「他者」和自我神化的符碼遊戲中放逐恐懼、救贖自我。
而在傷痕電影裡面,歷史並沒有被粗暴地「他者化」,而被指認為集體性的創傷經驗,然而也由此形成一個悖論―希冀通過傷口的展示來彌合社會肌體的撕裂。正是由於這一悖論的存在,使主流意識形態對傷痕電影採取了一種既利用又警惕的雙重態度。
除了重返近歷史現場,敘述者還對紅色革命歷史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祭奠儀式,其中,毛時代業已揚名的第三代導演的返場頗具況味。作為「十七年」文藝的代言人,長期受到壓抑的表達衝動是他們老驥伏櫪的內在驅力。電影上那些燃情歲月裡的英雄人物,或如赫拉克勒斯般揮荊斬棘,或如普羅米修斯般茹苦領痛,是謝晉《啊!搖籃》、謝鐵驪《大河奔流》、成蔭《拔哥的故事》裡永恆的主體。在這英雄落幕的歷史時刻,「菲勒斯」以父之名傲然挺立於電影中央,流露出敘事者略顯悲壯的英雄情結和揮之不去的懷鄉夢,滿足了其壯志未酬、英雄遲暮的自我想像。歷史場景再一次滑脫為潛意識場景。這同時表明講述歷史並不是要真正回到歷史,而是製造有關歷史的集體記憶,從而淡忘歷史本身。一些敘事架空浩劫直接接續到「十七年」,比如謝晉《青春》。在某種意義上,它們開啟了「指認他鄉為故鄉」的敘述模式,新時期的尋根電影(如《城南舊事》)、九十年代的懷舊電影(如《陽光燦爛的日子》)乃至新世紀的歷史題材(如《歸來》)皆於此展開。
最後,這種創作無意識也滲透到了現實題材的敘事方式上。愛情生活和私人領域被國族敘事徵用,觀眾在烏托邦式的通俗喜劇中被轉換為國家建設的主體。
概言之,通過檢視後神話初年電影內外的敘事症候,本書試圖抵達話語與現實斷裂的源點。
薩特說:「存在先於本質。」一經付梓,本書既成不可改變的事實(或事故),其中優劣,諸位讀者批評指正。
一直以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電影作為一段承上啟下的歷史被束之高閣。
對於後神話時代最初的這段時期,歷史未曾給予其一個明確的主體身分。
誠然,這一時期生產的大多數影片缺乏一般意義上的美學建樹,但依然可以「《於無聲處》」聽到「《生活的顫音》」,看到「《苦惱人的笑》」「《並非一個人的故事》」,觸到「《春雨瀟瀟》」裡「《櫻》」上綻放的「《小花》」,感受到「《青春》」裡的「《淚痕》」。
作為社會意義與價值再生產的公共文本和重要場域,這些影像向社會激流裹挾的普羅大眾提供了現實的解釋與精神的慰藉。對藝術家們而言,昔日詠頌的聖像紛紛崩塌,歷史的車輪走到了諸神退位的時代,如何描述剛剛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故事,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藝術問題,更關係後神話時代裡的自身命運。某種意義上,個人處境與集體想像形塑了電影生態的政治無意識―無論是審美與教化的功能之辨,還是精英與大眾的趣味之別,都與對個人/國族關係的想像方式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
1930年代,有關「硬性電影」與「軟性電影」的爭論,表徵著不同社會力量對於個人/國族關係的想像方式。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藝術服從政治論」終結了對上述關係不同想像的可能性。「文化大革命」時期,樣板戲在整個文藝界「獨領風騷」的畸形局面,正是貫徹「政治掛帥」文藝路線的典型症候。1978年底,一場自上而下的「撥亂反正」運動席捲神州。它宣告「文化大革命」落幕,與此同時,也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官方宣傳「解放思想」意味著政府對私人財產權給予部分承認。但是,由此引發民眾對個人/國族關係的再想像, 顯然超出基於啟動國民經濟目的的決策者預期。此後整個1980年代的文化熱點,都可視為以「實事求是」之名,就個人/國族關係再想像問題的闡發。山雨欲來風滿樓,要想釐清這段錯綜複雜歷史的脈絡,乃至理解今日中國之輪廓,需要回溯風雨生發的歷史現場, 即1977-1979年―社會轉型的劇烈震盪,也波及了原本鐵板一塊的思想場域。一場文化藝術領域的「解放思想」運動正在悄悄醞釀。
然而,倘若將歷史的時鐘撥回波譎雲詭的八、九十年代之交, 思想解放的理論來源的合法性其實是可疑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框架,無法解釋突如其來的回縮和逆流。這提醒我們需要重新評估政治對於社會強大的反作用力,尤其考慮到極權體制下政治運作的不透明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之牆在七十年代末的突然崩裂,與其說是生產方式改弦易張的副產品,毋寧說是權力集團內部自五十年代後期以來博弈與妥協的遺腹子。這種政治氣候的不可預測性,也直接導致了文藝政策及其規訓下文藝創作的舉棋不定。儘管有關個人的、欲望的、非革命的話語仍然受到諸多限制,但某些政治議題也開始尋求借助日常生活化的場景和民間話語來展現。因此,七十年代末的中國電影呈現一種政治敘事欲拒還迎、欲望敘事欲語還休的奇特景觀。
這種話語躊躇在回顧剛剛過去的歷史時表現得尤為明顯。一方面是歷史神聖性敘述的意識形態要求,一方面是傷痛的歷史記憶的切身感受。對此,敘述者唯有在國家的召喚和個人的訴求之間小心地閃轉騰挪,對歷史進行選擇性記憶和重述,並在審判「他者」和自我神化的符碼遊戲中放逐恐懼、救贖自我。
而在傷痕電影裡面,歷史並沒有被粗暴地「他者化」,而被指認為集體性的創傷經驗,然而也由此形成一個悖論―希冀通過傷口的展示來彌合社會肌體的撕裂。正是由於這一悖論的存在,使主流意識形態對傷痕電影採取了一種既利用又警惕的雙重態度。
除了重返近歷史現場,敘述者還對紅色革命歷史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祭奠儀式,其中,毛時代業已揚名的第三代導演的返場頗具況味。作為「十七年」文藝的代言人,長期受到壓抑的表達衝動是他們老驥伏櫪的內在驅力。電影上那些燃情歲月裡的英雄人物,或如赫拉克勒斯般揮荊斬棘,或如普羅米修斯般茹苦領痛,是謝晉《啊!搖籃》、謝鐵驪《大河奔流》、成蔭《拔哥的故事》裡永恆的主體。在這英雄落幕的歷史時刻,「菲勒斯」以父之名傲然挺立於電影中央,流露出敘事者略顯悲壯的英雄情結和揮之不去的懷鄉夢,滿足了其壯志未酬、英雄遲暮的自我想像。歷史場景再一次滑脫為潛意識場景。這同時表明講述歷史並不是要真正回到歷史,而是製造有關歷史的集體記憶,從而淡忘歷史本身。一些敘事架空浩劫直接接續到「十七年」,比如謝晉《青春》。在某種意義上,它們開啟了「指認他鄉為故鄉」的敘述模式,新時期的尋根電影(如《城南舊事》)、九十年代的懷舊電影(如《陽光燦爛的日子》)乃至新世紀的歷史題材(如《歸來》)皆於此展開。
最後,這種創作無意識也滲透到了現實題材的敘事方式上。愛情生活和私人領域被國族敘事徵用,觀眾在烏托邦式的通俗喜劇中被轉換為國家建設的主體。
概言之,通過檢視後神話初年電影內外的敘事症候,本書試圖抵達話語與現實斷裂的源點。
薩特說:「存在先於本質。」一經付梓,本書既成不可改變的事實(或事故),其中優劣,諸位讀者批評指正。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79折$237
-
新書79折$237
-
新書79折$237
-
新書85折$255
-
新書9折$270
-
新書$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