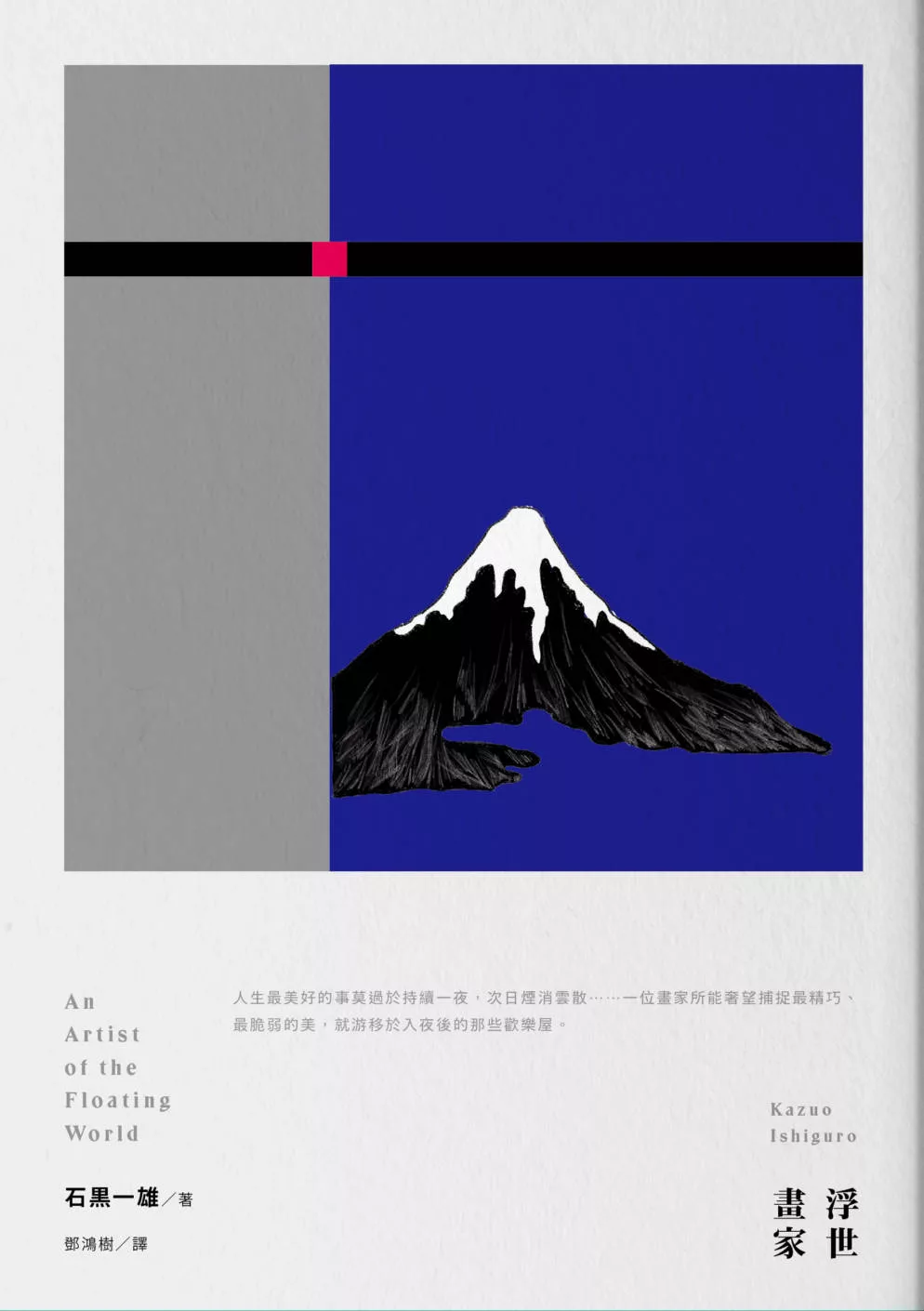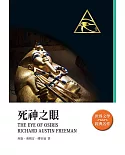序
浮游——讀石黑一雄《浮世畫家》
到達廣島時已是晚上,在「平和紀念公園」附近閒逛,天黑大霧,遠遠卻看見另一端横擱著原爆紀念館:一個墊高了的長方體,玻璃裡透出暗黄燈光。因電影《廣島之戀》之故,它在我印象中一直是黑白的,現實世界卻為它添上了顏色。兩天後到館內看展覽,礙眼的是講到二戰背景,提及日軍侵華時文辭間刻意地輕描淡寫。坦然面對歷史真難,剛在那天讀完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舊作《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對此正有深刻體會。
那是他第二本小說,背景設在一九四八年的日本,中譯《浮世畫家》,跟重視人間享樂的浮世繪相關。主角是畫家小野,出場時已是老人,住大屋,看來兼有名譽和地位。小野對二戰和繪畫有何想法,初段不太清楚,因他的唯一心願,只是幼女可早日出嫁,幾乎如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提及幼女相親一事,長女有天鄭重跟他說「要小心提防」,句子含糊,小野只聯想到自己不光彩的過去,擔心親家查起家宅,會找到他的朋友說他壞話,才逼不得已重訪故人。故事順著小野的第一人稱敍述開展,但他人老了記性不好,容易旁岔到戰前風光,有時卻更似推搪。小說的核心自然是:他戰時做過什麼,跟他的畫作有何關係?
石黑一雄把這重心隱藏得高明,讀來只約略知道小野曾犯錯,一直不知程度和原委。小說偶爾把小野的敍述和客觀現實並置,如錯版拼圖般格格不入之處,正透現這主觀描述之不足或扭曲,不可盡信;若無其事,或正因知道哪裡出了事,只不便細說。例如,他最希望探訪的,是從前最愛的學生黑田。探訪卻不是出於愛,而是恐懼,怕他中傷自己。要這樣提防自己最愛的學生,一定曾經種下巨大仇恨,那是什麼?不知道。我們只知小野連向友人查問黑田的地址也難以啟齒,到後來得知其地址和近況,卻心想,既然剛在大學取得教席,生活還不是很如意吧,幾年牢獄生活可能不全是壞事--這樣的自我安慰,不就已夠恐怖?及至走到黑田家附近,小野覺得他「did
not live in a good quarter」,語氣平淡。但接下來對環境的描述,如感覺像工廠、泊滿貨櫃車、鐵絲網外有推土機的噪音等,對比小野古雅的大宅,何止不好,簡直惡劣。但似乎唯有這樣自圓其說,小野才能繼續心安理得下去。
問題仍未解答:小野戰時究竟做過什麼?慢慢湊合前前後後零碎的故事,還是有眉目的:小野早年得浮世繪畫家老師賞識,拜其門下。老師有「現代喜多川歌麿」之稱,銳意改良傳統美人繪,縱情酒筵歌席,一心畫好在夜裡搖曳的燈籠火光。小野曾嫌老師生活糜爛,老師解釋,美好事物都是晚上聚合、早上消亡的,畫家要相信浮世的價值,才能捕捉那一瞬即逝的微妙之美。三十年代,在含糊其辭的「中國危機」(China
Crisis)期間,有人拉攏小野加入新組織,謂沉醉於浮世其實是避世,應用天賦呈現更真實的世界,譬如窮人苦況。小野暗中嘗試新畫風,終和老師決裂;那新組織認為社會問題源於天皇地位太低,政客和商家才能在國內上下其手,故有復興天皇的企圖。小野的畫風一再變更,畫中人從窮小孩變成士兵,背景也由陋巷轉成日本軍旗。小野這裡只仔細形容構圖和用色,從未用如「政治宣傳」等字眼歸納。但問題不止於此。借歐洲畫風改良美人繪的老師後來得到「不愛國」罪名而落難,小野則獲頒各式奬項而順遂,並加入國家組織,首章只提及「國家藝術協會」,到小說末處,寫小野當年到場為被扣查的學生黑田解圍,向警察亮出身份,我們才知道他原來還加入了「內政部文化委員會」,更是「非愛國活動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Unpatriotic Activities)顧問,負責舉報懷疑「不愛國」的活動,學生黑田才因此受到牽連,給投進監牢,畫作都給焚毀。
至此,一切似乎水落石出,我卻始終說不清小野是怎樣的人。他對藝術的追求應是真切的,這從他早歲學藝的艱苦可知。但他跟老師決裂時,真如他說,純屬畫風問題,抑或有實利考量?還是麻煩之處正在於,當時以為是個人選擇的轉向,正被軍國主義的潮流誘使而不自知?他在幼女相親時鄭重為舊事道歉,是懺悔,抑為權宜免得節外生枝?小野似非刻意誣陷師父和學生,卻又順水推舟,把他們送往死角。以大時代之藝術家為題的作品,有時著重其志向與堅毅,以時勢變遷凸顯其不變,寂寥、悲苦、光輝皆在於此。石黑一雄卻描寫了小野這樣一個畫家,在浩蕩的洪流裡分不清理想與現實,是有意點出,這拉扯才更貼近現實嗎?
欺騙自己是困難的,往往要騙了全世界才能回頭騙自己,正如小野總自言不在意名聲,要到故友一再稱許,他才邊推辭邊接受。但他慢慢也不得不為名聲而心神恍惚。別人是真忘記他了,大家對小野的過去已無興趣——不過是個畫家罷了。時代走得比他想像中快,報應不是譴責,而是遺忘,一切遮掩或懺悔都顯得多餘。誰都無意再回頭看他,以及他一幅幅精心的畫作。時代太急,個人對應不了更寛廣的世界而做了錯事,事後又沒法看清由來,便只能在殘缺的記憶裡永遠飄浮。
人真能從歷史得到教訓,抑或只會以歷史來教訓別人?不肯定。但五歲後便離開日本移居英國的石黑一雄,頭三本說都關乎歷史。首部小說《群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跟《浮世畫家》一樣寫戰後日本,淡淡筆觸卻寫出了陰魂不散的感覺。他在訪問曾說,那只是他想像中的日本,印象正隨年月消褪,希望在完全消失前用文字留下那珍貴世界。第三本小說《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轉寫英國,老聽差語氣得體地回憶尷尬的舊事,半生侍奉的主人原來是納粹德國同情者,主張英國行姑息政策而釀成大錯。石黑一雄幾本早期小說都有事過境遷的歷史感,在國家的成敗、潮流的消長以外,描寫如歷史沙石的主角而今那種暗淡,借小說回看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地方,不至在無知裡浮游。
香港作家 郭梓祺
原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七日
序
處子之心
世紀初,我在台北擔任中國時報文化版記者時,常跟大陸作家交往。上海小說家王安憶在大學開課的講稿《小說家的十三堂課》有一個概念,大意如此:「傑出的小說家在早期創作會出現一種『處女狀態』,在以後的作品此種狀態也會浮出、再現繼而昇華。」我欣賞安憶,常常想到她讀小說的視角。
我二〇〇六年結婚,冬天移民瑞典,自此參加每年諾貝爾文學獎宴會以及學院的年會盛典。二〇〇九年瑞典學院選出性情害羞四十五歲的詩人作家羅塔斯(Lotta Lotass)出任第一把椅子院士。我聽到院士恩達爾(Horace
Engdahl)說,「她寫得不多,很年輕的時候寫出創作者的初始狀態,寫得好極了。很可能寫了幾本書已經『寫完了』。世上很多好作家也有這樣的狀態。可是不要緊,我們需要這樣的院士。」
聽了心裡有些震動,我先想到霍拉斯說的初始狀態跟王安憶的處女狀態很相似。接著又想,文學思潮確實轉變了。一九一四年,瑞典學院的第一位女院士塞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她是一九〇九年史上第一位獲得諾文學獎的女性,台灣讀者知道她的兒童文學作品《騎鵝旅行記」,而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約斯泰.拜林的故事》,則是一部宏偉堂皇的北歐魔幻寫實小說。那個時代壓倒瑞典文豪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竟是個跛腳單身的女人,她可不簡單。人們曾驚奇瑞典學院發掘美國的寫實主義小說家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拉丁美洲的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中國的莫言,其實都有瑞典《約斯泰.拜林的故事》的文學基因,一種宏大的、鄉土的、幻覺與現實交錯的史詩小說。
新選院士入席瑞典學院是北歐文化盛事,代表一種新鮮的文學基因的植入,儘管羅塔斯選上院士只工作五年就隱居山林,離開學院,霍拉斯那一年的談話,隱然感覺是一種新思潮的轉變。不知我想得對不對。二〇一一年發給畢生只發表一六三首詩作的特朗斯特羅默(Tomas Gösta Tranströmer)。二〇一三年給了只寫短篇不寫長篇的小說家艾麗斯.孟若(Alice
Munro),二〇一六年則是美國歌手、歌詞詩人巴布.狄倫(Bob Dylan),跟過往選擇那些著作等身的大文豪的概念,確實不同了,視野清奇小品風格的作家也能進入正典文學的殿堂,以至於最近著作量豐富的美國小說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Milton Roth)以八十五歲高齡過世,出現一些責怪瑞典學院的聲音。
二〇一七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石黑一雄,是第二個出生亞洲以英語寫作獲得諾獎的作家,頭一個是一九一三年的印度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第一到第二需要花將近一百年的時間,中間有一個遺憾,因爲戰爭停發獎項錯過了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推薦英語寫作的林語堂。從一九〇一年第一次頒發諾貝爾文學獎到二〇一七年之間的亞洲裔有泰戈爾、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高行健、奈波爾(V. S. Naipaul)、莫言、石黑一雄。一百一十六年的歷史有七個人(我沒有算進一九六六年的以色列作家山謬·約瑟夫.阿格農〔Shmuel Yosef Agnon〕、二〇〇六年土耳其語作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使用英語、日語、漢語三種語言寫作。非洲裔有四個,其中沃克特(Derek Walcott)、索因卡(Akinwande Oluwole "Wole" Soyinka)、莫瑞森(Toni Morrison)都以英語寫作,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則使用阿拉伯語寫作。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一個世界文學的冠軍比賽,而是一個為了增加瑞典國民世界視野的文學獎,它就是一個北歐小國十八個院士選出來的文學獎,當前的十八個人會十六種語言,主要是歐洲的五種語言。要知道瑞典每一年出版翻譯的亞非文學作品佔總出版量不到百分之一。
石黑一雄不是一個瑞典媒體事先猜到的作家,卻是十八個當中的一個人等了快要二十年的人選。一九九八年第一次遇見悅然,他跟我預言這個人將來有一天會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沒有說過別的作家。今天我們回憶這個預言,世人會認為石黑一雄以六十歲得獎還算年輕。 悦然的看法是:「竟然要等二十年,可以大膽一點,早一點發給他。」
我很早以前讀過《群山淡影》、《浮世畫家》,當時讀得馬馬虎虎,只記得內容在講述戰後的日本生活。出國以前讀過《別讓我走》。以前我沒有多少人生經驗,現在我在遙遠的北歐成為白人社會的移民一員,家庭婦女,餘暇寫作,居住森林裡的老人社區,因為個人與家人疾病經常出入醫院。某個雪夜我看電視播《別讓我走》的電影,頓時感動不已。只有通過歐洲社會底層的生活經驗才能明白那些克隆人(複製人)生而只有一個使命:捐獻器官給人類,他們有人類的靈魂與肉體,他們忠誠的奉獻了自己的生命。這樣的敘述手法曾驚駭了許多文學評論家。
當石黑一雄來到瑞典領獎,媒體稱呼他是一個沒有「自我」的作家,這次我驚駭了,思考良久,身為一個歐洲人不會沒有「自我」,只是一個日裔的家庭,他的文化教養有著「忠誠」,這個現代歐洲人沒有的詞彙。現在的瑞典人之間階級平等,只講「信任」而無「忠誠」,忠誠還包裹了禮教的形式。個人以為,電視劇《唐頓莊園》劇情某些程度受到石黑一雄《長日將盡》的啟發,將忠誠的概念完整填進貴族生活的禮儀形式。
多年後,我重讀《浮世畫家》發現,石黑一雄寫作起步比較晚,卻一步到位。他的頭兩部描繪日本的小說裡頭,表現作者完好的「處子狀態」,而且日後他不再描寫日本的故事,朝向「國際性」作家的著作,都保持他的初始狀態找到所有寫作的元素:一個秘密、一團謎線、記憶不太清楚的事件,慢慢追索卻抓不到重點。當秘密終於揭露時,儘管無限感傷,還是要生活下去。
《浮世畫家》有所指向「浮世繪」,其代表日本匠人視覺藝術之最。小說主人翁曾經師從一偉大的藝師,他的美學後來轉變成服務愛國主義的宣傳藝術道路,因而離開師門,自創新路,極有成就。
故事一開始,主人翁很清楚地描述自己的社會成就與品德使他意外得到一棟美麗的莊園。從主人翁跟外孫相處的過程,我們知道家裡沒有一張他的畫。
因為戰爭之故,耽誤畫家的次女的婚姻,為了給女兒找出路,戰後略顯消極的畫家決定打起精神來拜訪故舊學生,我們慢慢會知道畫家在戰爭前後發生的那些故事。
畫家的老師曾指出最為美好而真實的那個靈魂世界往往在歌舞昇華,在夜間酒館,一瞬之間就消失,為了留住那個瞬間,畫師所有的精神必須嚮往那個瞬間。
戰後的日本藝術家呈現的安靜沉默就像城市裡大半消失的夜間酒館,戰後代表美國的民主意識主流掌握藝術的新發展,糾纏在老畫家個人記憶當中的是他在戰爭以前的愛國宣傳畫。一種怎麼看都不合時宜的美學,卻是他曾經引為驕傲的價值觀。
石黑一雄《遠山淡影》、《浮世畫家》都有一種相同的描述手法。以時鐘時間為經,主人翁的心理時間為緯。他後來的作品也常出現第一人稱敘述,兩種時間交織的方法,透露記憶的實在或者不實在。他的作品不多但是每一本書的寫法差別極大。
石黑一雄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提到,五歲離開日本,跟父母親到英國生活,他們每一年都以為就要回去日本,全家人在外過著英國生活,在家過著日本生活。在日本的祖父寄來日語雜誌書籍,母親給他講述過去的生活。我們在這兩部小說可以看見石黑一雄對日本的記憶。
作為二戰戰敗國的長崎家庭移民到戰勝國的英國生活,歷史現實感的反差極大。日後石黑一雄很少跟歐洲的媒體提到早期兩部描述日本小說,甚至很少講到現實當中他對日本在二次大戰扮演的角色。他不琢磨於戰爭的傷害,淡淡幽幽的語言,講的只是人與人之間過去現在相處的變化,著重藝術手法的表現。
石黑一雄曾經是英國的反戰青年、吉他歌手,去美國西海岸流浪、到蘇格蘭當社工人員。他當社工,訪問那些流浪無家可歸或者年長需要幫助的人,常常聽見他們描述自己的故事是那麼記憶模糊,經常想不清楚,邏輯混亂,卻是非常迷人好聽的故事。
他不樂意描述戰爭的責任歸屬究竟是誰。他只在乎當時這個主人翁如何感知他的世界。藝術手法高於歷史意識。可是歸根究柢,歷史意識仍然是一個基礎,他曾跟一個日本的文學評論家對話指出,日本遺忘二次戰爭加害者的歷史,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原子彈的扔擲,把受害者的悲劇擴大;二是在美國保護下,希望日本忘記過去,成為一個新的國家。從心理層次來看,日本社會情願遺忘,生活不能承載巨大的愧疚。然而,他的作品卻不願意著重在向讀者解說歷史,更大的層次是尋找小說的意義。
我很喜歡石黑一雄的《夜曲》那些老夫妻鬥嘴,為了利益結婚離婚的過氣歌星的故事。他自己說,當時寫不出《被埋葬的巨人》,轉而練筆寫作《夜曲》,寫出一個非常輕鬆的故事為什麼相愛,又為什麼不愛。繼而在《被埋葬的巨人》終於找到一種「故事」(saga),更接近原初文明起始的傳奇,遭受一條大龍呼出鼻翼的氣息所染,人民患了失憶的毛病。
二〇一七年,在斯德哥爾摩見到石黑一雄,看見他在學院演講時,敦厚有禮的模樣,我相信他是一個仁者。許多偉大的小說家叫我們記憶歷史,莫要遺忘,記憶歷史本身就是一個不背叛良知的作為。然而,石黑一雄有一顆慈悲溫柔的心,悲憫失去記憶的人,憐惜他們生活在愧疚的陰影下⋯⋯差別只是往後的作品在憐惜當中釋放出了更多的幽默。
閱讀《浮世畫家》,教我找到讀懂石黑一雄《被埋葬的巨人》的方法。從開始到最後的作品,作者始終保持處子的創作之心。
旅居瑞典作家 陳文芬
序
亂世的朦朧美學
二○一七年,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各界一致讚賞。他三十餘年的寫作生涯處理記取與忘卻的一貫主題,作品涵蓋歷史、科幻、奇幻三大範疇,文風壓抑低調,自成一格,廣受讀者喜愛。
石黑生於日本長崎,從小隨父母旅居英國。父親為海洋學家,原本計畫在英國從事短期研究工作,並不打算移民。石黑十六歲前,每年都被灌輸「明年會回國」的觀念。雙親為了要讓他適應未來的返鄉生活,在家中營造母語的文化教育。石黑在家裡不僅說日語,還定期閱讀從家鄉寄來的書籍,從小就對大人口中的祖國懷抱憧憬。
此非典型移民的成長背景培育出他的多元文化視野;從旅居成為移民的十年轉變期,則深深影響他日後的寫作方向。大學期間,石黑逐漸意識到腦海裡的「日本」實為情感的產物,早已不復存在。尋找人生方向之際,他突然感到一股衝動,希望能透過文字讓想像的國度得以永遠保存,以期在人生版圖自我定位。
《浮世畫家》為石黑第二本小說,淺顯易讀,字裡行間刻劃的情感卻洶湧澎湃,是體驗石黑創作哲理的最佳入門。故事背景設於二次戰後的一個日本城市,資深畫家小野料理女兒婚事期間,糾葛的往事不斷浮現,被迫重新檢視自我的人生價值。
小野年輕時不顧雙親反對,離家拜師學畫。他的師父藉由燈紅酒綠的「浮世」傳授活在當下的美學:「人生最美好的事莫過於持續一夜,次日煙消雲散……一位畫家所能奢望捕捉最精巧、最脆弱的美,就游移於入夜後的那些歡樂屋。」
燈籠下的享樂主義成為小野的藝術信仰。不過,友人的批評猶如當頭棒喝:畫家身處亂世,「若離群索居,力求完美無瑕的歌舞伎肖像畫,根本做得不夠。」他於是斷然與恩師決裂:「我不能一輩子都當浮世畫家。」
後來,小野轉而投身救國大業,畫下許多逢迎輿論的愛國主義畫作,許多人因而受到蠱惑。「勇敢的年輕人為愚蠢理念慷慨赴義」,戰後的家園猶如墓園。身為畫家的小野該如何面對歷史?要如何承認錯誤?
如道德哲學「雙重效應原則」(the principle of double
effect)所示,要評斷行動引發的後果好壞,必須考量做事的意圖。《浮世畫家》堪稱當代文學處理道德矛盾的典範。小野認為,他們這一代雖帶領國家走上歧路,但皆心懷救國大志,「不管做什麼,當時皆懷抱最佳信念」。因此,「出於善意而犯下的過錯,肯定是不需感到羞愧的」。可是,若善意的過錯足以亡國,有「作惡以成善」之嫌,又該如何看待為善的意圖呢?
《浮世畫家》闡釋,信念的侷限乃眾生苦難的源頭:歷史災難之所以不斷重演,正因每人都認為自己在做對的事。小野回顧人生所獲得的領悟,虛實之間善惡糾結難分,宛如恩師的早年畫作,亂世的朦朧燈火下,充滿「無從補救的瑕疵」。
台東大學英美系助理教授 鄧鴻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