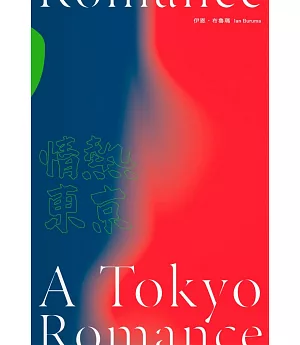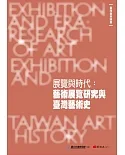導讀
無法成為日本人的外人,與需要靠外人塑造自身的日本人
對日本文化有興趣的讀者對於本書應該特別有感,寺山修司、鈴木忠志、唐十郎、大島渚、黑澤明、土方巽、麿赤兒、立木義浩、森山大道、荒木經惟,光是這些名字的羅列就令人振奮,因為就是這群人的縱橫交錯編織出日本戰後前衛藝術的圖騰,更何況這本書的每個字句,都來自作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臥底式」的觀察,不帶保留地暴露日本前衛藝術家們創作最核心的部分。伊恩是荷蘭人,他善用「外人」(老外)在日本所享有的特權,自由進出前衛藝術圈裏的各個角落。伊恩的經驗彌足珍貴,因為這幾個日本前衛藝術本家各據山頭,跟隨者凝聚在他們四周形成極度排外的小世界,一般日本人穿梭於這幾個團體之間幾乎不可能。在作者的描寫之下,這些前衛藝術家的生活顯得難以理解卻充滿奇幻,他們的世界時時跨越道德規範卻又生機盎然,作者將對這些藝術家的描寫交織在七〇年代東京這個奇幻都市的場景當中,色情電影院、有富士山壁畫的澡堂、便宜租金的同居房間、女體秀的舞台、帳篷劇場、六本木玻璃帷幕的豪華辦公室、和式廁所以及刺青師傅的小房間,「東京」被描寫成破碎不連續的許多角落,而每個角落卻又保留它們自己的時間。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一年之間的這段歲月,在作者的筆下彷彿夢境一般在眼前流過。對於理性思維的西方人而言,東京是超現實主義的空間,一個比任何現實都更鮮明的場所。
憑著不亞於藝術家的敏銳嗅覺,作者成功捕捉到日本「戰後」的氛圍。什麼是日本的「戰後」?它不單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時間的延續,更是日本人在「敗戰」後所面臨的持續狀態。廣島長崎上空爆發的原子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成立「聯合國盟軍駐日總司令部」(簡稱GHQ)管理日本,撤廢長久以來禁錮日本人民的「治安維持法」,並且釋放政治犯,頒布日本新的民主憲法,實施美國式的民主教育,在進行「東京裁判」同時,策動日本天皇向全國人民發佈「人間宣言」,自行撤銷在神道思想當中天皇的神性位置。對於日本人而言,所謂「戰後」,是「忠君」、「愛國」、「傳統」等,原本戰前所信仰、肯定的價值,在一夕之間突然成為否定的對象,在這種情境之下面對自我的不安與喪失感。另外一方面,日本在戰爭結束不久立即被納入冷戰結構當中,日本依附在美國的軍事庇護之下,利用韓戰與越戰發戰爭財,達成經濟高度成長。在尚未徹底追究戰爭責任之下,美國刻意讓日本戰後的政治體制溫存了戰前的政治勢力,對於戰後的日本人而言,繁榮的經濟生活是欺瞞的假象,其底下所潛藏的,則是更巨大的「美日同盟」政治力量。
作者在書中所描述的,是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一年這段期間在日本所遭遇的經驗。七〇年代後半,對於日本戰後而言是段過渡期間,然而,這種過渡的性格反而更能凸顯「日本戰後」的本質。就經濟而言,戰後日本滿目瘡痍,但因為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軍需讓日本的工業生產在最短時間內恢復運作,日本經濟在戰後急速復甦,一九五六年所發佈的經濟白皮書當中,「已經不是戰後」這句話似乎宣告日本經濟已經走出敗戰的陰影而進入軌道。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八年間,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達到十%,邁入所謂「高度經濟成長期」。但是到了八〇年代,日本高科技電子產品以及汽車大量佔領美國市場,導致美國工廠大量裁員,「日美貿易摩擦」問題引發美國普遍的反日情緒。而作者伊恩所經歷的日本七〇年代後半,是在日本經濟起飛,但「泡沫經濟」尚未形成,「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尚未爆發的短暫夾縫當中。
作者伊恩在日本的這段期間,日本電影「偉大的導演」的時代已經結束,製片公司已經無法以無上限的方式提供導演揮霍拍片。但是,在戲劇方面,七〇年代卻是日本劇場最「日本」的時期,日本戲劇捨棄對於西方現代藝術形式的外在模仿,開始進行文化根源的探求。儘管現代化與資本累積不斷改變東京的都市形貌,但是七〇年代的前衛藝術家們仍舊可以從東京都市邊陲找到殘存的「大眾的」、「陳舊的」、「非法的」東西。這些都市的殘留物是過去死亡的表徵,而前衛藝術家們卻從這些過去的、死亡的殘影找到新的可能。「敗戰」是一個民族對於過去自我的全盤否定,所以戰後日本的藝術家只能從過去死亡的屍體當中找尋自我的同一性。他們從過去死亡的灰燼、都市破敗的殘餘物當中創造出讓西方吃驚的前衛藝術表現形式。伊恩在東京所相遇的寺山修司、鈴木忠志、唐十郎、土方巽、大駱駝艦等,基本上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西方的藝術家對於他們的作品一定覺得既「前衛」又「日本」。
以寺山修司、唐十郎、鈴木忠志以及佐藤信等人為首的前衛劇場運動出現在六〇年代後期,這被稱為「地下戲劇」(アングラ)的戰後第一世代的劇場人,他們大多出身於學生劇團,以六〇年的「安保鬥爭」,以及七〇年的「學生運動」做為時代背景,他們的表現形式十分多樣分歧,但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於當時成為日本現代戲劇主流的「新劇」展開質疑與反叛。反映六、七〇年代日本社會的激烈氛圍,當時的前衛戲劇以徹底的激進為能事,就像書中作者所描寫的那樣,每場寺山修司的演出都是社會版的醜聞,而唐十郎的紅色帳篷則是綻放在新宿罪惡泥沼當中的毒花。但是,這世代劇場人儘管政治意識強烈,但是他們對於戲劇卻是純粹的。他們受到社會的關注,卻拒絕政府的資源,他們有一群觀眾的追隨者,對於「市場」卻不在意。這樣的戲劇環境到了八〇年代開始產生劇烈的變化。產生於六〇年代的「小劇場運動」到了八〇年代突然形成一股強大的潮流,看小劇場的觀眾層急速擴大。八〇年代中期日本社會進入泡沫經濟,炙熱的錢潮流入日本市場,不斷推擠日本人進行消費,在文化上造就出八〇年代的「小劇場狂潮」。當時具代表性的導演野田秀樹,他的劇團「夢的遊眠社」(夢の遊眠社)每一檔作品觀眾總動員數多達五、六萬人之多,這對於小劇場而言至今仍是個難以置信的數字。觀眾人數的暴增造成非商業劇場的小劇場開始走向「市場化」、「專業化」以及「職業化」。另外,自從一九八〇年日本總理大平正芳出版文化政策白皮書,宣告日本即將邁入「文化的時代」以來,日本的行政目標,將從「拼經濟」,轉移到「以文化為主軸」。之後日本政府對於藝文創作開始實施經常性的補助制度,八〇年代戲劇產業結構產生急遽的變化。對於作者在日本所接觸到的鈴木忠志、寺山修司、唐十郎、土方巽,麿赤兒等人而言,他們七〇年代末期所面臨到的是戲劇產業結構性轉換,同時也是戲劇理想主義的最後瞬間。
本書所有關於日本的電影圈、戲劇圈以及攝影圈,都是透過「老外」,尤其是以「西方人」的觀點所描述的,而這種觀點,無疑會「讓日本更像日本」。但是,作者並不企圖抹消自身的觀點,或者設法讓描述增加「客觀性」,相反的,作者在描述當中暴露自己「老外」的身份。作者善用自己「老外」的身份,自由進出於日本藝術圈,方便探尋東京角落,以及交日本女友,作者原本樂觀以為可以深入日本人群體的核心,但是最後發現在日本自己終究只是「外人」,作者將自身的遭遇赤裸地呈現在書中。或許,存在於西方與日本之間的「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才是本書的主題也說不定。
「老外」在日本的特權,除了歸因於自「黑船」以來日本對於西方文明所懷抱的自卑感之外,日本戰後對於自我的不安與喪失感更是重要因素。戰後的日本希望透過他者的眼光來重新建構自我,而藝術,雖然更複雜,但卻不例外。我們可以將《情熱東京》視為作者伊恩的「日本人論」也不為過。日本人際關係「內」與「外」的界線、集體主義的社會原則、「擬似家族組織」的劇團概念、以「禮節」作為社會秩序的原則、對於「日常」與「非日常」的區隔等等,作者以親身經歷為基礎,犀利剖析日本的藝術界。「老外」之所以被日本藝術圈接納,是因為戰後的日本人急於重建自我的需要,而對於「自我文化」的理解,本就必須透過「他者文化」。而這種「他者眼光」的代表,是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著作《菊花與劍》。
《菊花與劍》是在戰爭期間,美國警覺到自己對於這個奇特的敵國一無所知,因此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四年命令人類學家潘乃德對日本進行研究。潘乃德的研究有兩個值得注意之處,首先因為當時處於戰爭狀態,潘乃德在未曾踏上日本國土的狀態之下,僅憑藉文件資料,以及對於旅美日僑、日本戰俘的採訪完成這項研究。另外,這個研究是在戰爭的框架之下,在一九四四年的當時,美國已經預先看到戰爭的勝利,為了戰後對於日本的統治所需而進行研究。儘管如此,潘乃德的人類學素養讓研究超越戰爭的情境與文化偏見,以「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對於日本進行相對客觀的觀察。所謂「文化相對主義」是認為所有的文化都有其獨自的價值,文化的價值成立於文化的內部,因此無法以其他文化的價值標準加以衡量。潘乃德站在「文化相對主義」對日本文化的「特殊性」進行描述,其中尤其「集團主義」與「羞恥的文化」這兩點,對往後日本人進行自我文化的理解方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戰後出現大量由日本人所書寫的「日本文化論」或者「日本人論」,其背後當然是因為戰敗後的日本人自信心之自我回復。《菊花與劍》於一九四八年在日本翻譯出版,而潘乃德所描述的日本文化「特殊性」,成為戰後「日本文化論」日本人自我形容的特質。換句話說,美國在戰爭時期對於日本人特殊性的描述,成為戰後日本人自我認同的回復過程當中,自我構築時所仰賴的「他者視線」。在冷戰結構之下,對戰後日本而言,美國已經成為不可分割的「對」。如同六〇年代的「安保鬥爭」,在表面上是個「反美」的運動,日本企圖抵抗美國來建立自我,藉由「反美」的「否定性」來「自我肯定」。但是,這種「反」的構造,正如同大澤真幸所指出,在本質上卻只是反映出戰後的日本,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或者文化上,美國已經是「同盟」這個無可改變的事實。
所謂「東方主義」,是西方想像中的東方,並且西方將自身的壓抑以慾望的方式投射在東方想像當中。在「戰後」的結構當中,日美間的「東方主義」更以「性的慾望」形式所呈現。在終戰時期,就像是《擁抱敗戰》書中所刊登的,身穿傳統和服的日本女性迎接美國大兵的那張照片所顯示的,美國士兵與藝妓,以「纖弱柔順的女性」與「強壯可靠的男性」表象了美日的關係。但是到了八〇年代,在「日美貿易摩擦」的時期,日本人的形象成了「企業戰士」,戰爭時期日本軍人的男性形象再度登上美國人的想像舞台。伊恩在《情熱東京》書中不只將日本描述成慾望的對象,同時也描述暴力,那被以男性形象顯現的,一觸即發的衝突。最後故事以作者離開日本為結局。我喜歡這個結局,因為那是他者之間以慾望為開始,以暴力為結束,最逼近現實界的結局。
林于竝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