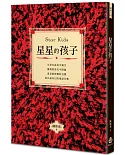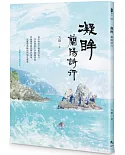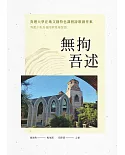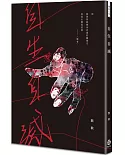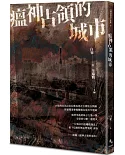推薦序
一個畫家的低唱──讀李承恩詩集《無人劇場》
楊智傑(詩人)
一個畫家死了,朋友走進他作畫的房間,發現他最後一幅畫。畫布上是一片空白,除了中央幾個模糊字母:那看不出是solitary(孤獨)還是solidarity(合群,原意為「在市場生活」)。卡繆小說描寫的這個場景,很接近我試著理解承恩詩歌的起點──當我們掩沒在以聲腔、姿態,口吻構成的主流詩歌浪潮時,李承恩似乎繼承了一種失傳的,寫實畫家般的冷門手藝──容我如此大膽的描述:那是台灣主流年輕詩歌中遺失已久的「景象」。
這些「景象」如何解讀?又有什麼意義?從細處看,李承恩寫「恍惚有些往事在暗夜/斷續成龐雜的飛塵,飄忽維持一種幽靈的平衡/越過桌上瓷器」,又寫「昨夜的蚊香沉滯不散/院外,一點車燈帶著警戒的紅由近而遠驟馳騁過」。時間的維度壓縮,讓空間在一個緩慢、巨大、可發酵並可觀察的量體中浮現出來。「反光像即將斷裂的線」、「粗糙的手即將再次彈過/最後一個音的時候」。似乎動了,然而沒動──記得在某個台北小咖啡館的下午,李承恩曾提到他想試圖「破除詩歌的線性結構,非以邏輯因果式的聯想推動詩歌進行」──誠然閱讀經驗總是帶著無可避免的線性特徵(包括圖像詩),但是藉由上述結構的「佯動」,藉由消除時序限制、敘述邏輯,李承恩掌握了使詩歌結構的整體共振成為可能的要素。
然而相對於對景的執愛、對凝視的瘋魔,承恩詩中的音樂性,我以為則採取了毋寧相對保守的策略──例如「我看見你在操場上行走/逐漸,我已經逐漸/領略那些晦澀的時光/恍惚間以為,那就是我」,以停頓、往復、長短句交錯的節奏操作模式,佔整本詩集的較多篇幅。不去對每一首作品作複調的延伸,有助於風格統一,有時卻因為近似的節拍帶來相似的情緒效果,致使部分作品的面目(如《午後練習曲》數首)較不能產生明確區別。
在《無人劇場》這本集子中,我尤愛彷彿靈光閃逝的人像素描。如輯四「班次之間的即興曲」作品〈深夜河堤〉:「橋上車潮散盡,燈光/在對岸如散場後的杯盤/金屬都已沉默。」介於繪畫與攝影術之間的幽靈,在結構中迴環出入。但不能僅將視線停止於這些光景的幻術之中,因為在作者本人與訴諸文字的詩句之間,仍存有一個獨特的抒情主體,一個少年,去「感受空氣裡的溫度,善變/透明,雪融在貓踏過的屋頂」。
那麼,若將《無人劇場》放在當代台灣詩歌的主流寫作中,那個習於展示傷口、乃至揮舞傷痛的「自我」,是否在場?然而關鍵終究在「自我」僅能依託於音樂(時間藝術)的線性流動,而非繪畫(空間藝術)的超然性注視中,猶如巴斯卡.季聶(Pascal Quignard)在小說《羅馬露台》(Terrasse a
Rome)中所細描,一名為絕望的欲愛所苦,因此專注於蝕刻創作的毀容畫師摩姆,客體化了他內心的深淵,傾注全部的表現力於二維的版畫藝術中。
更可以說,在承恩的詩歌精神裡,或在《羅馬露台》摩姆的毀滅性的創作意志前,空間不換取一切抒情所賴以寄託的時間,而是對抗時間。正如以蝕刻藝術對抗「我」的不定及匱乏,承恩同樣以其自外於「我」的詩歌景象抵抗、削除了當代那個浮腫、虛胖的抒情自我。
「陽光如浮躁的金屬/在水面上劇烈燃燒/爆破,如銅吼/沒有停止的跡象。」,即使我印象中的承恩,仍是一幅不善言辭卻急於辯論,敏銳卻寬厚,帶著強烈受困感的青年畫家肖像。最後,在這屬於聲音的時代,會有人把某個詩歌角落留給一個畫家的低唱嗎?無論如何,我更願意相信卡繆小說中畫家的最後一筆,那上面寫的是solidarity,而不是solitary。
祝福承恩。
楊智傑2018/05/31
推薦序
海底爬滿葡萄
蔣闊宇(詩人)
回想起來,我是在大學時代遇到李承恩的,一位讀著楊牧的纖瘦少年,中學制服底下卻藏著與他年紀不相稱的詩藝,令我驚異的天才。那段日子,我們曾在台大校園的杜鵑花樹下、在北藝大面向關渡平原的坂道,討論詩歌寫作的技術,分享一本又一本新出版的詩集,有時直到深夜。
讀著他晚近的詩作,好似書頁上的星辰,我不禁揣想,這十年的時光是如何琢磨著李承恩的詩藝與人生?
當年,我已驚訝於他詩中緣情體物的成熟技術,以及一種來自楊牧的、內斂的抒情風格;現在,我卻在內斂抒情的基調裡看見一種彷彿洛夫等現代派才會鑽研的意象控制技術,用它來進行「造境」,且其精準程度遠勝先前。然而,李承恩並不僅止於此,在這本詩集最好的一些詩句裡,更具創造性的,卻是把這種現代派的準確意象與造境運用成某種鏡頭、某種動態的電影,創造出一種生活中的、充滿細節與實感的、近似於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謂的「超真實」(hyper-reality)。
那些李承恩最好的詩句已不是古典抒情,也不從屬於現代派典範,而是透過細膩綿密的意象把詩歌寫得非常物質性,帶出某種直覺性的感受,但並不是不存在思想。李承恩到今天依然令我驚異,他讓我看見了跟我自己所慣用的抽象概念思考不一樣的、某種物理性的思想方式。
上面這兩段話可能讀起來不知所云。為了不要讓人以為我只是在用一些奇怪的術語捧李承恩,且為了明確指出李承恩詩作的特殊性,我將以剩下的篇幅詳細解釋它。
譬如〈波光〉詩中有句「陽光如浮躁的金屬/在水面上劇烈燃燒」,這在寫那些忘不掉的記憶,金屬大部分不會燃燒的,這種炫麗的鏡頭與「不可能」之感,恰如痛苦。而當陽光灑落在變動的水面,恰如陷於痛苦的人類意識掙扎於面對眼前的希望。又譬如〈變形〉詩有句「昨夜的昆蟲在牆壁上作夢」,用的是卡夫卡〈變形記〉的典故,描寫現代上班族的生活,越活越孬,像蟲一樣,簡稱為異化。然而即使依附在那堅硬厚實的體制之牆上,這隻蟲年輕的時候也有夢想,令人悲傷。這種直接可感,且與眼前景物融為一體的詩句,細緻、深邃,卻沒有現代主義的尖銳與奇崛,相反,好像只是某些生活中瑣碎的片段,好像所寫之物近在眼前,因而反倒有種日常的真實感。
這還只是單句的層次而已,隨著句與句的推移,單數句成為複數句,意象與意象間的更迭,李承恩便能在閱讀意識中動態地營造出一種分鏡與光影。這部分屬於詩的整體結構,要讀全篇,限於篇幅這裡就不摘引詩句了,讀者可以自行翻閱。譬如〈無人劇場〉如何在造境的變更當中,利用舞台光線的擴散與收攏,營造出繁華落盡後人生的寂寥,而收尾於最後一名觀眾關門離去的聲響。〈黑暗二十八行〉也是一首我很喜歡的作品,從女性身體中世紀的甬道,到愛情裡燃燒殆盡的灰燼,印象深刻。還有一個特別的例子是〈黑白即景〉,全詩讀不出微言大義,幾乎沒有抽象思考,美學與感情也者僅僅存在於意象與造境的推移當中,卻十分動人。這是高度技術本位的作品,除了詩藝,不靠其他。我甚至把詩集的最後兩個部分,午後練習曲與清晨前奏曲,看做這種技術本位的展演與磨練,當然這兩輯也有更多。
沒記錯的話李承恩後來有許多視覺作品,我想這種詩句大概和那種創作經驗相關。或許有人會說,這種直接的感受性,以及鏡頭推移之類,只是現代派意象技術的進階版而已,稱不上特別。是,也不是。這裡,我就要仔細分辨「意象」的用法。
意象的一種用法是意識流的,用來表現「心中物」,因而,讀者在讀的時候明確知道該意象並不是詩人眼前事物,而是心中概念的變現,現代主義多半是這種寫法。不會有人認為洛夫寫「棺材踢著虎虎的步子」的時候,真的在寫眼前一副棺材。另一種用法則是現實性的,我寫一樹梅,因為我真的看到了梅花,意象被用來表現「心外物」,只是所寫的梅花當然被賦予我心中的情感,古代詩歌與寫實主義常常是這種做法。前者不真實,後者好像比較真實。差別在於,文本內部有沒有暗示「我在寫實」,就會令讀者設想詩中意象有沒有在指涉「外在對象物」,這是一個文本內部虛構預設是否存在的問題。
李承恩的詩作兼而用之,然而,在詩集中最特別的一部分詩作裡,心景實景根本分不出來——他拆除了那個真實預設的判準。當區分真實與否根本不影響詩歌意義產出的時候,這些細膩的意象就變成了一種不必然指向「心中物」、也不必然指向「心外物」,某種彷彿可以獨立存在的東西,它就是物與畫面本身。無以名狀,暫且先用一個古老的經驗論詞彙來描述,意象已偽裝成純粹的「感性資料」(sense
data)。差可比之。
神奇的是讀者依然可以從意象中生產出複雜的意義,且它被詩人賦予了好多細膩的描寫,彷彿十分真實。在現代詩的典範當中,原本是心中所思賦予意象的「物」以意義,這裡反過來了,先有了眼前物,人才跟著物展開思索的旅程,從而流瀉出感情。這裡,我看到李承恩的那種強調感性的美學追求,以「物」為核心建構出一種直觀直覺的美學。那些光影,那些氣味,這種直接性,讓詩中的即物思考,有時比起抽象思考更有說服力。
這樣一種沒有客觀對象物,卻表現得如此真實的「再現」(representation),被布希亞稱為「擬象」與「超真實」。當然,李承恩的詩作並不是全然符合擬象的定義,但這是一個值得參照的概念,被我用來不精準地「指陳」詩歌中那種令我驚異,卻暫時無以名之的特色。我個人因為意識型態上是傳統的寫實主義者,期待在詩中讀到「知識」作為一種對現實世界的抽象概括,但李承恩自有其美感質地,他也是勞動者的子弟,從以前到現在,每當我與他及他的作品展開對話,都幫助我看見了世界的另一面。
無論如何,這是少年詩人的第一本詩集,我個人極度肯定這十年來李承恩在詩藝上對先前的突破,並抱著萬分熱誠,期望他可以在下一本詩集與下下一本詩集裡,融貫生涯經驗,運用技術寫出更偉大的作品。從技術性的「造境」進入到生而為人的「境界」。我個人深信詩藝可以承載這個世界的程度遠不止於目前所見,李承恩具備這般書寫技術,這種即物思維的技術,相信在未來可以應用在更多方面的題材。
記得有一天半夜,我騎著野狼載中學時代的李承恩回家。我們經過永福橋,頭頂上,一盞一盞昏黃的路燈向後飛逝,就像這十年。當我送他到家,一個狹窄的巷弄。我看見他背著我,步步前進的背影。我只想說,祝福你有一個美好的人生,但願這世界的苦難不會降臨到你的身上,希望你能與所愛之人廝守,在默默付出裡得到內心的安頓。祝福你,船艙堆滿所需,船桅漲滿了風,海底爬滿葡萄。
推薦序
時間的結構──讀李承恩《無人劇場》
郭哲佑(詩人)
我常常覺得承恩是不合時宜的。在這個速食的時代,凡事追求快狠準,但承恩寫詩追求的是景深、韻律與結構,不只是當下的聰慧巧思,還是背後心緒流轉的過程。這個過程並非是自我對話,承恩極擅於用景敘情,他所有的詩篇都不是落空,而是實在地呈現人被世界包圍的情境,比如這首詩:
昨夜有些雲層,長期
在夢境隱晦處滋長
以黏菌的密度構成
一種繁密難解的花紋:今早
溟濛的天色裡空間女神
彷彿來過,最寂靜處
陽光湧了進來,季節奮力掀轉
自她手中巨幅的布匹
密雜的思緒因此遽爾
歸位,裙裾在無雲的高遠處閃耀
──〈記憶〉
記憶在暗處匯集,在夢中洶湧,形成那些我們難以言說指認的世界的紋路,構成當下的自我。而「醒來」這個行為被形容彷彿有神翻轉、安排一切,致使在醒睡之間躁動的潛意識一一歸位,打開一個「空間」讓人們行走生活;最後一句尤其動人,陽光閃爍彷彿就是神的印證,時時提醒我們,每一個新的片刻,就是神蹟。整首詩以「雲」起,結在「無雲的高處」,結構完整,巧思遍佈,斷句音韻動人,就是一首「圓美流轉如彈丸」的小詩;重要的是,當中的情思鑲嵌在世界的結構之中,沒有一處流於耽溺自憐,彷彿無一句不在寫景,卻也無一句不把核心指向人的變遷挪移。
這種寫法,瀰漫在整本詩集當中。承恩擅寫意識與世界一同湧現撐開的過程,並時有驚人的創造力,比如寫初醒,他說:「概念尚未回到意識/──電線懸於半空/天色在途中,在超越/見證存在……」(〈清晨前奏曲8──「途中」〉用電線來同時指涉天色初亮與意識(資訊)流動之間的曖昧關係,在我有限的閱讀經驗裡從沒見過;又如寫自我與時間的關係,在對過往懷抱深情的同時維持堅毅,讓自我也領受時間的滄桑:「天冷了,心適合水流的溫度/是否偷偷拿出來洗滌/是否洗完,毅然不再放回去/時間在走/看明年流到哪裡」(〈迢遞〉),以水洗心,讓心隨時間一起冷冽,是否能減少一點與物相刃的傷害?或者把心掏出,就是傷害的最終了?
讀者應該可以輕易看出,在結構造句上,承恩的詩受到楊牧很深的影響。但是承恩絕非單純臨摹楊牧,這些語言在他筆下並非是刻意選用,而是成為自我思想的一部份,融入了自我經驗,隨著作者一起生長。故而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句子:「像教室裡一根生鏽的鐵釘/生鏽在剝落的牆面上」(〈昨天的歌〉)、「庇護過我的草地,不斷/纏繞的操場,晦澀的香/落於座位上,長成鮮豔的野莓」(〈無題〉),一些青春的澀味被包裹在複雜交織的句式中,形成一種老成甚至是早衰的少年口吻,與書中不斷出現的「女神」,情詩中輕盈的「妳」、往往未及言說的「我」,被操場、落葉、走廊所延宕的關係,一起構成某種少年式的緬懷與憂慮,這又是承恩詩作另一個迷人魅力了。
與承恩相識近十年,初識承恩時,我大三,他才高一,但他所寫的詩成熟度已不下於我,甚至與一些當代名家相比也毫不遜色。私下聚會時,我常常被他精緻深思的詩篇所震撼,甚而自嘆弗如。這十年來,承恩堅持創作,不斷琢磨詩藝,卻似乎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或許在這個時代,承恩的疏離、節制、繁複,不容易被看見,但詩不討好任何人,詩集出版之後,時間在走,我們看看它會到達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