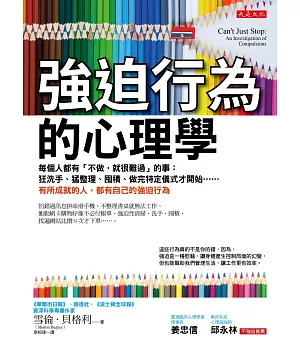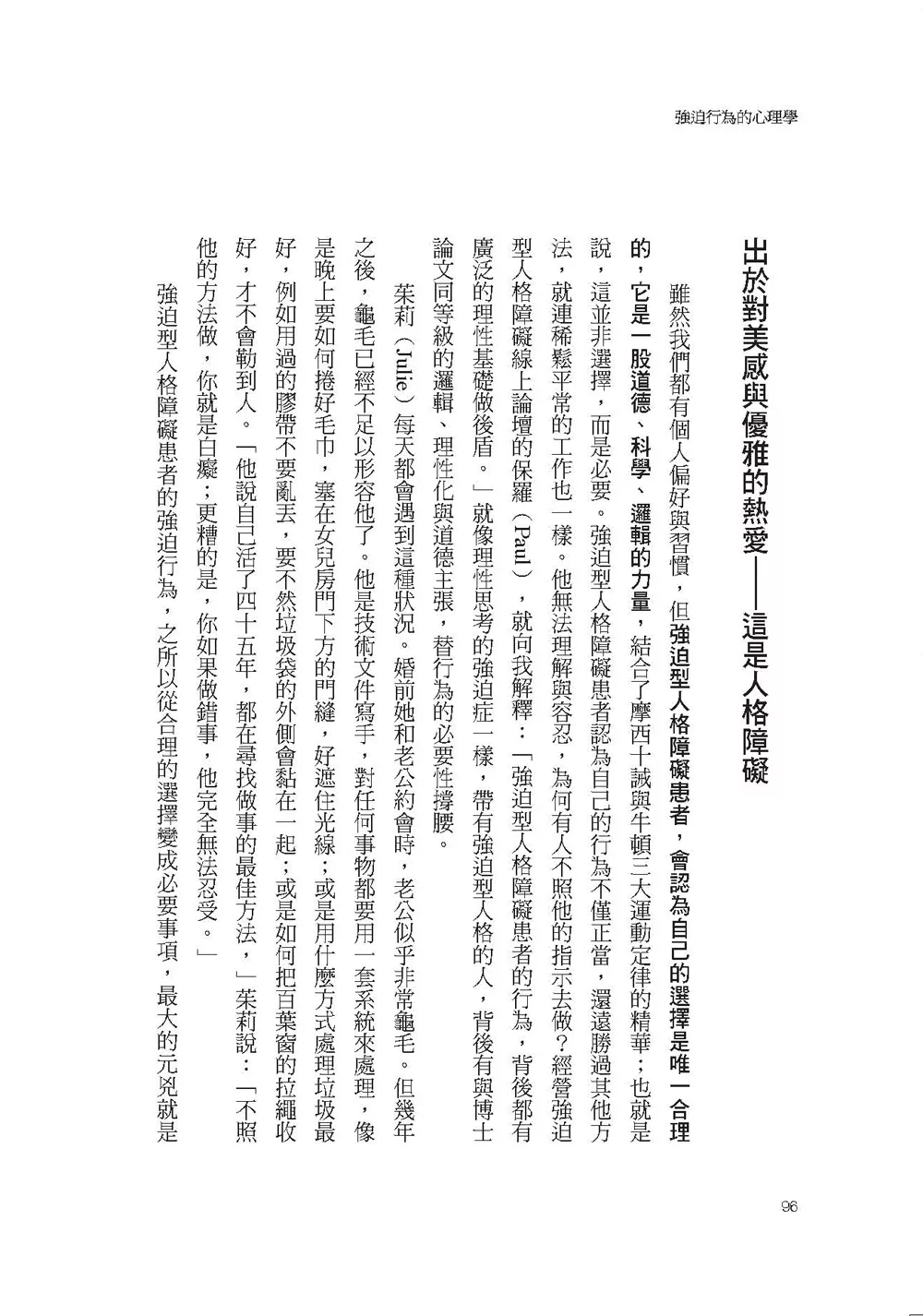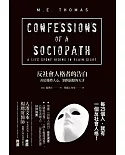序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強迫行為,為了化解焦慮(節錄)
當我開始寫這本書時,我把影響生活的強迫作用視為一種異狀,而且它幾乎到了令人害怕的地步:強迫自己反覆洗手的人;強迫自己打電動,打到大拇指抽筋的人;非血拚不可,導致循環信用到破產的人。但在我進行研究與報告的期間,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當我真正了解乍看之下像是瘋掉的人,我發現他們的強迫行為並非完全沒道理。相反的,他們的強迫作用,是因為擔憂某些事物可能將他們生吞活剝,而產生的可理解反應。他們並不瘋狂,甚至連崩潰都談不上;他們在應對,讓自己保持專注,而且比起讓焦慮吞噬他們,這麼做說不定還比較有用。
當我聽了越多囤積癖(譯註:過度收購或收集物件,即使是不值錢、有危險性或不衛生的物品)的動人故事,我發現自己思考的面向也越來越多。是啊,如果我也有一樣的經歷,那麼我家也同樣會塞滿雜物,只為在自己與絕望的深淵之間,築起一座堡壘。有強迫作用,並不代表腦袋崩潰。
我的第二個領悟是,雖然擁有極度強迫作用的人是異數,但驅使他們產生這些行為的焦慮,其實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主動平息焦慮的行為,是一種深沉且原始的衝動。這樣的體悟,改變我看自己與周遭事物的角度:乍看之下輕率、自私、具有控制性或傷害性的行為,現在似乎都像是對恐懼與焦慮的可理解反應。
有輕微強迫作用的人,並沒有達到精神病學上需要治療的程度,但感到恐懼的形式與症狀嚴重的人一樣,強迫行為對他們的效果也相同。只是越深沉、越嚴重的焦慮,就需要越極端(經常是自殘)的強迫行為來紓緩;而輕微的焦慮,只會讓我們手機不離手、只根據自己了解的規格來洗衣服,以及一定要用「這種方式」整理書桌。
把人變成這副德性的強迫作用,可說是千奇百怪,你能想像到的都有可能。
幾年前,阿姆斯特丹一位65歲的老人,引起了心理衛生診所的關切,因為16年來,他總是有股難以抗拒的強迫作用,想用口哨吹出嘉年華歌曲。「他老婆因為同一首歌聽了快16年而幾近絕望,只好向心理衛生診所求助。」荷蘭籍的精神科醫師,在2012年發表於《BMC精神病學》(BMC Psychiatry)期刊的論文中寫道:「他每天都要吹5~8小時,而且越累的話,吹得越難聽。」
醫師給「E先生」(醫師如此稱呼他)開了一種名叫「氯米帕明」的抗憂鬱劑,讓他一天「只吹」3~4小時,副作用卻難以忍受。當醫師們拜訪他家時,立刻就得面對「同一首歌吹不停,曲調清澈完美,幾乎毫無間斷」的狀況。醫師們開始探詢E先生是否真的得了強迫症(譯註: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簡稱OCD),但他向醫師保證,自己吹口哨的強迫行為,並非受到沉溺的想法所驅使。「不過,如果別人要求他不要吹的話,他還真的會覺得很煩躁、焦慮。」
連強迫性吹口哨都有了,那強迫性挖洞有何不可?英國的「鼴鼠人」威廉‧雷托(William
Lyttle),就有一種強迫作用,使他在倫敦東區的自家底下,挖出又大、又深、又迂迴的隧道。這條隧道總長60英尺,有些還深及房屋(繼承自父母)下方26英尺。他在2010年去世前不久,向記者如此表示:「一開始只是想挖個地窖,結果地窖變成兩倍大。」地方政府當局害怕房子垮掉,只好把雷托趕出去,接著工程師從隧道裡頭,移出了三十三噸重的破瓦殘礫,以及三台車、一艘船。
這種極端的疾患,或許會讓人覺得強迫行為是別人家的事,只有極少數人需要擔心這種精神病。但資料顯示並非如此。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科學家,在2006年的分析報告中發現,16%的美國成人(約三千八百萬人)都曾有強迫購買行為,而且其中有2~4%(最多約九百萬人)有囤積症(compulsive
hoarding)。不管是在哪一年,我們之中都有1%的人飽受強迫症之苦,這種病可說是眾多焦慮症中的黑暗王子。
至於有輕微強迫作用,也就是不嚴重妨礙健康、不足以被認定為精神病的人,甚至還更多;事實上,有些強迫行為還挺受用的,它們協助我們管理生活,或讓工作更有效率(起碼自己這麼覺得)。你應該不太會認識口哨吹不停、挖隧道挖不停,或是斷層掃描掃不停的人。但我敢跟你打賭,你應該認識不少人,早上醒來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機……更誇張的是,某位幹勁十足的作家經紀人,一動完開心手術就在找手機。我們的強迫行為輕微到沒人發覺,必須更仔細觀察才會發現。
你也可能認識像是艾美(Amy)這樣的人——我在餐廳和她見面,當時她是神經科學系的研究生,也是強迫症支援團體的創辦人。當我走近餐廳,並沒有多看一眼這位站在73街轉角的女性。我瞄到她的黑色秀髮,覺得這位美女絕對不是我的會面對象,因為她要和我談的是拔毛癖(拔毛拔過頭,使患者變禿的症狀)。
不過遲疑了一陣,她終於叫住我。「請問妳是雪倫嗎?」「妳……妳是艾美?」
吃完主菜後,艾美說她從十二歲開始就會拔頭髮,她說:「這變成我緩和焦慮的方法。」她的壓力來自於想在學業上表現優異,以及獲得紐約某間明星理工高中的獎學金。她會戴帽子掩飾被拔禿的地方;十年來她放棄游泳,因為她無法克制自己拔頭髮,而且連腿毛與手毛都拔,拔到身上一根體毛都沒有,全身像蛇一樣光滑。儘管她因為拔毛癖而被嘲笑,但這種方法確實緩和了她無所不在的焦慮。「我被焦慮纏身,當它變強時,我就拔毛。這非常有效,讓我恢復正常,從壓力的頂層退到底線。」
在艾美的拔毛癖患者支援團體中,其中有位成員是警察,本來很愛打高爾夫,但不得不放棄。艾美說:「他每次看到握住球桿的手,就會去拔手背與手腕上的毛。」還有一位成員是拉比(譯註:意指猶太教的學者),他整個人被罪惡感吞噬,倒不是拔毛動作本身所致,而是因為他在安息日工作(他認為拔毛也算工作!)——嚴格遵守規定的猶太人,連燈都不敢開。
雖然遍覽這些極端的人類行為,總是讓我很入迷(可能是因為我覺得「好險這沒發生在我身上」),但這些強迫行為的故事,給了我一個領悟:我在這些故事裡,看到自己、家人、朋友與同事的陰影。我們或許沒有活得很極端,但這些故事,闡明了人類行為光譜中,最廣闊的中間部位——我們大多數人都身在其中。
這幾年來,我為本書進行研究與報告,發現我們的所作所為中,有許多並非追求喜悅或滿足好奇心,也不是出於責任感或自尊心,而是為了抑制焦慮——雖然這些行為不會被診斷為疾病。或許會留下舊書報,是因為少了它們,你的房間就像沒了牆壁,讓你備感緊張;或許埋首於一項專案,是因為這樣才能緩和侵蝕心靈的焦慮——你擔心若不這麼做,就會有許多危險的事,發生在自己、家人與世界上。或許你採購雜貨就和軍事計畫一般精準;或許你毛巾非這麼掛不可;或許你做家事和編排芭蕾舞一樣,連喬治‧巴蘭奇(譯註:George
Balanchine,美國芭蕾舞之父)都會翻白眼。
推薦序一
或許,我們都需要一點點「強迫」
現代的人常常一空閒下來,就會拚命滑手機;朋友聚會時,往往不是交談甚歡的景象,而是每個人都低著頭看著手機螢幕。有些朋友甚至會在出門前,來回確認瓦斯有沒有關、門有沒有上鎖。其實,這些接近強迫行為的狀況,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只是程度輕重的差異而已。
多年以前,曾有一位女性強迫症患者,由她的丈夫陪同前來求診。我細問之下才發現,最困擾這位女患者的行為,是她每天必須花五~六小時在洗澡這件事情上。每天從下班回家、做完晚餐、做完家事後,她就開始準備洗澡的種種儀式……。
右手扭開浴室的喇叭鎖(這時右手髒了),進入浴室,手按壓殺菌洗手乳(這時左手髒了),並打開洗手檯水龍頭,清洗雙手。
褪去全身衣物(這時雙手又髒了),徹底清洗雙手。
右手擠壓洗面乳(這時右手髒了),徹底清洗右手,洗臉。
右手打開蓮蓬頭開關(這時右手又髒了),再次徹底清洗右手。
右手按壓洗髮精瓶蓋(這時右手髒了),再徹底清洗右手,再洗頭。
右手按壓沐浴乳瓶蓋(右手髒了),徹底清洗右手,再洗上半身(沒有衣物遮蓋的部位要洗兩遍)。
右手按壓洗沐浴乳(右手又髒了),徹底清洗右手,再洗下半身(沒有衣物遮蓋的部位要洗兩遍)。
千萬別以為這樣就結束了!
接下來,則是用各種不同的清潔劑與用具,把浴室從地板到天花板(這不是形容詞,真的包括天花板在內)刷洗、擦乾。地板和牆壁每塊磁磚與磁磚之間的縫隙,經過她經年累月刷洗的結果,不僅潔白如新,而且還向內凹陷幾乎半公分。等到每天晚上完成這冗長的過程,都已經是五、六小時後的深夜了。
經過將近半年的心理治療,患者終於順利克服這惱人的強迫症。在治療的過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患者的丈夫所付出的耐心與溫柔。每週不間斷的溫馨接送情,加上對妻子的鼓勵與包容。這對於「看慣」夫妻冷戰熱吵的我而言,無疑是一幅清新美麗的風景。
事情到此,原本是完美的終結篇……。
豈料,治療完畢後過了一年,這位患者又回來找我。只不過,這次丈夫已經變成前夫,她擺脫了強迫症,卻換來憂鬱症。經過幾次諮商後,這才釐清頭緒。原來患者克服了強迫症之後,卻逐漸對丈夫的噓寒問暖感到厭煩。她則是多年以來首次感受到自由,經常下班後流連在外,棄丈夫於不顧,結果兩人最終以離婚收場。
類似的案例始終讓人迷惑:為什麼病治好了,家庭卻也散了?
有些家中有罕見疾病孩童的家庭,夫妻同心為小孩遍尋良醫、籌錢治病。一旦孩子不敵病魔摧殘,夫妻卻以迅速離婚收場。難道這只能簡單的用「共患難易,同享樂難」來解釋嗎?
或許正如本書作者書末的智慧之語:「許多行為之所以吸引我們去做,不是因為它們能帶來喜悅,而是它們保證能平息焦慮。」這裡指的焦慮或許也可能來自生活,等到焦慮平息了,隱藏在其下的問題,或許才是應該解決的課題吧。這不僅是對於強迫行為而言,或許也可以是針對生活而言。
我的朋友們,別再一味的敵視、抗拒強迫行為,而是應該反過來、試著理解冰山底下埋藏的焦慮,到底來源是什麼?這也是我們可以思考的一個面向。
兩岸知名心理諮詢師/邱永林
推薦序二
平和看待我們或多或少都有的「強迫行為」
這本關於強迫行為的新書,是美國資深科學專欄作家雪倫‧貝格利(Sharon Begley)的著作。她在書中洋洋灑灑的論述關於強迫行為的種種情況,在其活潑流暢的行文中,時見其獨到的見解、批判的厚度。
書中也談到許多關於強迫行為的情況,例如有位女患者總是會擔心她的貓跑進冰箱裡,即便她明知道這不太可能,但卻受不了大腦裡頭不斷呢喃的聲音,而一次又一次跑去檢查。或是像網球明星納達爾會用只有自己知道的儀式放水瓶,以特定的順序拿毛巾。
我個人在臨床心理的專業雖不是在強迫症領域,過去主要的臨床經驗,是在大學輔導中心接觸過的大學生或研究生,這些學生中有些飽受強迫症的困擾,而來求助。在有限的臨床經驗中,我主要以傳統心理病理學中討論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來看待他們所身處的困境,並提供協助。
狀況嚴重者,透過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及社會支持,我發現難度雖高,但若能積極持續前來,問題是能逐漸緩解。狀況較輕微者,在心理治療的持續工作中,我也發現他們一旦有了「悟性」後(也就是認知行為治療常說的想法改變),他們會開始訝異,為何這強迫意念或強迫行為,在治療前如此難以撼動?而強迫性的意念及行為,若在一定的適應範疇內,反而是成就的重要來源。試想哪位優秀的藝術家、作家、建築師、學者專家等,沒有這樣的思考及行為特質?若放大將其當作向度(dimensional)而非類別(categorical)的角度來看心理病症時,則會有很不一樣的理解。
本書的作者,就是將類別化的強迫症,擴大成向度化的強迫行為或強迫心理現象,前者是窄狹的病理探究,後者則是普羅大眾的心理狀態,這樣的思維使得她的寫作格局,可以悠遊於傳統到當代的腦科學、心理學、社會學甚至宗教文化學的角度來切入探究;也讓我們了解,或許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強迫行為,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有了這樣的歷史縱深能耐,又能以新聞記者人物採訪的專業,直擊一些關鍵學者、病人或病人家屬的對話(注意,許多有強迫行為的人,常常又是大明星、大選手等等),來貫穿在整本書的文字中,使得本書讀來令人興味盎然,充滿趣味與啟發性。
我個人喜歡作者說:「強迫行為平息各種大小焦慮的能力,其實是大腦賜予我們最棒的天賦之一。」我想都值得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反覆去想:身而為人,我們該怎麼不帶評價的,看待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的「強迫」!
臺灣臨床心理學會理事長/姜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