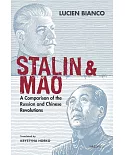中文版序
賈建飛將拙著《嘉峪關外》譯為中文,對此我甚感欣慰。我也非常榮幸拙著中文版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能夠讓更多的讀者一睹其顏。為了翻譯此書,建飛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尤其是為了術語和引文的精確,他查閱了大量的原始中文文獻和檔案,使得譯文在很多方面都較英文原文有了改進。因此,本書的中文和英文版本是可以相得益彰的。
《嘉峪關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1990年在北京進行的,本書最早的版本是我於1993年提交給斯坦福大學的博士論文。隨後,我對博士論文進行了修正,並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於1998年出版了英文版本。所以,本書的首次出版距今已將近二十年,距我最早開始寫作此書的時間就更久遠了。那時,在英文世界中幾乎沒有有關清代新疆的著述,在清史研究領域,新疆的地位一直非常邊緣。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家韓書瑞(Susan
Naquin)曾經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向我提出挑戰:「告訴我們清朝征服新疆對蘇州的百姓有何影響?」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劍橋中國史)中傅禮初(Joseph
Fletcher)的章節是當時僅有的有關新疆研究的新近作品;這些作品利用了傅禮初當時可以獲得的一些零散的多語種文獻,具有很深的洞察力,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視為是這個偉大的學者的巔峰之作。但是,由於傅禮初並未有機會接觸到清廷內部的檔案,因此有關清代新疆的很多問題依然無法解答。在英語世界中,我應該是第一個利用北京的清代檔案文獻對新疆進行研究的人,我的結論都是基於這些文獻以及當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友好和開放。
當然,自那時起,已經出版了一些有關清代新疆的英文著述(漢語的著述自然更多),如今沒有人會再懷疑這個地區在我們對清朝以及清朝作為一個帝國進行運轉的理解中的重要性。金浩東(Ho-dong Kim)的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中國的聖戰)是利用伊斯蘭、中文和其他語言的文獻,對阿古柏伯克政權進行的一部研究。事實上,在我寫作《嘉峪關外》一書的時候,金浩東的Holy War in China已經完成,只不過出版的較晚。吳勞麗(Laura Newby)的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 1760–1860(清帝國與浩罕汗國)利用滿文和漢文檔案,為我們講述了清朝與浩罕汗國的關係史。濮德培(Peter Perdue)的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中國西進)則從比較史的、泛歐亞的角度,論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與準噶爾戰爭中的軍事和政治歷史。近年來,賴恩.薩姆(Rian Thum)的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維吾爾歷史的神聖路線)精辟地闡述了在維吾爾語言tazkirahs中所體現出的歷史傳統,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在漢語和滿語文獻中不曾有過的新疆的歷史景象。另外,金光明(Kwangmin Kim)的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聖潔的中間人)對於拙著主要聚焦於漢、回商人的問題進行了糾正。金光明揭示了維吾爾精英在與明清的商業關係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強調了貿易對清帝國的形成的重要性。
我很高興這些著作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近代早期新疆的認知,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為這些作者能夠比我使用更多的滿文和維吾爾語的文獻。但是,我也很高興《嘉峪關外》的主要結論在二十年後還依然成立。
第一,商業貿易和商人對於清朝向中亞的擴張和將新疆整合入清王朝非常關鍵。從這個角度來說,很明顯「絲綢之路」一直都沒有終結。相反,遠程的交流已經延伸到了新的歷史時期,並使得中亞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聯繫在了一起。斯科特.列維(Scott Levy)與馬修.羅曼涅羅(Matthew
Romaniello)有關中亞和俄羅斯帝國的研究也從帕米爾的另一端對此進行了論證。人們可以認為在今天的中國和中亞、南亞以及西南亞之間擴張的商業和外交聯繫,包括「一帶一路」的提議,都是近代早期受到清朝激發下的全球化進程的延續。
第二,清帝國在新疆的統治十分成功。在整整一個世紀中,這個地區的人口得到了增長,經濟獲得了發展,大體上也保持了和平的局面。儘管在Makhdumzada和卓的派系之間存在本地化的教派衝突,但是並沒有發生反抗清朝的「聖戰運動」(jihad),在伊斯蘭教和北京之間也沒有內在的矛盾。十九世紀初期發生在喀什噶爾附近的變亂從來都沒有威脅到清朝在整個新疆的統治,整個地區一直保持了相當的穩定。由於清朝和伊斯蘭教雙方的靈活性,二者之間在思想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摩擦也得到了調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清朝並沒有要求當地的穆斯林蓄留髮辮。這是清朝統治者經過慎重考慮後的決定,不對具有象徵意義的宗教、服飾和身體外觀等事務進行干預。(清朝政策中的這種文化多元與中國政府在廿一世紀初期禁止維吾爾人蓄留鬍鬚、佩戴面紗或是限制齋月封齋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九世紀後期清朝喪失了對新疆的控制,這是內地發生的太平天國運動和其他叛亂的結果。這些叛亂使得清政府對新疆的白銀供應遭到中斷,導致了新疆地方官員的貪腐、剝削和暴政。在這種不穩定的氛圍下,陝甘回民叛亂擴展到了新疆,阿古柏伯克也從中亞侵入新疆。但是,在反抗清朝在新疆統治的叛亂中,宗教自身從未成為其中的起因。
第三,清朝在新疆的一個世紀的成功統治,證明瞭它在這個遼闊帝國中,針對民族多樣性所實施政策的明智。清朝統治者並不主張社會的同化,他們的統治理念不僅承認帝國的五個主要文化群體(滿、漢、蒙、藏和「回」)所代表的多元文化差異性,而且還在思想體系和政治上,通過標誌性的象徵和行政制度,主動接受和強調這種差異性。這與歐洲的海外帝國極為不同,也與今天一些人錯誤地認為漢化(sinicization)政策才是歷史的標準截然相反。事實上,乾隆時期對這種非同化理念的多重表述表明清朝的──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集權化的多元主義」(centralized
pluralism)並不只是統治的權宜之計:相反,正是這種典型的清朝認同的特徵,方才使得清朝能夠獲取這塊文化與民族多樣性的遼闊疆土並維持對其之統治,如今這一領土已經變成了現代的中國。後來,1980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由一些中國以外的學者提出了所謂的「新清史」,這在中國也產生了很多的爭論。事實上,在包括《嘉峪關外》在內的那些著作中所持有的很多觀點,已被如今的英語學術圈所接受,當然其中的一些觀點本身也再次得到修正──這些觀點也理應得到修正。無論如何,多數有關清史的英文著作,還有一些漢語作品,都已經或多或少反映出了我們對清代的民族性和帝國的重新構建。我依然記得當我們於1990年代在中國發掘更多有關清代新疆的歷史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老師們和我一起分享從檔案中所浮現出的新的、更為積極的清代形象時的激動的情形。遺憾的是,也有一些人視這種對清史進行重新思考的所謂「新清史」是對中國懷有惡意。和很多歷史觀點發生的變化一樣,今天為人們所知的「新清史」有關族群性和帝國的觀點,都是根據新的文獻和新的關注點而作的重新思考。這種思考並非是一個孤立的行為,而是包括中國史學家、檔案工作者和外國史學家在內的共同努力的結果。事實上,《嘉峪關外》一書的中文簡體譯本最初就是在中國官方資助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支持下出版的,只是由於和本書自身並不相干的原因,一直都沒有公開發行。
歷史講述的不僅是過去,也是今天。對清帝國的地理、族群和心理的疆界進行新的思索,將其視為一種靈活的文明、多樣的群體和一個現代的國家,對於加深我們對中國的理解大有裨益。新疆、西藏、蒙古、台灣和香港都在通過不同的形式將其與現代的中國民族國家之間的特殊的、有時候又顯尷尬的地位歸因於清帝國的遺產,這些都是偶然的嗎?對清朝歷史的坦誠的、無偏見的、周到的和創造性的考察,如何可以讓中國與那些地方和民族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和諧呢?
米華健
2016年1月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