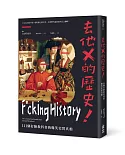《經濟學人》書評
據說,紙是在西元105年,由一位名叫蔡倫的宦官,在中國洛陽供職時發明的。蔡倫以桑樹的樹皮和植物的纖維研磨成漿,然後將其曬乾、鋪成片狀。紙的成本低廉、攜帶方便,而且可供印刷;它重量輕盈、可吸收墨水,而且質地強韌。在隨後幾百年間,紙已經取代了竹簡和絲帛,成為中國書寫文字的載體。
將近兩千年以後的今日,每年都有超過四億噸的紙張和紙板、報紙、大型紙箱和小香菸紙捲、牆上的廣告傳單和書籍被生產製造出來。本書作者孟洛對於這樣精疲力竭的一一詳述這五花八門的種類並不感興趣,他甚至對紙的用途裡,最重要的一種創發:紙鈔,也同樣沒有詳述的興趣。他宣稱說:「歷史上最有激勵振奮作用的思想理念,已經搭上(紙)表面這班便車了,」實際上等於是將前述這些可堪寫成專書的各種功能,只當成是陪襯的細節。
孟洛的焦點擺在他知之甚詳的中國。當希臘人和古羅馬人還在石碑上銘刻、在羊皮捲上寫字時,中國的讀書人已經在運用紙張了。到了西元四世紀時,中國成了一個紙張的文明,而佛教則成為第一個將經典書寫在紙張上,以向人們傳教的宗教運動。隨著佛教傳播到高麗(今韓國)與日本,造紙術同樣也傳到這些地方。
蔡倫發明的造紙術在751年的怛羅斯之役以後,開始了它向西方傳遞的過程;中國的軍隊在此役中,遭到阿拉伯阿巴斯的軍隊擊敗。中國的俘虜教導阿拉伯人造紙技術,到了795年時,巴格達有了一座造紙廠。在九世紀時,《古蘭經》一般已經以紙張傳抄,而不是寫在羊皮捲上了。
在歐洲,紙張的運用隨著1439年古騰堡發明活版印刷術而有了大幅躍進;印刷機成了強大的馬達引擎,造就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時期的各種文化思想、宗教和科學革命。馬丁‧路德翻譯的德文版《聖經》是第一本暢銷書籍。人權的概念透過書籍傳播;大眾傳播藉由報紙而得以達成。活版印刷術的發明,更加證明了蔡倫在一千三百餘年前的發明,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這使得孟洛得以在本書裡主張,紙的發明比起諸如電力、盤尼西林、玻璃或內燃機之類的創發,來得更加重要。
從紙鈔到盥洗室使用的廁紙(中國自八世紀開始使用),紙張讓人們的生活更加舒適,也使得理念思想的傳播更為便利。它的用處在這部歷史當中,更值得大書特書。另外一方面,電腦和網路的出現,構成了紙張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像孟洛這樣優雅追索紙的大歷史的書籍,終有一天會成為明日的陳跡。
導讀(節錄)
二○○八年北京奧運,中國重回世界舞台,迫不及待且雄心壯志地向全球展現自身文化,令人目眩神迷的文房四寶、竹簡論語與舞動的卷軸展演的,不僅是一個崇尚書寫與紙張的歷史文明,更隱晦地指出此文明自竹簡邁向紙張的軌跡。紙張作為書寫的平面與文字的載體,在數位發達的今日,顯得有些過時甚至岌岌可危。然而也拜科技之賜,這個圍繞紙張發展的文明及紙張本身,才能被展演至全世界的觀眾面前。這樣一個拗口迂迴的邏輯,與此番展演所聯繫的歷史、文明與全球,被《紙的大歷史》這本書的作者以一種更戀物、更懷舊、更宏觀也更鉅細靡遺的方式呈現出來。
本書的作者孟洛,在劍橋大學與北京研讀中文,對於中國歷史與紙張的熱愛在本書中表露無遺。在語言與文字的巴別塔中,作者試圖以紙張為媒介,黏合出一個世界性的文明地圖。或許是作者身上流竄著大英帝國的血液,因此關於紙張與發明者的故事,作者以一種世界帝國般的宏觀視野,熱烈繾綣地回望著一個遠方的文明;並以一種達爾文進化論式的視角,讓紙張從中國到全球的傳遞過程,緊緊呼應著世界文明的進程。紙張的傳奇,雖然自東亞發軔,得經由西方的認證才能完成。
本書第一章便是以馬可‧波羅(Marco
Polo)拉開序幕,《馬可波羅行記》中描述的元帝國,每天有一千輛馬車將白銀往京城裡送,並且擁有鍊金術般的紙鈔製造法。紙張在元帝國不只握有財富的象徵,也握有統治的權柄。此一橫跨歐亞的帝國靠著撰寫中文、藏文、波斯文與蒙古文等各種語言的敕命律令,治理著轄下幅員廣闊的疆域。馬上民族的驍勇善戰只能征服,得是紙張才能砌起一個帝國。這一切或許都要感謝千年前的蔡倫。
《紙的大歷史》顧名思義是在追索紙張從發明到發展的歷程,作者將本書的內容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紙張在東亞的故事,第二部分為紙張在中亞與中東的發展,而第三部分則為紙張在歐洲的凱旋。紙張的產生先決得是文字書寫的需求提升,並且讓紙張之前的書寫媒介屈居下風。因此,蘇美的楔形文字、埃及與中國的象形文字,以及其後衍生的語言巴別塔,為紙張的出現築建了舞台;而蘇美泥版的厚重、埃及莎草紙的脆弱,與中國甲骨青銅竹簡的不食人間煙火,則預告著紙張的登場。西元一世紀,皇帝命宦官蔡倫為皇家藏書閣整理圖書,為尋求更好的書寫材質以便詳加記錄藏書,蔡倫浸漬植物纖維來磨成紙漿,此番程序研發出來的紙張製作快速且易於使用。鄧太后青睞的這種「蔡侯紙」取代過去神祕又尊貴的青銅與竹簡等書寫載體,進入官僚體系與知識階層。竹簡成就了先秦的聖哲經典,卻也因為亂世中的散佚而遺失了經典。紙張的便宜、大量、易於攜帶與書寫自由,不僅能縫補秦朝焚書坑儒的傷痕,更打開了漢朝經典詮釋的話匣子。紙張的柔韌與親民性格更預示了隨後中國歷史的走向:一個書法的文明與佛教的興盛。
人稱書聖的王羲之,開啟了中國書法文明的璀璨篇章,據悉王羲之是從對天鵝彎下脖頸的觀察當中悟出運筆揮毫的技法。可想而知,承繼王羲之遺澤的中國書法,自當飽含生機氣韻與流暢優美。紙張的柔韌賦予中國文字表達情感的可能,更提供中國文人一方仕宦之外,得以吐納天地、揮毫己懷的自由空間。另一方面,紙張的親民性格則使其德澤遠及邊陲之地,如敦煌藏經洞所見證的。二十世紀初西方考古隊絡繹不絕地進入中國西北之境尋寶,讓此地數以千計的佛教石窟重見天日。其中,敦煌藏經洞中總數超過四萬兩千卷的手抄經卷,尤其驚為天人。
藏經洞中四萬多件的卷軸,幾乎全是紙張,佛教經文即占了五分之四。紙張書寫出一個佛教盛世,與一個靠文字與紙張便可得渡的信仰。抄錄經文、保存經文與供奉經文皆是功德,簡單重複的梵唄唱頌,亦可取代艱深晦澀的經文讀講。紙張成為佛教渡化眾生的信使,隨者佛陀的恩澤雨露灑向日、韓與越南諸國。韓紙、日紙相繼問世,紙張在這些國度不僅披上炫目的金銀華裳,更催化了在地文字的產生。
藏經洞中的經卷不僅數量龐大,使用的語言更高達二十幾種,漢文、藏文、梵文、波斯文、粟特文、回鶻文……,絮絮叨叨唱和出一個紙張譜出的大唐盛世。藏經洞如一個時光隧道,我們得以望而遙想各國僧侶、各式人種與奇珍異獸不絕於途的大唐盛世。在這一個盛朝底下,紙張進得了上層菁英的書閣,也出得了眾聲鼎沸的市肆;紙張承載得起聖哲的智慧、經典的重量、文人的情思、庶民的救贖與異國的旅程。如同唐朝的詩人白居易,藉著紙張,他可以文思泉湧成一名詩人,也可以經世濟民如一介儒家聖哲,亦可以抄錄謄寫如一佛門弟子。紙張至此,在東亞的故事即將告一段落。
藏經洞向我們預示了紙張即將開啟的世界旅程,而《馬可波羅行記》的出版,則證明紙張的旅程至少在相當於中國的元朝時已然在歐洲落腳生根。《馬可波羅行記》出版問世後二十年間,便出現另五種不同語言的新編版本。藉由紙張,馬可‧波羅筆下那個物資豐饒的帝國,讓西方心神嚮往,觸發之後的航海大發現,西方終於征服了世界。紙張在東亞統治帝國、書寫帝國,而最終在西方完成了它的世界霸權。而這個紙張霸權能夠環遊世界,還得仰賴《一千零一夜》的魔法地毯助其一臂之力。
如果說,紙張在東亞幫助佛陀普渡眾生的方式,是不斷地抄寫經文,那麼紙張在中亞成全阿拉拿下天下的方式,便是為《古蘭經》描繪美麗的扉頁。
紙張在唐朝已經遍布朝廷、士大夫、詩文、宗教與貿易市場,迎來了它在中國發展的巔峰。與此同時,不斷擴張的大唐版圖也在怛羅斯河畔與大食帝國(阿巴斯王朝的伊斯蘭哈里發帝國)短兵相接,大食帝國的軍隊在怛羅斯之役後所帶回的俘虜,將中國的造紙技術傳到了中亞,紙張由東亞往全世界的交棒傳播正式開始。
怛羅斯河流經之處,自古為商旅絡繹不絕的絲路。遠方物品經此輾轉買賣,異國風情的妝點,將能輕易為其標上奇珍與昂貴。相傳白居易為胡人之後,而胡服、胡服與胡毒,迄今仍是大唐電影《通天帝國》的吸睛之處。中國書籍在畏兀兒胡人手中自然也搖身成為神聖而充滿魅力的事物,即便以游牧為傳統的畏兀兒人大多不識字。然而,畏兀兒人在西域所建立的回鶻王廷尊摩尼教為國教,此一追求書籍之美的宗教,替畏兀兒在紙張西傳的故事中占了一席之地。
摩尼親自撰寫經文,因此摩尼教打從一開始便視書寫為極端神聖之事。摩尼教將書寫等同於靈魂,優美的字體必來自潔淨的靈魂。隨著驚人的傳播速度,摩尼教東至中國境內、西至北非,成為第一個世界性的宗教。遠比語言更能溝通世界的圖像便成為摩尼教經書的重心,因此,顏色、圖畫、幾何線條與花卉藤蔓爬上宗教的扉頁,藝術找到了救贖之處。摩尼教的美在中亞花繁葉茂,或許得力於早先在此地撒下種子的波斯。
伊斯蘭隨後強勢地征服了中亞十數個世紀,繁忙的貿易與遷徙自古為此地匯聚的多元文化,並沒有因此銷聲匿跡。縱使此地分歧龐雜的語言與文字,促使穆罕默德的女婿為了成就一個團結的帝國,而將阿拉伯文的《古蘭經》版本定於一尊。然而,中國的繪色、摩尼教的裝飾技法,以及受到影響的波斯細密畫,仍持續不懈地令《古蘭經》更加璀璨奪目。《古蘭經》上作者與繪者皆能留名,這樣的雙署名昭告著日後伊斯蘭經文與藝術共生的特質。當蒙古的鐵騎踏上這塊土地,興建起無數在陽光下閃耀著青綠光芒的清真寺,是鑲嵌其上的《古蘭經》文令其更加熠熠生輝,幫助起草設計的則是紙張。
隨著真主的神力日益遠播,《古蘭經》的數量也日益增加。伊斯蘭來自一個熱愛吟詠而對文字冷漠的民族,而最終這個宗教所締造的哈里發帝國,其統治基礎卻是一本仰賴紙張的經書。
王舒津(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版作者序
我在二十出頭的年紀時,曾經騎著馬、搭乘吉普車遍遊蒙古。這裡一片壯闊景色,而圍籬、道路和房屋,這些尋常的文明印記,在此毫無蹤跡。在離開以前,我已經在地圖上標記出所有和成吉思汗有關聯的地方,特別是他青年時期和早年崛起時經歷之處。
我到斡離(Onon)河去旅行,這裡是成吉思汗出生長大的地方。我跟隨他的人生進程,看著他逃離殺父仇人的追捕,充當馬賊直到有朝一日崛起於草原,在蒙古各部的一次大盟會上,升起氂牛尾製成的帥旗。
他完全沒有接受過教育,在各個定居文明的堂皇威嚴面前卻顯得毫無畏懼。然而這位有史以來最大帝國的創立者很快就發現,在以紙張施行統治時,帝國運作方能臻於至善。
在此時紙張已經遍及亞洲多數地方,但是它在十三世紀的歐洲仍是新奇而無足輕重的物事,還靜待著屬於它的時刻到來。
我在倫敦長大,說到這座城市,就令人想起那惡名昭著、而且還無休無止批評抨擊這座城市的報業媒體。它們在城市西側的弗列特街發展起來,這裡是舊日倫敦的金融中心。這是一座充滿書籍、雜誌和報刊的城市。我父親會穿著他那件細條紋西裝步行去上班,他一邊讀著舊式寬版《泰晤士報》,一邊還得忙著設法在街衢之中穿行─這可是一項須同時兼顧平衡、節奏和專注力的壯舉。不過,這樣的舉動在一座滿是由律師、詩人和匠師們所寫下、刊印出文字的城市裡,這並不是罕見的事情。
這本書說的就是我父親如何能夠讀到手中報紙的故事。它首先在亞洲開場,當中滿是皇帝、狂熱信徒、傳教士、詩人、激進分子、文官公僕、書法家、神學家、宣傳家和清潔工的記載。與其說這是由一群心志堅定的天才譜寫下的記載,不如說是一則關於識字大眾的故事,大眾閱讀的緩慢進展,先從亞洲開始,然後是歐洲,最終遍及全世界。
而最重要的,這本書說的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書寫平面,成為知識和理念傳遞者的故事。隨著這些思想理念受到更多的人們閱讀,它們在宗教和政治層面上,就受到愈來愈多的人們所信仰秉持。
即便我們已經減少對紙張的使用,我們的世界仍舊持續見識到它不可或缺的價值所在─紙張在多元社會裡的角色,與在由政府宣傳所主導宰制的社會一樣。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在一個由紙張所構成的世界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