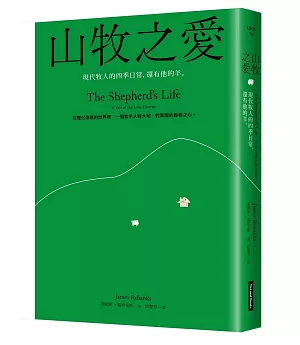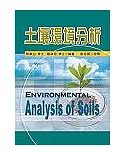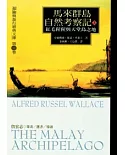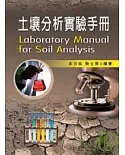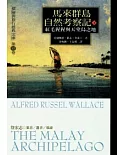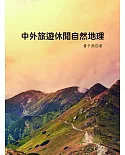留戀
一九八七年某個陰雨天的上午,我意識到我們不一樣,非常不一樣。我就讀城內的某所中學,坐在校內某棟六○年代風格的混凝土建築裡參加朝會。當年我十三歲左右,周遭坐著一群學業乏善可陳的同學,聽著一位年老的教師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不要一心只想著以後當農場工人、工匠、磚瓦匠、水電工、美髮師等等。她的滔滔不絕聽起來像已經重複多次的布道演講,她也知道這是白費唇舌,浪擲時間。我們就像父輩和祖父輩、母親與祖母那一代一樣,未來的前途早就注定好了,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其實我們之中也有不少人有足夠的聰明才智,但我們都無意在校內展現出來,那樣做只會惹上麻煩。
那位老師和我們之間隔著一道無法相互理解的鴻溝。介意前途的孩子早在一年前就去讀文法學校(公立重點中學)了,我們這些「放牛班」的孩子則是留在沒人想待的學校裡繼續混三年。結果是那些不抱幻想的老師和一些最厭倦學校、又膽大包天的學生整天在這裡玩諜對諜,游擊戰。我們全班會玩一種「把戲」,目的是在課堂上破壞最貴的教具,並把蓄意破壞搞得像「意外」一樣。
我很擅長做那種事。
地板上散落著故障的顯微鏡、殘缺的生物標本、搖晃的凳子、撕爛的教科書。一隻泡過福馬林、歸天已久的青蛙趴在地板上,呈現蛙泳的姿勢。瓦斯開關像鑽油平台那樣冒著火,窗戶的玻璃布滿了裂痕。老師淚流滿面地盯著我們,一臉崩潰。技術人員努力打理實驗室的亂象,以恢復元狀。有一堂數學課更妙,一名學生和老師上演全武行,後來學生衝下樓,逃之夭夭,穿越泥濘的操場,但被老師追上去擊倒,他努力掙脫以後才逃到鎮上。我們看著師生扭打,在一旁歡呼喝采,彷彿觀看橄欖球賽,看到球員撲上去抱擒對方似的。三不五時,就有學生意圖放火燒毀學校(但都沒有成功)。被我們霸凌的男孩,幾年後在自用車內自殺身亡。那感覺就像困在肯.洛區執導的電影裡:即使一個瘦弱乾扁的孩子突然亮出彈簧刀,大家也不會訝異。
有一次,我跟一臉震驚的校長爭辯。我說學校真的和監獄沒兩樣,而且「侵犯了我的人權」。他不解地問我:「不然你在家裡做什麼?」彷彿這題會問倒我似的,我回他:「我會去牧場上幹活。」我也一樣不解,他竟然不明白這麼簡單的答案。他無奈地聳了聳肩,告訴我別胡扯了,然後就轉身離去。每次有學生闖下滔天大禍,他就叫學生回家,因此我一直想拿磚頭去砸破他的窗戶,但遲遲不敢動手。
所以,一九八七年在那場朝會中,我望著窗外的雨做白日夢,心想自家牧場的人在做什麼,以及我不該坐在那裡,應該去做點什麼。這時我突然發現,這場朝會和湖區(Lake
District)的谷地有關,那是我祖父和父親放牧的地方,於是我開始注意聆聽。聽了幾分鐘後,我發現那個討厭的女老師認為我們太笨,缺乏想像力,無法「開創自己的人生」。她正在用激將法刺激我們發憤圖強。她說我們就是太傻了,才會想要留在這裡,做那些沒前途的工作,接受那些狹隘的鄉下觀點。這裡沒什麼值得我們留戀的,我們應該睜大眼睛看清楚。在她的眼裡,想要提早輟學去牧羊,簡直跟白癡沒兩樣。
她似乎無法明白,我們的父母可能是勤奮又有智慧的人,他們自豪地做著自己認為有意義、甚至令人欽佩的事。對一個只會從學歷、抱負、大膽及耀眼的專業成就來判斷人生成敗的女人來說,我們肯定是一群沒什麼前景的魯蛇。這所學校裡應該沒人提過「大學」這個字眼,沒有人想要離鄉背井。這裡的人一旦離開,對這塊土地就不再有歸屬感了。我們骨子裡都知道,他們離開以後就會改變,再也無法恢復元來的樣子。接受教育是一種「脫離」這裡的方式,但我們一點都不想脫離,我們已經做了選擇。後來我才了解,現代的工業化社會非常在乎「往別處發展」以及「開創人生」。言下之意是,留在家鄉幹體力活沒什麼出息,我後來逐漸痛恨那種觀點。
我聽著那個老師的說詞,越聽越惱火,因為她口口聲聲說,她熱愛這塊土地,卻又以我和家人都無法理解的說詞來談論它、思考它。她喜愛「原野」景觀,到處都是山巒、湖泊、休閒與探險,只住著一些我素未謀面的人。在她描述的世界裡,湖區是登山者、詩人、健行者、幻想家流連的樂園……那些人不像我們的父母或我們,他們是「真正有所成就」的人。她說教時,偶爾會以崇敬的口吻提起某個人名,妄想我們會有所反應。其中一個人名是旅遊作家「阿弗雷德.溫賴特」,另一個是登山家「克里斯.波寧頓」,某位叫「華茲華斯」的人的名字更是提了上百遍。
其實我從來沒聽過那些人,我想,當天朝會裡的學生也都沒聽過。
那次朝會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以這種方式(基本上充滿幻想)看待這片土地。當時我驚訝地意識到,我和鄉親熱愛的這片土地,我們扎根數百年的土地,這片所謂的「湖區」,竟然有人打著我幾乎無法理解的名義,宣稱這裡是他們的。
後來,我讀了一些書,觀察到「另一種」湖區,才逐漸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得知一七五○年以前,外界不太注意英格蘭西北方這塊山巒綿延的角落。即使注意到了,他們也覺得這裡貧窮、沒什麼生產力、原始粗獷、環境惡劣、醜陋落後。得知以前沒有人認為這裡美不勝收或值得造訪,我有點生氣,但是發現事隔幾十年外界對這裡完全改觀時,我又覺得很有意思。道路和鐵路陸續鋪設以後,大家更容易抵達這裡。浪漫主義運動及風景如畫運動改變了許多人對山巒、湖泊,以及我們這種崎嶇景致的看法。這裡的風景頓時成了作家和藝術家的焦點,尤其拿破崙戰爭爆發以後,遊客無法前往阿爾卑斯山,只好轉往英國的山間探索。
打從一開始,訪客對這裡的癡迷就是一種想像的風景,是一種內心理想化的景致。後來,這裡逐漸變成其他事物的對比(例如工業革命,那是發生在湖區以南不到一百哩的地方);或是用來闡述理念或意識形態的地方。對很多人來說,這裡從大家「發現」以來,就是讓人遠離塵囂的樂土,那些崎嶇的景觀和大自然可以刺激感官和情緒,是其他地方所無可比擬的。對很多人來說,這裡的存在是為了讓大家橫越、觀賞、攀爬、彩繪、書寫,或只是單純地夢想一番。這是很多人渴望造訪或居住的地方。
不過,最重要的是,我也得知我們的景觀改變了外在世界。這是第一次有人把一個概念訴諸於文字:每個人都可以因為某些地方或事物很美好、振奮人心或很特別,而產生直接的「擁有感」(無論他是否擁有產權)。一八一○年,湖區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提議,這裡應該是「某種國家資產,每個有目共睹、有心賞玩的人都有權享有」。如今影響全球各地的保育主張都是從這裡發想出來的。地球上每個受到保護的景觀、英國國民信託組織的每項資產、每座國家公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世界遺產的每塊地方,本質上都帶有一些同樣的理念。
我畢業後的那幾年,得知我們不是唯一熱愛這片土地的人。無論是好是壞,這裡在英國人及無數外國旅客的心中,其實是風景優美的遊樂場。我只要橫越丘陵到阿爾斯沃特(Ullswater),看著路上的車流或湖畔熙熙攘攘的人群,就可以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了。這樣的發展帶來了好處,也帶來一些不太好的結果。如今,每年有一千六百萬名訪客造訪湖區(在地居民僅四萬三千人),消費逾十億英鎊。這一帶半數以上的就業機會都在旅遊業,許多牧場的營收是來自於經營民宿或其他事業。不過,有些山谷地區,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屋舍是外地人的第二居所或度假屋,很多本地人反而住不起本地的房子。所以,本地人常心有不甘地說我們「寡不敵眾」,我們都心知肚明在這片土地上,各方面來說我們都是極少數的「少數民族」。有些地方感覺已經不屬於我們的了,彷彿賓客已經反客為主。
所以,那位老師對湖區的觀點,其實是兩百多年來城市化及日益工業化的社會所塑造出來的。那是夢想一個更廣泛的社會,裡面充斥著和這片土地毫無關聯的人。
對於在本地工作的我們來說,那從來不是我們的夢想,我們老早就在這裡做著我們該做的事。
我想告訴那位老師,她完全搞錯了——她根本不了解這個地方或這裡的人。這些想法隔了多年以後,才在我的腦袋中清晰明朗起來,但我覺得打從一開始,它就以籠統、幼稚的形式存在著。我也概略知道,如果書籍可以界定一個地方,那麼寫書就很重要,我們需要由自己所撰述、有關在地的一切書籍。但是一九八七年在那場朝會上,我才十三歲,尚未開竅,只懂得用雙手製造出放屁的聲音,博得眾人哈哈大笑,老師則是在演講完後氣呼呼地離開了。
如果說華茲華斯與他的朋友「發明」或「發現」了湖區,那跟我們家完全無關。一九八七年我回家以後,才開始問起老師說的那些事。打從一開始,我就覺得那種說法不對勁,為什麼這片土地的故事竟然和我們在地人無關?我覺得不合理,後來我才知曉這分明是歷史學家所謂「文化帝國主義」的典型案例。
當時我不知道的是,華茲華斯認為,牧羊人和湖區小農所組成的社群,在政治和社會上都是更有意義與價值的理想。這裡的人自我管理,不像其他地方受到貴族精英的主宰,華茲華斯認為這是一種良好社會的模式。他覺得,相較於英格蘭其他地方的商業化、都市化和日益工業化,湖區是重要的對比。即使在當時,那也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觀點,但是在華茲華斯的眼中,湖區是個充滿獨特文化與歷史的地方。他認為大眾日益欣賞這片景致時,訪客有責任確實了解在地文化,否則旅遊業會變成一股威脅,抹殺掉這個地方的獨特性。他在〈麥可,田園詩〉(Michael,
a Pastoral Poem)的草稿中(寫於一八○○年),寫了以下幾句後來被刪除的詩句,他主張這裡的牧羊人有截然不同的觀點,而且那些觀點本身別具意義。他的看法相當現代:
你若直問他是否熱愛山林,
他遇此屢見不鮮的貿然提問,
可能凝視著你,直言山林望之駭然。
但聊起工作細節及天地現況,
你會看見他思緒中雜糅著朦朧、驚奇與讚賞,
猶如內心孜孜所求。
但有好一段時間,我對這一切一無所知。我責怪華茲華斯忽視我們這些在地人,使這裡變成外人流連忘返的地方。
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文化概念與態度的影響。我對這塊土地的概念不是來自於書籍,而是出自另一個來源:一個更古老的概念,那是比我更早來到這裡的人所傳承下來的。
接下來的文字,一部分是說明我們牧羊人一年到頭的工作,一部分是我在一九七○年代、八○年代、九○年代的成長回憶錄以及當時周遭的人物紀實,例如我父親與祖父;還有一部分是從在地人的觀點,以我們代代相傳數百年的方式,講述湖區的歷史。
這是一個家族和一座牧場的故事,但也更廣泛地談到被現代世界遺忘的人們。我想藉此故事告訴大家,我們需要睜大雙眼,看看周遭受到遺忘的族群,他們的生活方式往往非常傳統,根植於遠古時代。我們若想了解阿富汗山麓下的人們,可能必須先試著了解英格蘭山麓的在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