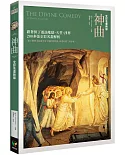《船長的詩》譯序 小我與大我之愛
1995年上演的電影《郵差》(Il
Postino),使拉丁美洲家喻戶曉的詩人聶魯達,變得舉世皆知。《郵差》故事內容講述流亡國外的聶魯達和義大利某小島上一名郵差之間的動人情誼。這位名叫馬利歐的年輕人,受僱為聶魯達的私人信差,也因此有機會結識詩人,進而走入詩的世界;聶魯達的詩作以及政治理念,像一根根透明的絲線,穿行於馬利歐的生活和思想,從此他的人生有了重大的改變。這部影片不但獲得了包括「最佳外語片」在內的多項奧斯卡金像獎提名,也喚起了世人對聶魯達的懷念和興趣,更掀起了重讀聶魯達的熱潮。唱片公司出版的電影原聲帶裡,還特別加進十四首聶魯達的詩作,請到了史汀、瑪丹娜、茱莉亞?蘿勃玆、安迪?賈西亞等著名影歌星來朗誦。這十四首詩中,多半是情詩,透過聆賞,我們重溫了聶魯達情詩裡知性和感性的交融,愛之喜悅與現實陰影的追逐,以及美麗與哀愁的對話。
《郵差》的背景應在1952年。陪著四十八歲流亡中的聶魯達,悠遊地中海島上的那位女士,是後來成為他第三任妻子的瑪提爾德.烏魯齊雅(Matilde Urrutia, 1912-1985)。當時聶魯達和第二任妻子卡麗兒(Delia de Carril,
1885-1989)仍維持婚姻關係,只能和瑪提爾德這位秘密情人偷偷幽會,飽受相思之苦。據說他幾乎每天都寫情詩給瑪提爾德,這些詩作於1952年結集成冊,於義大利那不勒斯匿名出版(只印了五十冊),名為《船長的詩》。1953年,阿根廷的出版社將之重新發行,多次再版,成為暢銷詩集。這本詩集以簡單、直接、強有力的筆法,呈現他給瑪提爾德的蜜語和怨語。電影原聲帶裡瑪丹娜唸的那首〈如果你將我遺忘〉,即出於這本情詩集。
聶魯達一生總共結婚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擔任駐巴達維亞領事時,對象是荷蘭裔爪哇女子哈根娜(Maria Antonieta Hagenaar, 1900-1965)。二十六歲的聶魯達寫了一封家書告知他父親︰「我覺得她樣樣完美,我們事事快樂……從今起,你不必擔心你的兒子在遙遠他鄉會覺得孤單,因為我已找到一位將與我白頭偕老的伴侶……」這段婚姻只維持到1936年。
1934年,聶魯達奉派駐西班牙,在馬德里結識大他二十歲的卡麗兒,彼此一見鍾情。卡麗兒的父親是阿根廷富有的牧畜者,她曾嫁給一位紈?子弟,過了一段荒唐糜爛的生活,遇見聶魯達時已是廣識畢卡索、阿拉貢等畫家詩人,政治嗅覺敏銳,機靈迷人,好客也好鬥的共產黨員。她很快成為聶魯達的導師,母親兼戀人。主動搬進他的家,鳩佔鵲巢,逼退原配。兩人至1943年始於墨西哥舉行了一項不為智利法律所承認的婚禮。
聶魯達與瑪提爾德初遇於1946年智利總統大選期間,在森林公園戶外音樂會中因友人介紹而認識。聶魯達幾乎忘了這次邂逅,瑪提爾德卻對之難以忘懷。1949年2月聶魯達開始流亡,經阿根廷至巴黎,莫斯科,波蘭,匈牙利。8月至墨西哥,染靜脈炎,養病墨西哥期間再遇瑪提爾德。她原在聖地牙哥音樂院,後離開前往好幾個拉丁美洲國家作巡迴演唱,曾在祕魯拍過一部電影,在布宜諾斯艾瑞斯和墨西哥當電台歌手,最後定居在墨西哥,辦了一所音樂學校。輾轉重逢的詩人與歌手如是開始了秘密的戀情。為了與詩人在一起,瑪提爾德必須躲在暗處,隨聶魯達、卡麗兒夫婦作平行旅行。1952年的義大利之旅,讓兩人恣意地度過了一段愉快時光。在卡布里島,聶魯達寫作了《船長的詩》,如前所述,匿名出版於那不勒斯。這是對瑪提爾德愛情的告白,但出於對結髮多年的卡麗兒的情感考量,遲至1963年他才承認是此書作者。
在以聶魯達之名重出的此詩集序言裡,他寫道:「有許多人討論此書匿名出版的問題。我也進行過自我辯證,考慮應否將之移出私密的源頭:揭露來源形同讓其私密的身世曝光。在我看來,這樣的舉動對狂烈的愛情與憤怒,對創作當下憂傷卻熾熱的氛圍,似乎有欠忠誠。我認為,就某些角度而言,所有的書本都應該匿名出版。究竟該將我的名字抽離我的著作,還是將之回歸到最神秘的著作,我在其間猶疑,最後,我屈服了,雖然不太樂意。為什麼長久以來我對此事秘而不宣?毫無理由卻也理由充分,為了這,為了那,為了不合宜的歡樂,為了異國的磨難。當Pablo
Ricci這位有見識的朋友於1952年於那不勒斯首次印行此書時,我們以為他極細心籌畫的這幾冊書會在南方的沙地消失無蹤。結果不是那樣。現在眾人要我揭開秘密,讓它成為永恆之愛的存在標記。我如是呈現此書,不做任何進一步的解釋,它彷彿是我的作品,也彷彿不是:它應該能夠自行穿越這世界並且獨力生長,這樣就夠了。既然我承認了它,我希望它憤怒的血液也會承認我。」
《船長的詩》共有四十二首詩(包括收於前四輯「愛」、「慾」、「怒」、「生」裡的三十九首較短的詩,以及壓卷的三首較長的詩),雖是聶魯達寫給瑪提爾德的情詩集,但其營造出的情感氛圍和其述說的語氣頗為繁複多樣:時喜時怒,時剛時柔,時而甜蜜時而怨懟,時而懇切時而焦躁。在詩集《地上的居住》第三部「西班牙在我心中」(Espana en el
corazon)和詩集《一般之歌》,義憤、激情填膺,以眾生、「大我」為己任的聶魯達,寫出充滿社會、政治關懷的「大愛」之詩,也寫出詛咒佛朗哥獨裁政權與惡勢力的「大恨」之詩;在《船長的詩》,我們讀到以溫柔深情和華美想像歌頌女體與性愛的「小愛」情詩(〈大地在你裡面〉、〈王后〉、〈陶工〉、〈昆蟲〉、〈失竊的樹枝〉等都是佳例),也讀到因嫉妒、誤解或懷疑所引發之帶有怒意、怨恨和憎惡的「小恨」情詩。譬如,在〈偏離〉一詩,他以冷酷、恫嚇的語氣道出背離他的愛人可能淪落的淒涼下場:腳會被砍斷,手會爛掉,雖生猶死;在〈永遠〉一詩,他語帶挑釁地宣稱:不管愛人曾經有過多少次情愛經驗,他都不嫉妒,他會將她過去的歷史溺斃河裡,拋諸大海,往後她只能永遠專屬於他,他們將「在大地上/開始生活」(像亞當和夏娃一樣),建立全新的愛情生活。青春期因失戀而黯然神傷的少年聶魯達,此刻是佔有慾高漲、霸氣十足的中年男子。
聶魯達在《船長的詩》裡不時展現此種「大男人主義」的姿態——以男性自我為中心,另一種形式的「大我」。在〈禿鷹〉一詩,他是盤旋空中的禿鷹,猛然將愛人叼起,要她隨他狂野飛行;在〈虎〉一詩,他對愛人說他是潛伏於森林、水域的老虎,伺機「以火、/血、牙的一躍,/伸爪一擊,我撕下/你的胸脯,你的臀部。//我飲你的血,逐一/折斷你的四肢」。在他筆下,兩性關係儼然是獵者與獵物的關係,身為男性的他充滿著操控和駕馭的慾望。不管在愛情的路上或生命的途中,他都是強勢的領導者,他要愛人改變原本的自我,追隨他的價值:「你必須改變心思/和視野/在接觸到我胸膛給予你的/深沉海域之後。……//我的新娘,你必須/死去再重生,我等候著你。/……從不受我愛慕的人/?變為我衷心愛慕的全新女子」(〈你來〉);「可人兒啊,請接受/我的憂傷和憤怒,/容許我敵意的雙手/對你稍事破壞,/好讓你自黏土再生/為我的奮鬥被重新打造」(〈傷害〉)。因為他親吻愛人的嘴肩負了更神聖的使命──替沉默的眾生發聲,他要擁抱的不僅是小個子的愛人,更是飽受苦難的眾生。
青春期的聶魯達喜歡用大自然的意象歌讚蘊含無窮魅力、展現多樣風情的女體,一如我們在《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所讀到的。寫作《船長的詩》的中年聶魯達依然以純熟的技巧讓女體與自然交融出動人的風情,但是此時他感受到的不再只是戀人的體膚,而是摻雜了「遼闊的祖國」的形象色澤,添進了「泥味」的愛情的滋味。他放大了情詩的格局,將視野自兩個人的肉體版圖和愛情小宇宙,擴大成為納入了「土地與人民」之疆域的大宇宙(〈小美洲〉)。在許多首詩裡,他讓愛情(個人的情慾經驗)和革命(集體的國族意識)這兩個主題產生微妙的連結。在〈美人〉一詩,他在歌讚愛人形體之美後,寫道:「你的眼睛裡有國家,/有河流,/我的祖國在你的雙眼裡,/我走過它們,/它們照亮我/行走的世界」;在〈你的笑〉一詩,他說愛人的微笑會「在最黑暗的時刻/綻開」,成為他戰鬥時手中的「清新的劍」,他要她的笑容像花朵一般綻放在他「回聲四起的祖國」。聶魯達的愛人除了是性愛的伴侶,心靈的寄託,更是他投身革命的動力,是與他並肩為社會正義奮戰的同志。在《船長的詩》裡,我們聽到了在大我之愛與小我之愛之間迴盪的戀人的聲音,戀人肉體夢土上吟唱的是和革命之夢同調的共和國讚歌。
《船長的詩》裡有不少詩很明顯是《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某些詩作的前奏或序奏,我們也可以將《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裡的許多詩作視為《船長的詩》詩集中某些主題的變奏或發展、再現。譬如頌讚瑪提爾德是「我的黑女孩和我的金髮女孩,/我的高個兒和我的小個兒,/我的胖女孩和我的瘦女孩,/我的醜人兒和我的美人兒」的〈多變者〉一詩,到了《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就變奏為第20首的「我的醜人兒,你是一粒未經梳理的栗子,/我的美人兒,你漂亮如風,/我的醜人兒,你的嘴巴大得可以當兩個,/我的美人兒,你的吻新鮮如西瓜」;〈你的手〉一詩中,聶魯達說其愛人的手「飛越時間而來……/當你將/你的手放在我胸前,/我認得那些金色/鴿子的翅膀」,「在我這一生/我四處尋找它們……/木材突然/帶給我你的觸感,/杏仁向我宣告/你秘密的柔性,/直到你的手/收攏於我的胸前,/在那裡像兩隻翅膀/結束它們的旅程」,而在《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第35首裡這相同的「你的手自我的眼睛飛入白晝」,「輕觸叮噹作響的音節,輕觸/杯子,盛滿黃油的油壺……」,「等傍晚到臨。夜悄悄地將它的天艙/置於男子睡夢的上方」,「……你飛翔的手又飛了回來,/闔上我原本以為不知去向的羽翼,/在被黑暗吞噬的我的眼睛上方」;〈不只火〉一詩中,「與肥皂和針線為伍/散發出我喜愛的/廚房(雖然我們可能無法擁有)/的氣味,你的手炸著薯條/你的嘴在冬日歌唱/等待烤肉出爐……」的「日常的小妻子」,在《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第38首裡再現為「屋子聽似一列火車/蜜蜂嗡嗡叫,鍋子在歌唱」,「上樓,唱歌,奔跑,行走,彎腰,/種植,縫紉,烹飪,鎚打,寫字……」的忙碌的主婦。
在〈亡者〉一詩,聶魯達對其愛人表示「如果突然間你不存在,/如果突然間你不在世,/我將活下去」,因為他還有重責大任,他入獄的兄弟們,他的革命同志和「偉大的勝利」在等著他,而在《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第89首裡他反過來對其愛人說「當我死時,我要你把手放在我的眼睛上:/我要你可親雙手的光與麥/再次將其清新傳遍我身:/我要體會改變我命運的那份溫柔。//我要你活著,當我睡著等你。/我要你的耳朵仍然傾聽風聲……」,在第90首裡他說「我想像我死了,感覺寒冷逼近我,/剩餘的生命都包含在你的存在裡:/你的嘴是我世界的白日與黑夜,/你的肌膚是我用吻建立起來的共和國」——在《船長的詩》裡視自己為「人中之傑」,不時惦記著自己偉大革命志業,對枕邊戀人曉以「大義」的鬥士聶魯達,到了《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裡,選擇體會愛情的溫柔,讓激情的呼喊變成自足恬靜、歡喜甘願的戀人絮語,讓用詩、用吻建立的戀人肌膚陰柔的共和國,取代用筆槍字彈、用雄心打出的天下。
《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譯序 光與陰影並治的愛的共和國
電影《郵差》原聲帶裡影歌星們唸的詩,有三首出自《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一首出自《船長的詩》,作為始末的則是《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中的兩首(第27與81)——這本大方、公開題獻給瑪提爾德的情詩集,是聶魯達於1955至1957年間寫成的。
1952年8月聶魯達結束流亡返回智利。他在智利有三處住所︰一在聖地牙哥的林奇街,與卡麗兒同住;一在聖地牙哥的普洛維登西亞(Providencia),為與瑪提爾德的密窩;一在聖地牙哥之北,智利中部太平洋濱的小村落黑島(Isla
Negra)。黑島本為一未開發之地區,僅有三戶人家,1939年,聶魯達在此購了一間簡陋的面海的石頭房子,大發奇想,稱其地為「黑島」,但它既不是島,顏色也非黑色。他輪流與卡麗兒和瑪提爾德同居於此,居然不曾被卡麗兒識破,直到有一天女管家向卡麗兒透露實情,七十歲的卡麗兒遂毅然求去。1953年,聶魯達開始建造他在聖地牙哥的房子「查絲蔻納」(La
Chascona)。1955年,與卡麗兒離異的聶魯達結束惱人的雙重生活,和瑪提爾德搬進新屋「查絲蔻納」同住,一直到1973年他死為止。他們曾在國外結婚,但直到1966年10月才在智利舉行婚禮,完成合法手續。
聶魯達與瑪提爾德曲折的愛的旅行,負載著光,也負載著陰影。《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出版於1959年,自然是他與瑪提爾德愛情的紀錄與信物。但比諸古典大師——譬如西班牙葛維鐸(Quevedo)、龔果拉(Gongora),義大利佩脫拉克,英國莎士比亞——所作,聶魯達的十四行詩大多未依循傳統骨架。傳統十四行詩對韻腳的講求,格律的設計,強化了十四行詩情感的密度與辯證的張力。聶魯達的十四行詩則每每鬆弛如一段散文,結構開放,思緒自然流動,發展。如他在書前獻辭所言:「我深知自古以來詩人們早就從各個面向,以優雅出眾的品味,為十四行詩營造出像白銀、像水晶、像炮火一樣的聲韻;然而,我十分謙卑地,以木頭為質料創作這些十四行詩,賦予它們那不透明的純粹物質的音響,傳送到你耳邊……」這些詩是木頭的,是質樸的,然而詩人說話的聲音卻自有一種黏合的力量,將這些詩行結構成完整的有機體——一間間包容詩人廣博、遊動的情思,「以十四塊厚木板」搭蓋起來的愛的小屋。
五十多歲的聶魯達在歷經社會及政治滄桑之後,終於在對瑪提爾德的愛裡找到了歇腳的地方:
親愛的,我自旅行和憂傷歸來
回到你的聲音,回到你飛馳於吉他的手,
回到以吻擾亂秋天的火,
到迴旋天際的夜。
我為天下人祈求麵包和主權,
為前途茫茫的工人,我祈求田地,
但願無人要我歇止熱血或歌唱。
然而我無法棄絕你的愛,除非死亡到來。
就彈一首華爾滋歌詠這寧靜的月色吧,
一首船歌,在吉他的流水裡,
直到我的頭低垂,入夢:
因我已用一生的無眠織就
手居住、飛揚其間
為睡眠的旅人守夜。
(第80首)
雖然聶魯達在這些十四行詩裡時而展露歡顏,時而動情地歌讚,但是絕少綻放出清朗的微笑,甜美滿足之中總夾雜著幾分苦澀與寂寥。他認為愛情有時候「是一座瘋狂城市,╱門廊上擠滿了面色慘白的人們」,有時候像一股巨浪,會將戀人們「推向堅硬的石頭轟然碎裂」,將他們磨成粉末,有時候又「拖著痛苦的尾巴,╱一長列靜止的荊棘之光」,因為現實的陰影無時不刻地盤據於愛情的背後奸險竊笑:
惡毒的腳步尾隨著我,
我笑,可怖的鬼臉模擬我的面容,
我歌唱,嫉妒咬牙切齒地詛咒我。
而那是,愛人啊,生命給予我的陰影:
一套空蕩蕩的衣服,一跛一跛地
追逐我,彷彿露出血腥微笑的稻草人。
(第60首)
但愛情儘管苦澀,卻是帶領戀人們飛出陰影的一對翅膀,是將混亂擾攘的世界屏棄門外的秘密城堡,是開啟被陰影關閉之門的唯一鑰匙,是唯一可與死亡、挫折、孤寂等人世黑暗相抗衡的力量:
在我們憂患的一生,愛只不過是
高過其他浪花的一道浪花,
但一旦死亡前來前來敲門,啊,
就只有你的目光將空隙填滿,
只有你的清澄將虛無抵退,
只有你的愛,把陰影擋住。
(第90首)
這本情詩集絕非一面倒的對愛情的歌頌,光與陰影在其中頡頏角力,相辯相成。對生命苦樂參半本質的深刻認知,賦予了聶魯達的情詩更豐富的質地,更繁複的色澤。雖然在某些時刻,他的愛情是荊棘叢中的玫瑰,是憂鬱的島嶼,是孤寂的屋裡疼痛的窗口,是掉入甜美的憂傷,是,充其量,緩緩長河脈動中的一滴水;但在更多時候,他的愛情是永不熄滅的火光,是無法折斷的纖細荊棘,是穿過生命之樹的奢華光芒,是拋扔於冰涼生命枝葉間的火。
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是一百次網罟撒向大海,企圖打撈愛的魚苗;是一百隻觸角伸向未來,企圖向時間追討永恆;是一百次巨浪拍岸,將詩人捲入洶湧險惡的現實,又將疲憊的他送回岸上——而瑪提爾德正是守候在岸邊的柔軟溫潤的草地。
一如他前兩本情詩集《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與《船長的詩》,聶魯達在這本十四行詩集裡大量使用與自然界有關的意象描寫女體,將瑪提爾德提昇成為紛亂人世裡美好秩序的象徵,一股安定靈魂的力量。她是大地,是結實纍纍的果樹,是飽滿的蘋果,是芬芳家國的泥土和樹脂,是熟稔的黑黏土,是野地的小麥;她是音樂、時間、雨樹,是沙子、木頭,布,是琥珀、瑪瑙,是邊界、河流、小村落,是透明的桃子,是溢出酒香的酒窖;她是生活,是芬芳的月亮所揉製的麵包,她的額頭、腿和嘴是被他吞食、隨晨光而生的麵包,她是麵包店的旗幟,是他的靈魂每日的麵包;她是美的化身,她赤裸的身體是月之線條,是蘋果的小徑,纖細如赤裸的麥粒,遼闊澄黃如夏日流連於金色的教堂,蔚藍如古巴的夜色,藤蔓和星群在她髮間駐留;她是人間最動人的風景,她穿山越嶺,像一陣微風,像湍急的水流自雪下滴落,是糾纏的藤蔓所統領的丘陵地,是荒涼的銀灰色大草原。她結合了水和大地的深沉本質,純淨如水又富含土香,使浪潮滿漲,種籽鼓脹——如同陰影跟隨光,她是他存在的最佳理由。
整本《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分成早晨,中午,傍晚,和夜晚四部份,季節變動的光影,死與生的形貌,愛之喜與悲的色澤,不斷閃現其中。這是詩人一日之作息,也是一生之作息。它是十四行詩歷史的一個陸標,不僅再次讓讀者見證到聶魯達滿溢的創作才氣,也為逐漸枯乾、僵化的古老詩體,注入新生的氣息。它神奇地將最屈從、最封建的詩體(十四行詩裡常可見為討贊助者歡心的騎士似的克己無私以及慇勤恭維)轉變成為一個丈夫日常作息、悲苦、隱私、憂思的備忘錄。它將一度忽而羞怯、忽而冷酷的情人,從中世紀城堡的高塔,帶進以「蠟,酒,油,╱大蒜」為武器,以「杯子,盛滿黃油的油壺」以及湯杓、鐮刀、肥皂泡為盔甲的中產階級廚房,聽著她「上樓,唱歌,奔跑,行走,彎腰,╱種植,縫紉,烹飪,鎚打,寫字……」。
聶魯達的十四行詩融合了優雅與鄙俗,永恆與當下,讓愛與死,光與影共同執政。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譯序 美麗與哀愁的青春情愛之旅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在九十年前出版時可謂突破了拉丁美洲現代主義和浪漫主義詩歌的窠臼,被譽為拉丁美洲第一批真正的現代情詩。如今這本詩集被譯成多國語言,在全球銷售已達億本,而詩中許多美麗的詩句在拉丁美洲當地像流行曲調或諺語般家喻戶曉地被傳誦著,也廣為世界各地讀者和寫作者引用,成為文學經典。這本詩集是聶魯達的第二本詩集,在寫作這些情詩時,他還只是個年近二十的年輕小伙子,就創作生涯而言,應該尚屬學徒階段,但筆端已然透露出銳利的鋒芒,詩中多處奔躍出樸拙然而動人的意象,笑中帶淚卻也一針見血地刻畫出愛的歡愉和痛楚。
這本詩集是青春期的聶魯達的愛情心路歷程,性的探索,愛情的惶惑、渴望與失落,無法獲致心靈溝通的焦躁,強烈的孤寂感……諸多複雜的情緒與思緒生動且赤裸地流瀉於文字之中。年輕的詩人企圖向世人宣告令他歡喜悸動的性與愛的體驗,更企圖為令他躁動不安的情感難題或心靈課題尋找安頓的力量。我們看到一名青年為了捕捉愛情的輪廓或釐清情愛的真義,時而歡喜歌唱,時而哀傷詠嘆;時而嘶吼吶喊,時而搥胸頓足;時而自我辯證,時而作繭自縛。這本詩集是歌詠愛情的浪漫獨白,是傷痕累累的愛的印記,是尋求溝通的心靈記錄,反覆誦讀這些詩作,似乎感覺一波波跌跌撞撞的生命浪花在心中湧動,撩撥起美麗與哀愁並陳的青春追憶。
聶魯達出生於智利中部盛產葡萄的帕拉爾(Parral),母親在生下他數週之後死於肺結核。兩歲時,他隨擔任鐵路技師的父親遷居智利南方偏遠的拓荒地區泰穆科(Temuco)。成長於原始森林區的聶魯達同年最親密的友伴是花草樹木和甲蟲、鳥、蜘蛛等自然景物,這樣的成長背景無疑在他日後的詩作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意義與影響。在《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裡,我們看到聶魯達信手拈來地自大自然擷取意象,營造出美麗與哀愁交融的愛的氛圍:「光以其瀕死的火焰包裹你。/出神而蒼白的送喪者,如是站著/背對那些在你周圍旋轉的/夕陽的古老螺旋槳」,「一束陽光落在你深色的衣裳。/夜巨大的根莖/突然從你的靈魂生長出」(第2首);「早晨滿是風暴/在夏日的心中」,「雲朵漫遊如一條條道別的白色手帕,/風用其旅人的雙手揮動它們」,「無數顆風的心/在我們相愛的寂靜裡跳動」(第4首);「夜鳥啄食初現的星群/星光閃爍如愛戀著你的我的靈魂」,「黑夜騎著陰暗的馬奔馳/把藍色的花穗灑遍原野」(第7首);「下雨了。海風追獵著流浪的銀鷗」,「水赤著腳走在潮濕的街上。/樹葉,像病人般,抱怨那樹」(第8首);「有時像一枚錢幣/一片太陽在我兩手間燃燒」,「總是在黃昏時拿起的那本書掉落地上,/我的披風像一條受傷的狗在我腳邊滾動」(第10首);「啊,走那條遠離一切的道路,/沒有苦惱、死亡、冬天在那兒攔截,/在露水中睜開它們的眼睛」(第11首);「風突然大叫,捶打我緊閉的窗。/天空是一張大網,擠滿了陰影的魚群。/所有的風在這裡先後釋放,所有的風。/雨脫掉身上的衣服」,「悲傷的風四處屠殺蝴蝶」,「風暴捲起黑葉,/搗散所有昨夜仍然停泊在天空的船隻」(第14首);「風在幽暗的松林裡解開自己。/月亮在遊蕩的水上發出磷光。/同樣的日子相互追逐糾纏」,「月亮轉動它夢的圓盤。/最大的那些星星藉你的眼睛望著我。/而因為我愛你,風中的松樹/要用它們的針葉歌唱你的名」(第18首);「夜綴滿繁星,/那些星,燦藍,在遠處顫抖」,「晚風在天空中迴旋歌唱」(第20首)。
【女體與自然景象】
在詩中,聶魯達也喜歡將女體與自然景象結合,讓她們化成為泥土、苔蘚、星辰、霧氣、露水、海浪……。在年輕詩人心中,女體似乎蘊含無窮的魅力,展現出多樣的風情:女人的身體有時是「白色的山丘」,是供粗獷如農人的男性開墾的大地,有時是「陸上的海螺」,有時由「使果實成形,麥粒飽滿,海草捲曲的太陽」塑造而成,有時卻像火苗四射、灼傷靈魂的「森林裡的大火」。她的肌膚柔嫩似苔蘚;她的雙手白皙光滑似葡萄,適合戴上他用話語編成的「無盡的項鍊」;她的雙臂時而清涼如花朵,時而透明如石頭,是他的「吻拋錨」、他「潮濕的慾望築巢」之處;她的膝蓋和陰部宛若「玫瑰」;她的腰身神秘如「霧」;她的眼睛有時是晚霞火焰的爭鬥場域,千萬道霞光在深處照耀,有時湧動如「燈塔四周的海水」,有時可見「暗夜的翅膀」在其中撲打,有時則是與陽光嬉戲的小溪留下的「兩潭幽暗的靜水」;她杯狀的乳房有時像「白色的蝸牛」,腹部睡著陰影的蝴蝶,有時散發出忍冬的芳香;她及肩的髮絲是由「黑色、渴切的太陽」滾動而成。在這本詩集裡,這類擷取自自然的意象處處可見,大自然儼然成了聶魯達專屬的巨型愛情隱喻貯藏庫。
「女人是什麼?」、「愛情為何物?」是年輕詩人在這本詩集裡不斷追索的主題。在有些時候,詩人在女人身上找到的是歡愉、安定、希望的象徵。女人是對抗孤寂的利器:「為了存活,我鍛造你如一件武器,/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彈弓上的石頭」(第1首);女人是生之源泉:「一個蒼白的藍色民族,剛從你/那裡生出,如是獲得滋養」(第2首);女人是有著「松樹林的遼闊,破裂的濤聲,/緩慢的光之遊戲,孤寂的鐘」的「玩具娃娃」和「陸上的海螺」,大地在她的體內歌唱(第3首);女人於他如「孤帆上的天空,山丘下的阡陌」,她的記憶是「由光,由煙,由平靜的水塘」所組成的(第6首);女人是在他靈魂中嗡嗡作響的「白色的蜜蜂」,讓他因蜜而陶醉;女人是他「最後的纜索」,牽繫著他最後的渴望,是他「荒地上最後的玫瑰」(第9首);女人是「風用發亮的葉子製成的東西」,是「在夜間群山後面,燃燒的白色百合」(第11首);女人擁有「宇宙的光」,是造訪花與水的「微妙的訪客」,他要「像春天對待櫻桃樹般地」對待她(第14首);女人安靜的時候「明亮如一盞燈,簡單如一只戒指」,彷彿是「默不作聲,滿佈繁星」的夜晚,她的靜默是「星子的靜默,如此遙遠而單純」(第15首);女人是「蜜蜂瘋狂的青春」,「浪的癡癲」,「麥穗的力量」,是「甜美而堅定的黑蝴蝶」,如同「麥田和太陽,罌粟與水」(第19首);女人如同一個「盛著無盡的溫柔」的杯子,將他包容在她「靈魂的土地」,在她「雙臂的十字架」,用雙臂收容他「黑色的孤獨」;在他飢渴的時候,女人是「水果」,在他心如廢墟的憂傷時刻,女人是「奇蹟」;女人「像一個水手般立在船首」,「依然在歌聲中開花,依然破浪而行」(〈絕望的歌〉)……。
雖然女人帶給他許多美麗的愛的回憶,但是在更多時候卻是他哀愁的源頭:她是「夢之蝴蝶」,只在美麗的夢境中飛舞,難以在現實中捕捉,她像「憂鬱」的代名詞;她是無法掌控的,她的到臨「如露水滴在花冠」般地柔和但短暫,她「像波浪一般,永遠逃逸著」,她有時「彷彿松樹」一般在風中歌唱,有時又「彷彿船的桅杆」,高高在上又靜默無言,有時會「突然傷感,如一次旅行」(第12首);她是他的渴望,卻也是他「無盡的苦惱」,「游移不定的路」,「流動著永恆渴望,繼之以疲憊,/繼之以無窮苦痛的黑暗的河床」(第1首)。愛情讓他「騷亂癡迷」,讓他心生恐懼:「對你的欲望何其可怕而短暫,/何其混亂而醉迷,何其緊張而貪婪」;愛情失落時,他是「蒼白盲眼的潛水者」,「不幸的彈弓手」,「迷失的探險者」,焦慮的「掌舵者」,被遺棄的「黎明的碼頭」,「廢料的底艙,溺水者殘酷的洞穴」(〈絕望的歌〉)。總之,對年輕的詩人而言,女人是「萬物的混合」,是難以界定的名詞。
1921年到聖地牙哥讀大學的聶魯達,離開了熟悉的家鄉,來到陌生的都會,孤寂可想而知,不斷地寫詩或許就是他對抗孤寂的一種手段,於是他在1923年和1924年連續出版了兩本詩集——《霞光》(Crepusculario)和《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他以愛情為題材,在情詩中大量使用大自然的意象追憶愛情,企圖以自然象徵生命的活力,用以對抗僵死、無愛的都會生活,但這些情詩多半在愛情的母題中融入孤寂、痛楚或毀滅的子題,營造出憂傷的浪漫,也傳達出孤寂的心靈渴望溝通的吶喊。在第7首情詩裡,詩人將自己比喻成遭遇船難的旅者,向愛人發出紅色的求救訊號,多麼希望她的眼睛能像燈塔一樣發出光芒指引他方向。然而,她的眼睛卻像是在燈塔四周湧動、頗具毀滅性的汪洋大海,他稱她為「遙遠的女人」,目光浮現出的是「恐懼的海岸」。他撒出「憂傷的網」,卻未能得到即時的救援,一如他發出企盼溝通的訊息未能得到回音,於是孤寂的他更感孤寂:「在最高的篝火上我的孤獨/蔓延燃燒」,只能像溺水者一般揮動臂膀自求生機。然而在失望之中,詩人仍懷抱著一絲希望:即便「夜鳥啄食初現的星群」,他愛戀著她的靈魂依舊散發出閃爍的星光,即便「黑夜騎著陰暗的馬奔馳」,他相信它還是會「把藍色的花穗灑遍原野」。
對當時生命體驗與智慧皆嫌稚嫩的他而言,女人與愛情無疑是個過於艱鉅的課題,因此他追憶愛情的時刻無時不是籠罩在惶惑、孤寂、不安與焦躁的陰影之中,第17首情詩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這首情詩一開始,詩人說:「思想著,影子糾纏於深深的孤獨中。/你也在遠處,啊,比任何人都遙遠。」愛情無法掌握的本質是詩人憂愁的源頭。他不斷追問女人「你是誰,你是誰?」他極欲探知她們究竟是由什麼樣的質地或紋路所構成的,為什麼與他的軀體繫在一起的會是「想哭的欲望」,為什麼讓他的靈魂「無止盡地滾動,歡喜,悲傷」?他不斷地思索愛情,卻不得其門而入,「影子糾纏於深深的孤獨中」,而女人的存在「彷彿物品一樣陌生」。他於是到自然尋求慰藉,為鬱積胸中的強烈情感尋找出口:「面對大海,在岩石間的吶喊,/自由、瘋狂地擴散,在海的霧氣裡。/悲傷的憤怒,吶喊,大海的孤獨。/脫韁,粗暴,伸向天際」,吶喊過後,他也只能「思想著,將燈埋進深深的孤獨中」。埋葬燈是一種儀式,等同埋葬希望,年輕的詩人面對複雜的愛情,幾經思索,疑惑依舊。這何嘗不是古往今來人類共通卻難解的生命課題?
【為飽和的情感尋找出口】
在情慾飽滿或情感找不到出口時,年輕的聶魯達在有些時候會直接表露他的悲喜憂歡,忘情地吶喊、嘶吼:「啊,乳房之杯!啊,迷離的雙眼!/啊,陰部的玫瑰!啊,你緩慢而悲哀的聲音!」(第1首);「你充滿一切,充滿一切」,「愛我吧,伴侶。別棄我。跟隨我。/跟隨我,伴侶,在這苦惱的波上」,「你佔據一切,佔據一切」(第5首);「那時,你在哪裡?/在哪些人中間?/說些什麼話?/為什麼全部的愛會突臨我身/當我正心傷,覺得你在遠方?」(第10首);「悲傷的憤怒,吶喊,大海的孤獨。/脫韁,粗暴,伸向天際」,「所有的根在搖撼,/所有的浪在攻擊!/我的靈魂無止盡地滾動,歡喜,悲傷」(第17首);「噢肉,我的肉,我愛過又失去的女人,/在這潮濕的時刻,我召喚你並為你歌唱」,「噢,被咬過的嘴巴,噢,被吻過的肢體,/噢,飢餓的牙齒,噢,交纏的身軀」,「啊,超越一切。啊,超越一切」(〈絕望的歌〉)。但在寫得最好的時候,我們看到詩人以精確、獨到、前後呼應的意象捕捉愛情的面貌,前面提到的第7首即是一例,第4和第15首是另外兩個佳例。
第4首情詩共有七節,每節只有兩行,卻隱含頗具想像空間的故事情節:夏日早上陣陣暴風吹襲(「早晨滿是風暴/在夏日的心中」),年輕的詩人和他的愛人在樹林子約會,他們看著天上的雲被風越吹越遠(「雲朵漫遊如一條條道別的白色手帕,/風用其旅人的雙手揮動它們」),覺得風像旅人一般揮動著白色的雲朵手帕,向世界道別。不過相愛的兩人即便靜默無言,內心卻狂野如肆虐的風(「無數顆風的心/在我們相愛的寂靜裡跳動」)。吹掃過樹林的暴風,對他們而言「如管弦樂神聖地鳴響」,彷彿是「一種充滿戰鬥與歌的語言」。狂風大作,瞬間枯葉紛紛落下,飛翔的鳥群一時之間也失去了方向(「以快速的偷襲劫走枯葉且讓/鳥群跳動之箭偏離了方向的風」)。風太大,他的愛人因無法站穩腳步而跌倒(「將她推倒在無泡沫之浪,無重量之/物質,以及斜傾之火中的風」);風無泡沫、無重量、無火苗,卻具有像海浪、像重物、像火一般的威力。他在樹下親吻她,試圖藉戀人的激情,對抗風暴的突襲,外在的威脅(「她眾多的吻爆裂並且沉落,/在夏日之風的門口搏鬥」)。在這首詩裡,詩人以他慣用的將自然擬人化的手法形塑情景交融的氛圍,而在第四到第六節,他以名詞片語取代句子,讓詩產生新的律動。詩中意念的鋪陳頗具層次感,並且以「風」的意象貫穿全詩,讓它時而溫柔浪漫、時而神聖莊嚴、時而粗暴兇猛、時而充滿威脅地以多種形貌呈現,成為愛情故事的背景音樂。
第15首情詩是一首用字輕淡、情感溫柔的詩作,糾結的情緒、濃重的愛的惶惑、痛楚的哀嘆彷彿經過某種洗禮頓時沉澱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耐人玩味的美麗與哀愁。詩人說愛人「沉默的時候」彷彿她不在身邊,彷彿她在遙遠的地方,這樣的時刻雖然或多或少蒙上一層憂鬱,但是他喜歡這樣的時刻,因為距離產生美感:她「彷彿在哀嘆,一隻喁喁私語的蝴蝶」;因為愛,愛人如影隨形:「由於萬物都充滿我的靈魂,/你從萬物中浮現,滿是我的靈魂」。愛人在沉默時,「明亮如一盞燈,簡單如一只戒指」——燈是希望的象徵,戒指是愛的信物,心靈的溝通有時是無需言語的;愛人在沉默時,彷彿繁星滿佈的靜夜星空,她的靜默是「星子的靜默」,「如此遙遠而單純」地守候著他。可是愛人如果一直都不說話,還是會讓他覺得「遙遠而令人心痛」的,因為彷彿她「已經死去」,那意味著永遠的分別。這時只要她說出「一個詞」或給他「一個微笑」,就能讓他感到歡喜,因為這讓他真切地感覺到她並非真的死去。整首詩的特別之處在於略帶疏離感的抒情氛圍的營造,以及兩種情緒拉鋸——享受距離騰出的美感又擔憂真正分離的痛楚——所產生出的情感張力。「我喜歡你沉默的時候」,「你彷彿……」和「你遠遠地聽我說話」這樣的句法在詩中多次出現,使得此詩更具音樂性,是一首值得吟詠再三的戀歌。
【情詩為誰而作?】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究竟為誰而作?詩人獨白的對象究竟是何人?這是許多讀者、學者、文學評論者和傳記作者相當感興趣的話題。聶魯達在他的回憶錄裡閃爍其詞地說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這些詩篇所指涉的女子主要有兩位,或許可將她們稱作瑪莉索爾(Marisol)和瑪莉松布拉(Marisombra)。Marisol是西班牙文mar y
sol的組合,意思是「海洋與太陽」,她是聶魯達在家鄉泰穆科西邊的薩維德拉港(Saavedra)度假時結識的女孩,彷彿是自森林蹦出的自然景物,有著薄荷的氣味,蕨類般的頭髮。他曾在潮濕的沙灘寫下兩人的名字,作成告示牌的形狀,公開卻又秘密地向世界宣告他們戀愛了。這段戀情在聶魯達到聖地牙哥讀大學之後還持續一段時間,1922到24年間,聶魯達寫了許多封信給她,並在放假的時候回鄉探望她,而她也曾到聖地牙哥和他見面。不過,最後因為地理上的距離、社會地位的差距和女方父母的反對,他們的戀情沒能繼續。這樣的結果讓聶魯達傷痛不已,他久久無法忘懷她深邃的眼睛,烏亮的秀髮,黝黑的皮膚,開朗的笑容,以及她曾經帶給他的充滿陽光的歡樂和活力。聶魯達的密友泰德鮑姆(Volodia
Teitelboim)在他所寫的《聶魯達:一本親密的傳記》中透露第3、4、7、8、11、12、14、17、20首情詩以及〈絕望的歌〉的靈感來源即是聶魯達稱為瑪莉索爾的泰瑞莎(Teresa
Leon)——在1964年出版的《黑島的回憶》裡,聶魯達稱她為泰露莎(Terusa)。泰德鮑姆說他鮮少讀到如此忠誠地懷念舊愛的詩作:「泰露莎,即使在遺忘中也是無法抹滅的。」泰瑞莎在與聶魯達分手之後,始終珍藏著聶魯達寫給她的那些訴說思念、愛戀與苦楚的情書;二十五年之後,她才與一位小她二十歲的打字機修理技師結婚。聶魯達第20首情詩裡的名句或許也正是泰瑞莎的內心寫照:「如今我確已不再愛她。但也許我仍愛著她。/愛是這麼短,遺忘是這麼長。」
另一位聶魯達稱為瑪莉松布拉的女孩本名為阿爾貝蒂娜(Albertina Rosa Azocar),是聶魯達在聖地牙哥讀大學時的同班同學。Marisombra是西班牙文mar y
sombra的組合,意思是「海洋與陰影」。從聶魯達給她取的名字可知她的個性特質和瑪莉索爾是不同的;她內向沉默且帶有幾分憂鬱的氣質。他們一起上法國文學、法文文法和拉丁心理學等課程,下課後聶魯達時常送她回到她與哥哥所寄宿的住處。由於她和聶魯達都來自智利南部的省份,因此在九月和十二月學校放假時,他們通常一起搭火車到聖羅森多,然後再各自返家。但是一年之後,阿爾貝蒂娜聽從父親的安排,轉學到家鄉羅塔(Lota)附近的康塞普西翁(Concepcion)大學就讀法文課程,聶魯達則仍留在聖地牙哥。兩地相隔三百哩路,聶魯達只能拼命寫信,用文字抒發心中的苦悶、孤寂和想念。然而,阿爾貝蒂娜往往隔很久才回一封很簡短的信,而且時間越隔越久,信件越來越短,到最後甚至全無回音。阿爾貝蒂娜的冷淡和冷漠並未澆息聶魯達對她熱烈的愛,在1921到32年間,聶魯達總共寫了一百一十多封信給她。1927年,聶魯達被任命為駐仰光領事,人生地不熟的環境讓他感到空前未有的孤單和寂寞,對阿爾貝蒂娜的思念也因此更為強烈。他多次寫信央求她到仰光與他結婚,卻久久等不到她的回信,失望與憤怒的聶魯達在忍無可忍之下寫信要求對方銷毀他的信件並退還他的照片。後來有人問阿爾貝蒂娜在獻給她的情詩中哪幾首是她的最愛,她輕描淡寫地不作正面答覆:「最廣為流傳的是〈沉默〉那首。他寫過好幾首給我,但我已不記得是哪幾首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然而,在聶魯達所寫的幾本詩集裡,譬如《霞光》,《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和《地上的居住》,阿爾貝蒂娜始終佔據重要的位置。詩人的詩作風格改變了,但不變的是對逝去的愛情難以忘懷,或者是對真心付出卻沒有回報的愛的煎熬久久無法釋懷。透過文字,聶魯達得以釋放長年禁鎖在心靈鐘瓶裡的精靈,在詩歌裡找到救贖的力量。
聶魯達在五十歲的時候說第3、4、6、8、9、10、12、16、19和20首是為瑪莉索爾(泰瑞莎)所作;其餘十首(即第1、2、5、7、11、13、14、15、17、18首)則是寫給瑪莉松布拉(阿爾貝蒂娜)的。時間會模糊或混淆記憶,聶魯達有時候說「灰色的貝雷帽」是瑪莉松布拉的,有時又將它戴在瑪莉索爾的頭上。或許這兩個女孩都曾戴過同樣的帽子,也或許這兩位青春期的戀人早在詩人心中融合為一體。六十五歲時,聶魯達還說第19首情詩其實是獻給馬莉亞.帕若蒂(Maria
Parodi)——他在散發著海洋和忍冬氣味的薩維德拉港所結識的另一名女子。聶魯達曾這樣回答一群渴望知道真相的聽眾:「我曾答應你們為我寫的每一首情詩提出說明,但是多年歲月已流逝。並不是我遺忘了任何人,而是你們能從我給你們的名字當中獲得什麼?你們能從某道霞光中的一些黑色髮絲中得知什麼?你們能從八月雨水裡的大眼睛得到什麼?我要如何向你們訴說你們所不了解的我的內心世界?讓我們坦誠相待,我從未說過一句不誠懇的情話,也無法寫出一句不真實的詩句。」誠如聶魯達所說,情詩為誰而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情詩裡所流露出的動人情意。我們應該感謝這些曾經出現在聶魯達生命中的女人,因為她們不同的個性特質讓聶魯達的愛情體驗如此濃烈,如此多姿,也讓聶魯達在日後頻頻回望這些記憶,並自其中汲取創作養分。
年輕時飽受情傷之苦寫出《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的聶魯達對愛情未曾絕望,因此我們讀到了他近半百之齡後所寫的《船長的詩》(1952)和《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1959)。在這些詩裡,愛情告白的對象不同了,寫作風格不同了,面對愛情和生命的態度不同了,但聶魯達對愛情的浪漫與憧憬依舊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