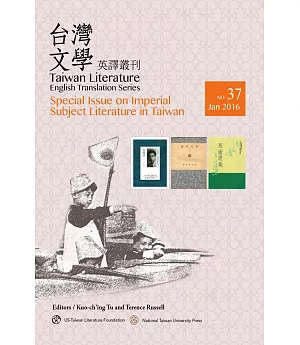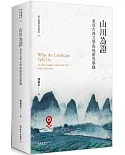「台灣皇民文學專輯」卷頭語
台灣經歷日本殖民統治長達五十年(1895-1945),對台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各方面,以及戰後台灣的整體發展都具有極大的影響。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推行的皇民化運動,也是了解這段台灣歷史不能不正視的現象,而由此產生的「皇民文學」,更是台灣文學史上無可否認的一頁。本叢刊特地以「台灣皇民文學」為主題,選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有助於英語讀者對台灣文學史上這一特殊現象和所產生的文學作品,能有所認識和了解。
「皇民化運動」是日本殖民政府推動日本化運動的一環,也是日本對殖民地族群實行一系列同化政策的一節,包括琉球、台灣、朝鮮、滿洲等地。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並不是一開始就推行皇民化運動,因此不能將殖民統治和「皇民化運動」直接畫上等號。台灣總督府是日治時期最高的統治機關;五十年間共任命十九位總督,根據其出身背景,出任的使命並不一樣。大致言之,總督的任命顯示出三個不同的統治時期:初期武力整治時期(1895-1919)有七位武官總督;中期社會平治時期(1919-1936)有九位文官總督;後期推動戰爭國策時期(1936-1945)有三位武官總督。
日本在台灣的「皇民化運動」開始於1936年9月,當時改派海軍大將小林躋造(1877-1962),接替政黨出身的文官總督中川健藏(1875-1944),以便推動戰爭國策。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9月10日台灣總督府的近衛文磨內閣隨即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形成輿論,「皇民化運動」於是展開。
小林總督上任後提出統治台灣的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政策」,主要內容包括:台灣人「創氏(姓)改名」、推行「國語運動」、實施「志願兵制度」、倡導「寺廟整理」等,在宗教上、教育上、精神文化、日常生活上的改革,同時基於其他兩個原則,提升工業水準,發展軍需工業,將台灣建設為日本執行「南進政策」的基地。
到了1941年4月,「皇民奉公會」成立時,「皇民化運動」進入另一階段,亦即「皇民奉公運動」,意圖使台灣的人力物力全面納入日本軍事體制。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將皇民化運動推向高峰;在政治上積極宣揚「八紘一宇」、主張「天下一家」,在精神上企圖消除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而在生活上促使台灣人脫離傳統的生活習慣和民間信仰。
1942年6月29日發布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鼓勵台灣人參加志願兵,「真誠」、「同心」協力投入戰爭。1943年11月召開「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台灣進入最後決戰時期,不到兩年,1945年8月日本終於投降,戰爭結束。要而言之,皇民化運動在台灣的推動時間,是從1936年9月到1945年8月,前後約九年。
「皇民文學」,在思想和主題上,可以歸結為三類﹕(一)描寫成為皇民、日本國民的心路歷程的作品;(二)描寫志願從軍或歌頌、預祝戰爭勝利的作品;(三)描寫南進、增產、團結、協力戰爭等積極意識的作品。(〈所謂「皇民文學」評述〉,網上課程大綱╱陳建忠)。
在日治時期三〇年代後半,台灣文壇上有兩個重要的文學刊物:以日本人作家為核心的西川滿(1908-1998)主編的《文藝台灣》,創刊於1940年1月,另一個是與之對抗的張文環(1909-1978)主編的《台灣文學》,以台灣人作家為主要成員,於1941年5月創刊。這兩個刊物互相對峙,各領風騷。可是,到了1943年11月,「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在台北市公會堂召開,為了配合戰爭,決定兩者合併,其實是為了將台灣人作家聚集的《台灣文學》解體,將文壇一元化同歸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為配合戰爭的新機關雜誌統一發行(1944年1月)。會議中有西川滿和濱田隼雄(1909-1973)提議將《文藝台灣》奉獻給「台灣文學奉公會」,發表歸屬宣言,而《台灣文學》派的黃得時(1909-1999)和楊逵(1905-1985)表明反對。
當時會場氣氛劍拔弩張,相當緊張,代表《台灣文學》身負眾望的張文環,立即提出「沉痛的辯白」,決然立起聲稱:「在台灣沒有非皇民文學。假若有那個傢伙寫作非皇民文學,都該銃殺處決」,這才平息紛爭。結果這場會議,官方達到預定的目的,而「本島文學決戰態勢」因此確立。(見中島利郎〈從「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到『決戰台灣小說集』〉,「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台灣小說集乾之卷╱坤之卷』」解說。)
這個會議之後次年(1944)6
月,奉公會立即呼籲與會者呼應「台灣文學界總決起」的號召,選出十三名會員,派遣到各生產現場。各以一週的日程,「不只是表面上的見聞而且要真正挺身到現場,接觸人們的氣息,體味其勞苦,一週之間,待在現場內外,起居飲食與共,而將這期間的見聞體驗作為素材,寫成小說。」據此,作家以具體實踐,將會議的主題「文學者的戰爭協力――其理念與實踐方法」具體化。派遣作家的感想和作品,六個月之內陸續在各報章刊物刊登,而於1944年12月和1945年1月出版《決戰台灣小說集》乾·坤二冊,距離會議的召開,只有一年,就獻出如此具體的成果。
因此,《決戰台灣小說集》該是反映皇民文學題材和主題的一個具體的樣板,雖然作品的文學價值,見仁見智。這兩本選集的作者十三人中,台灣人作家七人,日本人作家六人,作者和作品的名單如下:
《決戰台灣小說集》乾之卷(1944 年12 月30 日,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濱田隼雄〈炉番〉
高山凡石〈御安全に〉
龍瑛宗〈若い海〉
西川滿〈石炭·船渠·道場〉
吉村敏〈築城の抄〉
張文環〈雲の中〉
河野慶彥〈鑿井工〉
《決戰台灣小說集》坤之卷(1945年1月16日,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西川滿〈幾山河〉
周金波〈助教〉
長崎浩〈山林詩集〉
楊逵〈增產の蔭に〉
新垣宏一〈船渠〉
楊雲萍〈鐵道詩抄〉
呂赫若〈風頭水尾〉
自1945年戰後到1987年解嚴前後,在國民政府中國本位的統治下,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研究,長期被認為是禁區。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的發掘及其作品的出土工作,是在上世紀七〇年代中期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開始的。1979年7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的出版之後,台灣才真正開始面對日治時期皇民文學的作者,而將他們的作品翻譯成中文,因而引發作品如何取捨和作者如何評價的問題。
《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的主編鍾肇政對「皇民文學」的定義認為:「簡言之就是做一名日本順民的文學,不用說,是失去了民族本位的文學。」(見〈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盲點――對『皇民文學』的一個考察〉,1979年6月1日《聯合報》,中島利郎〈『皇民作家』的形成――周金波〉所引。)他將這一「全集」中收錄的「皇民文學」區分為以下四個類型:
「盲目型」:相信日本人的宣傳,讚賞皇國、皇軍及聖戰,諂媚統治者,民族意識非常稀薄到極近已消滅的作家。
「屈從型」:在文壇上具有聲望、被邀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並派遣到各地發表自己的見聞,小說家屬於這一類型的居多。
「自覺型」:自覺身處險境而不忘民族立場的作家,以楊逵為典型的代表。
「命令不能型」:決然拒不從命者,特別是指吳濁流,在日本警察嚴密監控的戰時環境下,仍秘密寫作《亞細亞的孤兒》。
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中,將周金波、王昶雄和陳火泉三人定位為皇民文學的代表作家。周金波的〈志願兵〉發表於1941年9月20日《文藝台灣》第二卷第六號、陳火泉的〈道〉於1943年7月1日《文藝台灣》第六卷第三號、王昶雄的〈奔流〉於1943年7月31日《台灣文學》第三卷第三號。這三篇代表作,都呼應時潮,寫於1941年4月皇民奉公會成立、皇民化運動進入第二階段之後。有趣的是,這本「全集」第八卷中,在「出版宗旨及編輯體例」中,特別說明「寓褒貶於編選之中,凡是皇民化意味甚濃的御用作品,以不選錄來隱示我們無言的寬容的批判。」因此,只收錄了收錄的王昶雄〈奔流〉中文翻譯,而將而陳火泉的〈道〉及周金波的〈志願兵〉摒除在外,顯然後二者是「皇民化意味甚濃的御用作品」。
首先,我們得了解周金波與他的〈志願兵〉。
周金波1920年出生於台灣基隆,翌年由母親帶到日本與留學的父親團聚,四歲時返回台灣,受小學教育,十三歲時再到日本上中學,進入日本大學齒科,畢業後,1941年4月回台繼承長壽齒科醫院,9月在《文藝台灣》第二卷第六號發表〈志願兵〉。1943年8月,參加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大會發表「皇民文學の樹立」,認為:「眾所周知的,我們台灣可以說是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個縮圖,大和民族、漢民族、高砂族這三個民族,公平地在天皇威光之下,共榮共存,現在就是這樣,三位成一體達成聖戰而協力向前邁進。」
至於周金波的〈志願兵〉,葉石濤在〈台灣作家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認為「這是一篇『皇民文學』,但是在『決戰下』的台灣文學裡,卻是唯一的一篇不折不扣的皇民文學」,進而他在論「四〇年代的台灣日文文學」時,認為周金波的〈志願兵〉是「證實了日本人的奴化政策,在一部分無知的青年中奏效的寫實。周金波曾參加了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周金波的小說顯示了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如何地摧毀了一部分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奴化成功的事實;這也算是血跡斑斑的歷史性記錄吧。」(《走向台灣文學》,1990年3月)
許俊雅在《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書中,針對周金波前期的作品〈志願兵〉和〈水癌〉與後期的作品〈尺的誕生〉和〈鄉愁〉比較之下,認為:「從周氏後期作品觀之,其對皇民化摸索後之困惑,之無法釋然,實已遠超過西川滿一廂情願之樂觀。〈鄉愁〉一作不正說明了皇民之路是走頭無路,一籌莫展嗎?如果僅據周氏先前二篇作品而完全否定其人其作,而將之廁於皇民文學最具代表之作者,豈非對他日後之追求全盤否定?漠視其轉變歷程,對周氏而言是否公平呢?」
事實上,周金波在1920年出生時,日本統治台灣已有25年,因此他沒有抗日的感情存在,對成為日本人沒有什麼抵抗感。〈志願兵〉是以1942年6月29日發布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為主題。作者在日本長大,受日本教育,念日本大學,自認為就是日本人,一如小說人物明貴所表明的:「我們台灣人是不當日本人是不行的。……為什麼不做日本人不行的原因,這是我首先必須考慮的。我在日本的領土出生,我受日本的教育長大,我日本話以外不會說,我假如不使用日本的片假名文字我就無法寫信,所以我除了成為日本人以外沒有別的辦法。」
另一方面,小說人物明貴在心態上具有台灣人精英階級的優越感,認為台灣人在文化層面上很落後。台灣人憧憬日本,希望將台灣的文化提升到日本的水平,而「皇民化」是提升台灣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一種手段。作者和小說人物的民族認同意識雖然較薄弱而受到批判,但是作為一個殖民地作家,認同殖民地政府政策、協助皇民化運動,其實作者是為台灣好,也有評論者認為他是「愛台灣」呢?
日本學者中島認為〈水癌〉是從被同化的觀念中產生出來的理想小說。在未回台之前寫的〈水癌〉,周金波的價值觀,實際上已經內化與日本人的概念如出一轍。他以個人生命經驗中的「日本眼光」觀看真實,而在故事中展現出「現代日本」與「傳統台灣」、「進步」與「落後」的二元對比的文化差異(〈『皇民作家』的形成〉一文。
其次,讓我們看看陳火泉和他的代表作〈道〉。
陳火泉(1908-1999),彰化鹿港人,戰爭時期改姓名為高山凡石。六歲進私塾學習漢文,十歲進鹿港第二公學校。台北州立工業學校畢業後,1930年任職日治時期台灣製腦株式會社,台灣總督府專賣局。1943年7月陳火泉發表處女作〈道〉於《文藝台灣》第六卷第三號,獲芥川賞候補,引起日本人作家濱田隼雄的讚賞﹕「是否曾經有過,將由衷做皇民的熱忱,這麼強烈且這麼清楚地描寫出來的作品?是否曾有過將皇民化的苦惱這麼痛切地傾訴的作品?並且將身為一個人跟皇民化的苦惱戰鬥的過程,這麼強勁有力地表現出來的作品,是否有過呢?這條道路就是通往日本的道路。……這的確是以往的台灣文學所沒有的,可說是現在的台灣獨自的皇民文學。我認為從這作品可預見新的台灣文學。」(濱田隼雄,〈小說「道」〉,《文藝台灣》第6卷第3號,1943年7月。)
這是「皇民文學」第一次的出現,是殖民者的讚賞之詞,認為是開拓台灣人的作家新境界的作品。但戰後在台灣學術界,對「皇民文學」的評論,一般是帶著批判性的。
陳火泉的〈道〉提示本島人邁向成為皇民的道路。故事描寫本島人青楠面對皇民化
的苦惱和掙扎的過程,而所追求的是「日本精神」、「日本人的國民性」。殖民政府以「教育」台灣人「同化」成日本人為目標。「同化教育」讓台灣人體會「日本的精神」,不只要求本島人使用正確的「國語」,還要體會日本人的習慣、表情、舉止,鼓勵和歌和俳句的創作和對日本古典文學的喜好,以提高本島人的「文化水準」和「文明化」。教育與修煉是導向「皇道之路」的手段,企圖將本島人變成具有「大和魂」的「日本民族」。可是,《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執行編輯之一林瑞明提出對〈道〉的責難,認為:「陳君雖有其苦悶、掙扎,甚至也曾拆穿『一視同仁』的假象,
但在全文中所佔的比例,分量不足,而主題的走向,完全「歪斜」了,只有『日本精神』,只有『為天皇而死』,台灣人的苦悶完全看不見了,矛盾也完全解除了。」所謂「分量不足」的評論,可能過于苛求,因為在當時環境下,這篇小說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抗議或批判殖民政府的戰爭國策,而在小說中間接地流露出殖民地台灣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苦悶、和作為次等國民的掙扎和無奈,並不是完全歌功頌德的。
最後,關於王昶雄和他的傑作〈奔流〉。
王昶雄(1916-2000),本名王榮生,台北淡水人。1929年公學校畢業後,到日本進入東京郁文館中學。1931年回台就讀於台北商工高等中學,1935年考上日本大學文學系,隔年因父親去世,為生活計,轉念牙醫科系,一生以牙醫為職業。
王昶雄的成名代表作〈奔流〉,於1943年7月發表於《台灣文學》第三卷第三號。該作品是否為呼應時局的「皇民文學」最受爭議。內容描寫皇民化運動下台灣人面臨適應的困境和內心兩難的掙扎。〈奔流〉這個題目就令人聯想到時代騷動的形象,以及難以抗拒的時潮的奔騰。
故事的主角本島人中學教師朱春生,過著皇民化的生活,改姓伊東,娶日人為妻,崇尚日本精神,認為台灣文化為低俗落後,甚至對親生父母為台灣人感到羞恥,引起他的學生林柏年的反感。林柏年認為崇尚日本,也不必踐踏父母,認為我必須是堂堂的台灣人,才能成為堂堂的日本人。他對伊東春生的思想和行為,極為不滿,甚至屢屢反抗,而與伊東春生形成強烈的對比。處在兩人之間的「我」,與伊東一樣,曾經留日,也憧憬日本內地的一切和對日本文化的認同,但無法放棄對台灣鄉土的愛心,卻也難堅決地否定伊東春生的皇民思想與生活方式。陷入這一兩難的困境,小說最後,「我」還是莫衷一是,在不知如何是好的逃避中結束:「我忍無可忍,連呼著去你的!去你的!拔起腿從崗上往山下疾跑起來。像小孩子般地奔跑。跌了再爬起來跑,滑了再穩住地跑,撞上了風的稜角,就更用力地跑。」
上述這三篇「皇民文學」的代表作中,王昶雄的〈奔流〉,本叢刊第20集(2007年1月)「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II」專輯中已加以譯介。其他兩篇〈志願兵〉和〈道〉在本集譯介之外,我們特地再選與這一主題相關的三篇小說:周金波的〈水癌〉,以及呂赫若的〈風頭水尾〉和〈清秋〉。
「皇民小說」中常見的一個情節是,台灣的知識分子,留學日本之後回到故鄉,發現台灣與東京、故鄉與帝都、本島人與內地人,在文化上和現代文明程度的對比和落差。為了提升台灣文化水平、尤其是在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衛生條件的改善上,小說描述殖民地現代化的情景,藉以展現同化的正面價值,以及小說人物在戰爭時期,積極配合國策、為國奉公、甚至志願從軍犧牲的正當性。
這一描述都呈現在〈水癌〉、〈鄉愁〉、〈清秋〉和〈奔流〉中。呂赫若的〈清秋〉,雖然最後表現出呼應「南進」的國策,支援到南洋從軍,但與周金波的〈志願兵〉相比之下,顯得含蓄多了。呂赫若的〈風頭水尾〉是在「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之後,應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的邀請,作者被派遣到臺中州下謝慶農場一週的體驗而提供的文學作品。一如《決戰台灣小說集》序中所宣稱的,這類作品「為了如實描寫要塞台灣的戰姿,以資啟發島民之同時,培養明朗而有滋潤的情操,振起明日的活力,而一起成為鼓舞激勵產業戰士的糧食。」面對當時殖民政府的政治壓力,呂赫若能夠化險為夷,微妙地創作出這樣的一篇突破政治干擾、超越時空而具有高度文學價值的作品,作家的人格及其技巧和功力值得敬佩。總之,對「皇民作家」的評價,可能因評論者的立場和觀點不同而大不相同。這一專輯的翻譯,都是根據原作,從日文譯成英文,尤其是〈清秋〉和〈道〉,篇幅較長,翻譯者Lili
Selden, Christopher Ahn, Faye Yuan Kleeman, Jon B. Reed, 以及日英翻譯老手佐藤紘彰,共同加入我們的翻譯陣容,盡心盡力,勞苦功高。Dr. Selden在譯稿的最後審訂階段助以一臂之力,Terence Russell和Fred Edwards
兩位英文編輯不辭辛苦,任勞任怨,此外我校台灣研究中心繼續提供編輯作業上的協助,以及台大出版中心的合作和協助,使本集能夠順利出版,在此謹致最大的謝意。
「皇民化運動」自1937年開始推動以來,至今時隔七、八十年,台灣也在上世紀九〇年代之後,逐漸民主化,成為多元的民主社會;時空迥異、學術觀點多元並存、互相尊重。因此,對「皇民文學」的評價,及其作者的功過評斷,應該拋開政治正確、民族立場和道德譴責,以更包容和理解的態度來看待台灣文學史上這一特殊現象。我們希望能從史料中發現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優越作品,而以作品的文學價值作為論斷優劣的主要根據。本集在選譯作品時,我們以作品的代表性和文學性為主要考量,希望能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文本。另一方面,日治時期的「皇民文學」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複雜性,可以為文化研究和後殖民研究者,提供一個值得不同詮釋和深入探討的研究對象,尤其是經歷過東西殖民地經驗的東亞各國,關於殖民文化和現代社會的比較研究。因此,本叢刊這一專輯,除了感謝諸位譯者的辛勞和貢獻之外,我們希望所選譯的「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本身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和一定的代表性,值得向讀者和這一領域的學者和研究者特別推薦。
杜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