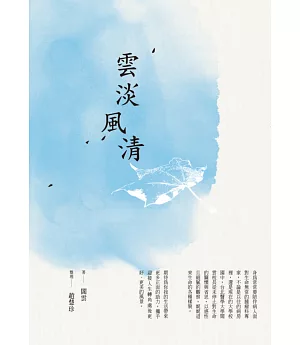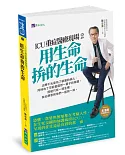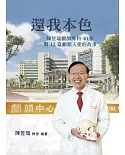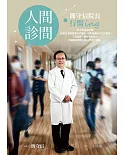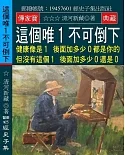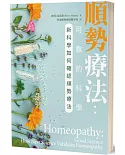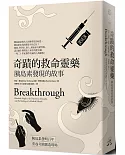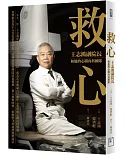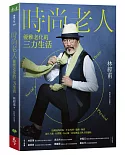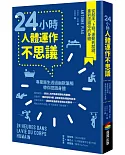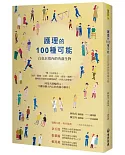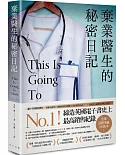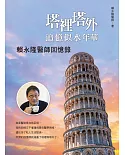推薦序
醫惠髓緣 智饗心聲
日前得知閻雲校長的新書《雲淡風清》即將出版,非常歡喜,謹以感恩之心,樂為之序。
算一算,認識閻雲醫師轉眼已經二十多年了。當時我們都是在美國的臨床執業醫師。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慈濟美國分會在南加州洛杉磯郡成立了海外第一家「慈濟義診中心,籌備期間就由我擔任慈濟醫療諮詢委員會主席(Chairman of the Tzu Chi Medical Advisory Committee)。而閻雲醫師也剛好是在那一年七月到希望城國家癌症中心(City of Hope
National Medical Center)工作,專長是血液腫瘤科,在慈濟人接引之下,如果遇到弱勢居民或病人來到慈濟義診中心求救,發現罹患癌症時,我們就會將病人轉到希望城委請閻醫師治療。
一九九五年,我決定返回台灣投入慈濟醫療志業服務,美國慈濟義診中心就敦請閻雲醫師接任慈濟醫療諮詢委員會的主席。除此之外,更要感恩閻雲醫師的是,在台灣成立的慈濟骨髓資料庫之所以能順利運作,就是閻醫師的助緣。
為了給罹患血液疾病的華裔患者一線希望,在確認不影響捐髓者健康後,證嚴上人首肯成立慈濟骨髓資料庫。約莫在一九九三年底到九四年初,也就是在資料庫籌備時期,閻醫師就承諾擔任義務顧問。運作初期,台灣的慈濟志工辛辛苦苦舉辦驗血活動所募得,每位志願者的10
cc血樣,因為台灣沒有相關檢驗技術的實驗室可以承接,所以必須空運到美國做檢驗。感恩閻醫師因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保羅‧寺崎(Paul Terasaki)教授熟識,熱心居中協調,說明慈濟以私人機構之力籌辦國家級骨髓庫的大愛,讓寺崎教授不僅願意接案,每一筆血樣也只收取一半的檢驗費用,讓募款不易經費拮据的慈濟骨髓庫稍微鬆了一口氣。
我的印象很深,閻醫師曾在《慈濟月刊》發表過一篇文章〈心靈的桃花源〉,寫下他在接觸慈濟與拜訪上人後的心情感受,原本單純想當一個好醫生的心情,由於見證到上人力行佛法在人間的大智慧,與慈濟人點滴付出的大平凡,找到他自己對人生意義的定義。拜讀時,也讓我回想起自己得識上人與慈濟之後,找到心靈依歸的初感動。
閻醫師在美國二十多年,不管是在臨床、教學或研究方面,都有非常傑出的成就,而他長年對於台灣醫學界默默奉獻所長的用心,更讓人感動。二○一一年閻雲醫師應聘,回到母校台北醫學大學接任校長一職,投入醫學教育領域,帶回專業新思維,傳承以人為本的醫療人文,實為台灣醫界之喜。
閻校長投入臨床與教育多年,感知無常,珍惜當下,在忙碌之餘,亦書寫在美國行醫時期與病人互動的真情記事,以及在美國與臺灣投身醫學教育的所知所想。此外亦感恩閻雲校長近二年來接受《人醫心傳--慈濟醫療人文月刊》邀稿,每月撰寫〈醫聲〉專欄,將所思所想與大眾分享,並提點年輕學子。
這些寶貴的內容皆收錄於《雲淡風清》新書中。讀者可藉由此書,領略閻校長對病人的真心、對醫學教育的用心,與從中散發的人文風采,謹此衷心推薦這本值得一讀的好書。感恩。
文/林俊龍 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
序
大醫醫心
唐代名醫孫思邈《千金要方》
內稱「古之善為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已成古今名言。上醫一句原出《國語.晉語八》,晉平公有疾,秦景公令一名姓和的醫生前去探視,這位和醫師出來說道:「不可為也⋯⋯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後來有一個叫文子的哲者(據說是老子門徒)問和醫師:「醫生也可以醫治國家麼?」醫師答道:「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就是說,最好的醫師,所謂上醫,可以醫治國家疾病,再其次醫治人疾病的,就是所謂醫師了。和姓醫師既不能諫導晉平公的迷惑,無法阻止平公生病,他只是一個醫人的醫官,不是高明的上醫,能夠治療國家的疾病。
許多醫生除了醫病以外,更有治國救民的抱負,現代例子比比皆是,菲律賓的黎剎,被稱為菲律賓國父。德國的史懷哲在非洲叢林行醫前,就曾這般起願,「三十歲以前要把生命獻給傳教、教書與音樂,要是能達到研究學問和藝術的願望,那麼三十歲以後就可以進入一個服務的方向,把個人奉獻給全人類。」當他決定將後半生奉獻給非洲人,便開始學醫,三十六歲取得醫師資格,三十八歲前往非洲叢林,在那裡服務非洲五十二年,終其一生。
治國的醫生也很多,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台灣的蔣渭水、賴和,都堪稱上醫。知識分子關心人民疾苦,拯黎民於水火,利用醫理來分析天下之病,如同醫者切脈用藥,望聞問切,最有名就是唐代柳宗元一篇「癒膏盲疾賦」,以醫者討論治療秦景公夢寐膏盲之疾為例,導論除弊利政,治好社稷。
台北醫學大學校歌也有「上醫醫國,博愛濟世」及「學好做人方做醫」之句,引申而言:一所全人教育的醫學大學,不只是基本醫學的培育訓練,還要有上醫醫國的精神;
要有巨大慈悲,以一顆關懷世人的愛心,博愛濟世。北醫大校長閻雲是個腫瘤專家,碰到多是奇難絕症,病人絕處逢生,一方面固是醫術高明,另一方面卻是他能醫病醫心,不單從藥物或科技治療入手,更能照顧及病人心理建構及其家庭社會背景,因此,上醫可以醫國,大醫且能醫心。
禪宗謂有心有世界,醫者有愛心去關心,人溺己溺,息息相關。如醫者無心,事不關己,縱使醫術高明,亦不過名醫一名。聖保羅《哥林多前書》內說到的,信、望、愛三者中最大是愛,愛不只是愛自己,而是愛別人。為什麼要愛別人?因為信望,均可自己修行,惟有去愛人去關懷人,才能把基督降世的使命體驗透澈。本來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極至尊榮,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必聖子下凡,降生為人,以血與肉為世人贖罪?原因便在神愛世人,願意降生與人同類,祂的終極使命,除了訓誨世人,樹立人的典範,還要以愛釋恨,犧牲自己,救贖世人,從此世人可以藉祂的人類名稱———「以耶穌基督之名」去祈求幫助。
手捧此書,內心多所感動,這絕非一般病例治療讀本,作為讀者以心比心,我讀出一個醫師替病人與社會把脈的用心。閻雲曾長期居留美國,並為洛杉磯「希望城」(City of
Hope)醫院首席腫瘤專家及實驗室主任,他毅然放棄高職,回台服務母校,夙夜匪懈,無怨無悔,這是一個大抉擇。他的抱負不止要醫人,還要醫心,這是大乘、大智慧、大慈大悲。書內的「劉先生」及「燒鴨大夫」,分别道出亞裔在美國種族大溶爐理想下的悲哀。劉先生本可姓Lau 或
Liu,就像每一個美國華人的英文拼音名字,但他求好心切,改名路易(Louie,取廣東台山人的雷姓拼音),以為利用一些名字拼音的混淆,可以獲得一些他人對西方名字的聯想認同,從中取得方便,但終其一生,路易這發音只怕更較接近魯蛇(loser)。原來大溶爐是個大騙局,他的一生代表了一個美國夢的幻滅,妻離子女散,最後的一句遺言是,「到頭來,我想,我還是一個中國人⋯⋯」。
在閻雲接觸各類不同病人,或朋友的黑暗面與光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