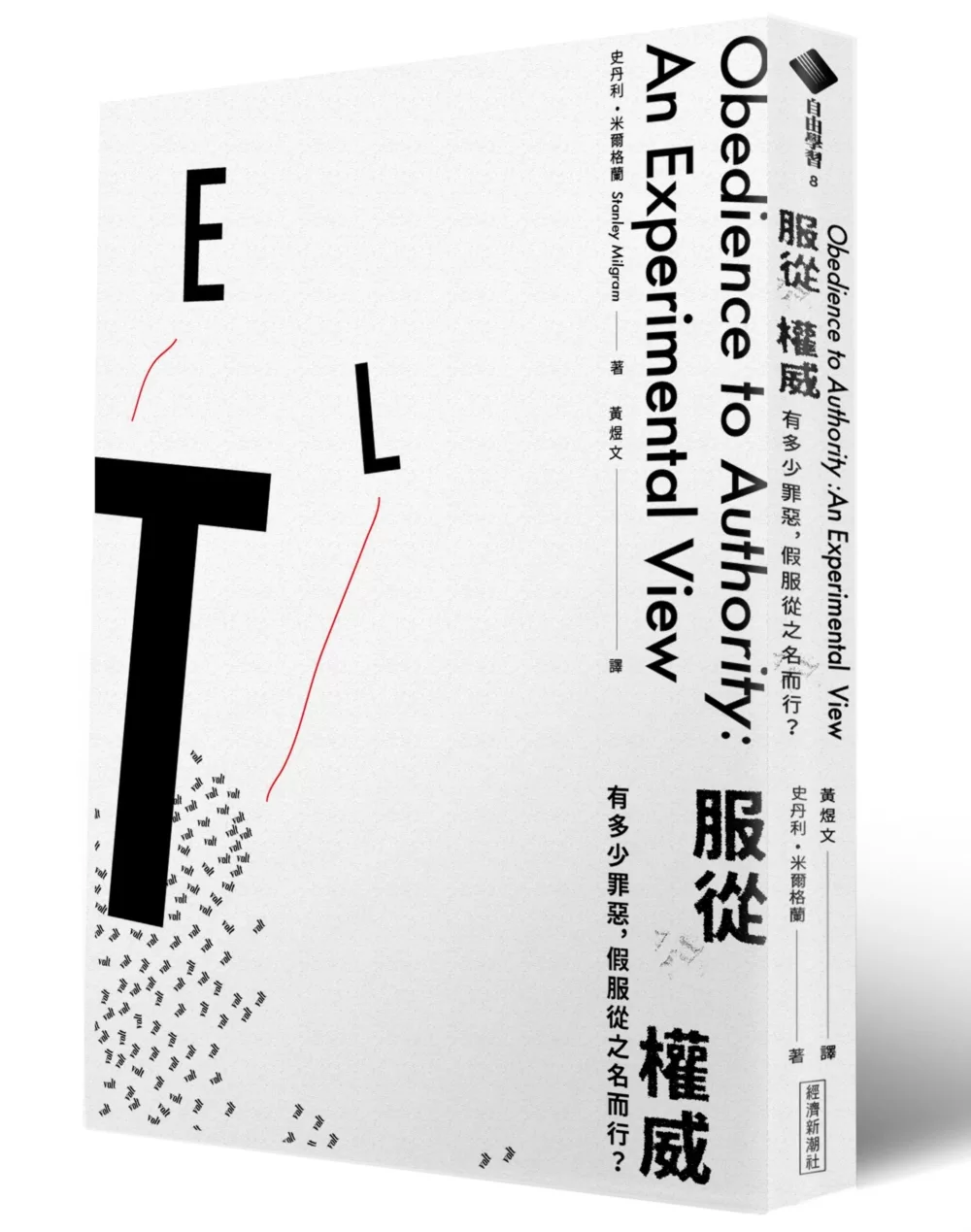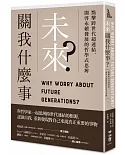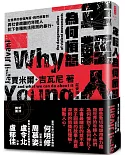推薦序
服從或反抗?
服從是人性嗎?或反抗是必要的嗎?
我們的文化中,受儒家倫理的影響,很強調尊卑的關係,例如孝順不只要求「尊敬」更要求「順從」長者,甚至從很小就要小朋友「聽話」,不然就是「不乖」,可見「服從」尊長甚至被提升到倫理價值的層次,而不論其是否有值得尊敬或崇揚之處,「聽話」本身即被賦予正當性。換言之,小孩子的責任是在「聽」而不在「說」,更彰顯在我們的俗諺:「小孩子有耳無嘴」,其被期待能服從,而不在於有自己的意見。
比較令人訝異的是,西方社會並未受到儒家的影響。在一九六○年代耶魯大學教授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所進行的十九次一連串的實驗,參與人數多達一千人,年紀從二十歲到五十歲,當中沒有人是大學生或高中生,在非使用外部的強制力之下,受試者被告知要進行處罰與學習的效果研究,當被電擊的對象已展現高度的痛苦,很高比例的實驗對象仍然會服從實驗的指示,縱使有所疑慮,仍服從指示持續地按下更高的電力,直到最後的階段。
這項實驗的結果,或許可以呼應哲學家漢娜.鄂倫(Hannah Arendt)所謂「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在一九六一年其在以色列觀察公審二戰的戰犯艾克曼(Adolf
Eichmann),這位前納粹執行屠殺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主要負責人,其並非對猶太人有多大的反感或深仇大恨,而是一位如鄰家大叔般的平常人,執行大屠殺就像公務員在執行一般的公務一樣,如同前面的實驗當被指示進行電擊的工作,即使對其正當性有所質疑,甚至對被電擊者產生同情,而大多數的受試者仍然會服從指示完成電擊的工作。漢娜.鄂倫提醒我們,不是很邪惡的人,才會做出邪惡的事,一般的人若不加思索地服從邪惡的指示,仍會做出邪惡的事,甚至大多數的邪惡,都是這樣造成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提問,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難道不會反抗嗎?這些受試者,若反抗不執行電擊的工作,也不會有任何的威脅或損失,但為何不反抗,而選擇繼續服從指示。或許他們認為既然已經承諾要進行實驗,即有義務要完成實驗,雖然對於這樣的實驗仍有一點質疑。換言之,或許履行承諾的責任感高於停止被電擊者的苦痛,只是這樣的思考,是對的嗎?對於艾克曼來說,執行長官所交辦的任務則高於數百萬猶太人的性命,而這樣的判斷是對的嗎?這樣的說法,或許更反映出他對於自己所執行的任務,是不是「邪惡」或「不正確」,並未產生任何的懷疑,或縱有,但其他的考慮更高於殺掉幾百萬的猶太人。
其實,我們若反觀人類的歷史,類似幾百萬人被屠殺的案例,並非是罕見的,且往往是在成就許多人自認為的「神聖」的事,不管是基於階級、種族、宗教、國家、民族、政治意識形態等等的理由。一直到人權思想的出現,強調人性尊嚴的不可剝奪;認為每一個人的人權都是神聖的,且應該超越前揭各種的理由,才開始對於大規模滅絕人類的行為,視為一種邪惡。人權對於一切的殺戮行為都認為應該被禁止,甚至包括死刑,而前揭種種「神聖」的理由,甚至被認為係各種的歧視或不正確,而喪失其正當性。
人類營社會生活,欲形成公共的秩序,難免會有支配服從的關係,惟不同的是在於其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如在政治上,不管是威權專制或民主政體,其區別不在於是否有支配服從關係,而在於其政治正當性的基礎,如在君權神授的時代,其統治之正當性訴諸於宗教的神聖性,而在民主時代,其更奠基在人權、法治、民主的選舉等之上。甚至,在社會上人際的關係,更可能基於經濟上、知識上、階級上、種族上、性別上等等之不對等或優勢,所造成的支配服從關係,而這些過去傳統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尊卑倫理關係,亦被重新檢視其正當性的基礎,例如過去重男輕女的父權倫理觀,從性別平權的角度而言,即視為是不對的或邪惡的。
因此,在強調人權保障的民主國家,所謂支配服從的關係,很難不被檢視其正當性的基礎,如法國哲學家卡謬(Albert Camus) 所主張:「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反抗即代表著一種新的存在抉擇,而不是默默地服從各種既存的倫理價值。要避免「邪惡的平庸」,端視我們是否能針對各種支配服從關係,進行思辨,若認為「邪惡」即須反抗,才有新的存在可能性。
甚者,前揭米爾格蘭教授後來將其實驗結集成書,在名為《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的書中,其指出服從的本質「在於一個人把自己視為他人期望的工具,因此不再認為自己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換言之,服從除不思辨自己的行為以外,更深沉的意涵在於規避自己的責任與自主性,而選擇追隨強人或威權,這或許是民主政治最大的敵人,即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所謂:「逃避自由」。民主社會肯定人民的獨立自主性,而將政治的正當性建立在人民的參與;若人民選擇不參與或規避責任而將權力集中於強人或獨裁者身上,從德國的威瑪民主共和退化成希特勒的納粹威權政體,即為歷史的實例。
米爾格蘭教授的實驗雖然是在一九六○年代的美國,但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且民主化仍未成熟的台灣,我們如何看待政治權威,服從或反抗仍不斷地考驗著我們所有的人,是選擇或逃避自由?
林佳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系主任
教育部人權教育輔導群召集人
推薦序
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這個「服從權威」的電擊實驗,我們多多少少在不同的文章裡面見到過,但我們知道的大都是比較簡化的版本:受測者會被要求扮演「教師」的角 色,當「學習者」犯錯時要啟動電擊,然後隨著犯錯越多而電擊的強度越大,而根據實驗結果,多數的人會持續服從「權威」要求他繼續電擊,即便這個權威沒有其
他實質上的威脅,而假的學習者則表現出非常痛苦的樣子。
如果你對於米爾格蘭實驗這個故事感到困惑,或是好奇:難道整個實驗在不同情境、性 別、職業下面也完全沒有分別嗎?那你應該要讀一下這本《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這是米爾格蘭完整實驗記錄和說明的一本書,裡面有超過 1000人參與實驗,而且針對不同的實驗情境做出完整說明。
這並不是一本看了會令人愉快的書,但對於想要了解人類服從威權的「心態」,絕對是一本必讀的經典。
楊士範
關鍵評論網共同創辦人
序言
路西法(Lucifer)墜入地獄,亞當與夏娃被逐出伊甸園,這是影響西方文化最深遠的兩段敘事,警惕世人,不服從權威招來的可怕後果。上帝要求所有的天使尊崇亞當,也就是上帝新造的完美生物:人類。但路西法──上帝最寵愛的天使,他是「明亮之星」,在聖經中又稱為「晨星」──卻忤逆上帝的命令。路西法與一群想法與他相同的天使認為,在亞當被創造出來之前,他們早已存在,況且亞當只是凡人,而他們是天使。上帝聽了之後,立刻認定他們犯了兩項彼此關係密切的大罪,一個是驕傲,另一個是不服從祂的權威。上帝毫無化解衝突的打算,祂召來大天使米迦勒(Archangel
Michael),要他將服從的天使組織起來,以武力討伐這些叛逆。當然,米迦勒贏了(有上帝為他撐腰),路西法變成撒但(Satan),又稱為魔鬼(Devil),他被放逐到上帝新創造的地獄裡,其餘的墮落天使也隨他一起墜入其中。然而,撒但從地獄返歸,他證明不尊崇亞當其實是適切的,因為亞當不僅不完美,更糟的是,他輕易受到蛇的影響而敗壞。
當初,上帝讓亞當與夏娃自由地統治完美的樂園伊甸園,只規定了一個小小的禁令。上帝特別耳提面命: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絕不可吃。可撒但卻化為蛇的形體,說服夏娃吃一口善惡樹的果子。夏娃吃了之後,也要亞當跟著吃一口。他們只不過吃了一口禁果,就立即受到責難,並被永遠趕出伊甸園。他們必須辛苦耕種,體驗許多苦難,甚至親眼目睹自己的子女該隱(Cain)與亞伯(Abel)相爭。他們也失去了純真。更糟的是,不服從權威造成的可怕後果,居然讓他們的罪不斷傳承給後代,直到永遠。世上每個天主教的孩子一出生,就帶著亞當與夏娃惡行的原罪詛咒。
顯然,這些敘事是男人與權威創造的神話,絕大多數出自僧侶、拉比與牧師之手,因為這些敘事發生的時間,遠在人類能夠目擊與記錄之前的宇宙歷史中。這些敘事就像所有的寓言一樣,是經過一番設計,目的在傳遞一項強有力的訊息給聆聽與閱讀的人知道:無論如何,你都要服從權威!不服從權威的結果非常可怕,甚至要下地獄。這些神話與寓言一旦被創造出來之後,就由一代代的權威予以傳承散布,例如今日的父母、老師、上司、政治人物與獨裁者,他們希望他們的話受到遵從,不能有不同的意見或挑戰。
因此,在傳統的教育環境裡,身為學童,我們都學過而且體驗過這一連串的校規:除非老師准許你站起來離開座位,否則你必須乖乖坐著;發言前必須先舉手,老師同意後你才能說話;不能跟老師頂嘴,也不許抱怨。這些行為規則深深灌輸到我們的腦海裡,即使我們長大成人之後,它們依然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周遭,就好像我們身上永遠掛著一個牌子,提醒我們要服從權威。然而,不是所有的權威都能做到正義、公平、道德與守法,我們從未受過清楚的訓練,讓我們明辨正義與不義的權威有何關鍵差異。正義的權威值得尊重與服從,甚至於毋須太多質疑,但不義的權威應該會引起大家的疑慮與不滿,最終引發挑戰、反對乃至於革命。
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的一系列服從權威實驗──實驗過程清楚完整地呈現在這本新版作品裡──代表了社會科學對人性核心動力進行的重要調查。米爾格蘭的作品首開先河,把服從權威的本質研究引進到實驗室的控制環境裡。某個意義來說,米爾格蘭遵循的是社會心理學之父庫爾特‧勒文(Kurt
Lewin)的傳統,不過一般不會將米爾格蘭歸為勒文學派,舉例來說,像里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史丹利‧夏克特(Stanley Schachter)、李‧羅斯(Lee Ross)與理查‧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明顯走的就是勒文的路線。不過,米爾格蘭利用實驗室環境的限制與控制,來對現實世界裡的意義現象進行研究,這種做法本質上與勒文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式不謀而合。。
米爾格蘭之所以想探索服從,最早是從思索德國民眾輕易服從納粹權威開始的,德國民眾在納粹的命令下歧視猶太人,最後允許希特勒實行最終解決方案對猶太人進行屠殺。米爾格蘭是年輕猶太人,他猜想,儘管文化與歷史背景不同,但猶太人大屠殺有沒有可能會在他自己的國家再次出現。雖然許多人斬釘截鐵地認為這種事絕對不可能在美國發生,但米爾格蘭卻對大家的信心感到懷疑。儘管我們相信人性本善,卻無法否認下列的事實:一般人,甚至是我們眼中的好人,都有可能遵從命令,犯下世上最可怕的惡行。英國作家斯諾(C.
P. Snow)提醒我們,以服從之名犯下的違反人性的罪名,遠比不服從來得多。米爾格蘭的老師索羅門‧艾許(Solomon Asch)在此之前即已證明團體的力量會左右聰明大學生對視覺現實錯誤概念的判斷。
但這種影響是間接的,會讓團體與個人對相同的刺激產生不同的感受。從眾(儘管團體的想法是錯的)可以解決這種差異問題,參與者從眾可以獲得團體接受而避免團體排擠。米爾格蘭想找出擁有權力的個人對另一個個人下達違反良心與道德的指令時,會產生何種直接而立即的影響。他想知道,當人面對嚴酷的人性考驗時,實際上會做出什麼事,而這個結果跟我們一般認為人在這樣的情境下會做出什麼反應,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
遺憾的是,許多心理學家、學生與一般大眾自以為了解「米爾格蘭電擊」研究的內容,事實上他們只知道一個版本,而且絕大多數只是看了他那部具影響力的電影《服從》(Obedience)或讀過教科書上的簡單介紹。有人質疑他只找男性來接受實驗,一開始確實如此,但之後的實驗他也找了女性參與。也有人質疑他只找了耶魯大學的學生,因為他起初的研究是在耶魯大學進行的。然而事實上,米爾格蘭的服從研究涵蓋了十九次彼此獨立的實驗版本,參與的人數多達一千人,年紀從二十歲到五十歲,當中沒有人是大學生或高中生!有人嚴厲批評他的實驗違反倫理,他創造的情境讓扮演老師角色的人感到痛苦,因為這些受試者以為這些扮演學習者角色的人真的遭到電擊。我想,一般觀眾可能是看到電影中受試者痛苦與猶豫的神情,因此才強烈地認為這項研究有嚴重的倫理問題。閱讀米爾格蘭的研究論文或他的作品,會發現當中並未特別強調參與者的壓力,我們只看到參與者明知道他們造成無辜者的痛苦,卻依然繼續服從權威。我提出這個觀點不是要主張這項研究是否合於倫理,而是要求讀者應該閱讀第一手的研究資料,了解米爾格蘭的觀念、方法與結果,這樣才能充分了解他的做法。這也是本書將米爾格蘭服從研究的文章結集起來的理由。
接下來我要簡略說明我怎麼看待這項研究。首先,這是社會心理學或社會科學領域內最具代表性也最具概括性的研究。米爾格蘭的樣本數相當龐大,涵蓋了系統性的變數,他找來美國兩座小鎮──康乃狄克州的紐海芬(New
Haven)與布里吉波特(Bridgeport)──各色各樣的一般民眾,並且詳細說明了方法論。此外,米爾格蘭也在不同文化與不同時間重覆進行相同的研究,充分顯示研究的有效性。
米爾格蘭的實驗充分證明社會處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他的實驗結果呼應了行為決定論者情境主義的核心觀點。這項研究說明了一點──絕大多數人無法拒絕不正義的權威的命令。在研究一開始,權威看起來符合正義,而且明白提出合理的意圖,然而之後權威下的卻是不合理的命令。心理學研究者以懲罰做為改進學習與記憶的工具,這種做法是明智的,而且合理。然而,一旦學習者堅持退出,抱怨自己心臟不舒服,而且在電擊提高到三百三十伏特之後,已完全停止做出回應,這個時候再繼續加強電擊,已完全失去合理性。如果學習者被電暈過去,或者是發生更糟的狀況,還談什麼協助提高記憶力?實驗到了這個階段,其實不需要費神多想,照理來說每個受試者應該會拒絕繼續進行實驗,並且拒絕服從殘忍而不正義的權威的命令。然而恰恰相反,受試者施加的電擊力道顯然已經太強,但他們似乎陷入了米爾格蘭所說的「代理人心態」(agentic
state),因此完全沒有罷手的意思。
受試的一般民眾淪為毫無判斷能力、一味服從命令的小學生,他們不知道如何從這個極為不快的處境中解脫,除非老師要他們停手。當他們的電擊很可能導致嚴重的醫療問題時,在這個關鍵時刻,是否有任何受試者從椅子上起身,走到隔壁房間看看受害者的情況?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想想下個問題,我曾經當面問史丹利‧米爾格蘭這個問題:「在調到最高的四百五十伏特之後,有多少受試者自發地起身,並且詢問學習者的狀況?」米爾格蘭的回答是:「一個也沒有,零個!」因此,小學時代服從基本規則,也就是老師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的習性,的確延續到了成年時期,除非身為權威的老師同意、允許與命令,否則一般人是不會停止的。
我對情境權力所做的研究(史丹福監獄實驗)與米爾格蘭的研究有幾個彼此互補的地方。我們的研究就像是情境主義兩側的書擋:米爾格蘭顯示了權威直接對個人施加權力,我則顯示了機構間接對權力領域內的所有對象施加權力。我要說明的是系統權力創造並且維持了某些情境,對個別的行為施予支配與控制。此外,我們的研究都戲劇性地顯示外在權力對人類行為的影響,這一點可以輕易地從讀者與觀眾的反應看出。(我也拍了一部電影《寧靜的憤怒》[Quiet
Rage],對於世界各地的觀眾產生了不少衝擊。)我們的研究都引發了倫理問題,因為我們的實驗都發生了參與者感到痛苦或罪惡感的狀況。我在我最近的作品《路西法效應》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討論這類研究的倫理問題。一九七一年,當我首次在美國心理學會年會上簡單報告史丹福監獄實驗時,米爾格蘭很開心地跟我打招呼,他說,我可以做點更違反倫理的研究來分攤眾人對他的指責!
最後,我可以說點別的事來滿足本書讀者的興趣,那就是史丹利‧米爾格蘭跟我是布朗克斯區詹姆斯‧門羅高中的同學(一九五○年畢業班),我們高中時代就處得很好。他是同年級最聰明的孩子,畢業時拿下了所有的學業獎項,我則是最受歡迎的孩子,曾被高年級選為「吉米‧門羅」。十年後,當我們在耶魯大學相遇時,小史丹利告訴我,他在高中時希望自己是最受歡迎的孩子,我則對他說我希望自己是最聰明的孩子。我們只能運用自己手中的一切,盡力做到最好。往後數十年,我與史丹利有過許多有趣的討論,我們差點一起聯名發表一份社會心理學論文。令人惋惜的是,一九八四年,米爾格蘭因心臟病突發而以五十一歲的英年離開人世。他留下充滿創意與生命力的思想遺產,從最初的服從權威實驗,到後頭延伸出許多新的領域──都市心理學、小世界效應、六度分隔理論與希拉諾效應(Cyrano
Effect)等等──他總是別具創意地混用各種方法。史丹利‧米爾格蘭是人文景致的敏銳觀察者,他總是注意著新的典範,希望能揭露古老真理,或是用全新的眼光來看待隱藏的運作原則。我經常想,如果史丹利還在人世,他會怎麼研究眼前這些全新的現象。
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
二○○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