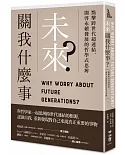導讀
搖滾的力量:一場搖滾音樂會與柏林圍牆的倒塌
這可能是搖滾史上最撼人的演唱會之一,因為這場搖滾演唱會展現了搖滾樂如何在關鍵的歷史時刻,賦予了準備追求改變的聽者深刻的力量與信念,從而改變了世界─讓柏林圍牆倒塌。
1988年7月,就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十六個月之前,美國搖滾巨星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來到東柏林舉辦演唱會。
這是東德有史以來最大的演唱會,至少有三十萬人參加,地點是柏林圍牆以東三英里的巨大露天體育場。因為想要進場的人太多,主辦單位只得打開柵欄,讓每個人都得以興高采烈地衝進去─這彷彿預示了十六個月之後,當柏林圍牆崩塌,人們帶著不敢相信的笑容奔向自由。
從第一張專輯開始,史普林斯汀的創作主軸就是探索美國作為一個許諾之地(promised
land)的幻滅,以及美國夢的虛妄和現實的殘酷之間的巨大對比。他在七○年代的作品描繪了小鎮青年的夢想與失落以及找不到出口的憤慨與焦慮,進入八○年代,他更關注美國經濟轉型下的社會正義,歌唱工人階級日常生活中的夢想、苦悶與挫折,並且不斷質問,所謂的美國夢為何在現實中只是虛幻的泡影?尤其八○年代是雷根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社會越來越不平等,經濟貪婪和軍國主義成為新的時代精神,因此史普林斯汀成為雷根時代最重要的異議者。
1984年的專輯《生在美國》不只讓他成為最重要的巨星,甚至成為美國流行文化的一個重要象徵。
他對音樂的信念是「我對於如何利用自己的音樂,有很多宏大的想法,想要給人們一些思考的標的─關於這個世界,以及孰是孰非。」
1988年在歐洲演出時,史普林斯汀臨時起意想去東柏林演出。
彼時的東德仍然是極權的共產主義政權,政府嚴密控制人們的表達和思想自由。長期以來,對這些共產國家而言,搖滾樂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產物,只會腐蝕年輕一代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因此是國家的敵人。
這些來自共產政權對搖滾樂的指控只對了一半;錯的是,搖滾樂並不是和西方政權站在一起,反而更經常是批判掌權者;但這些政權的擔憂確實也對,因為搖滾樂歌唱的就是自由與反抗,而社會主義青年們當然也難以抵擋住搖滾樂對他們青春欲望的挑動。
1985年,蘇聯新領袖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推動「重建」與「開放」的政治經濟改革,這不僅改變了蘇聯,也影響了東歐各地的政局。此時,共產主義多半已經淪為一副空殼,一個牆上空洞的標語。但不像波蘭和匈牙利已經開始轉型,東德和羅馬尼亞等國卻依然堅守著共產主義陣營的最後防線,只是看到其他國家已經出現變化的苦悶青年越來越不能忍受體制的僵化和腐臭,渴望那巨大的改變之風。
當史普林斯汀試圖探詢1988年是否可能在東柏林舉辦演唱會時,東德共產黨的青年組織「自由德國青年團」也正好也看到政權在年輕人心中已經搖搖欲墜,想要安撫年輕人,因此雙方一拍即合。這不僅是因為史普林斯汀是當時最重要的搖滾巨星,而且他是站在勞動階級這邊,並對美國的雷根政府諸多批評─史普林斯汀常翻唱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的經典歌曲〈這是我的土地〉2,而蓋瑟瑞和美國共產黨走得很近。
在這個東柏林的夏日午後,史普林斯汀的開場曲是〈惡地〉(Badlands):
談論著夢想,試著實現它
你在夜裡驚醒,感到如此真實的恐懼
你耗費生命,等待一個不會來臨的時刻
別浪費時間再等下去了
你每日在此生活的惡地
讓破碎的心站起來
那是你必須付出的代價
我們只能努力往前推進,直到被了解為止
這些惡地才會開始對我們好一點
擁有理念,深植於心的人們啊
活著並不是一件罪惡之事
我想要找一張不會看透我的臉孔
我想要找一個地方,我想對著這些惡地的臉吐一口口水
原本他歌唱的〈惡地〉是夢想破碎的美國,但這當然也是極掐死人們夢想的東德。
史普林斯汀的歌曲主題不論是許諾之地的虛妄,或是年輕人想要離開困頓的小鎮,每一首歌都可以輕易地被東柏林年輕人轉化為他們的現實。尤其,史普林斯汀原本就是最能將搖滾的真誠轉化成演出現場巨大光熱的歌手,在演唱會中,史普林斯汀也準備講一段話告訴人們,他並非出於任何政治性的理由才來到這裡,而是來這裡為人們演唱搖滾樂,並且說:「希望有朝一日, 所有的障礙都能被拆除。」
全場激昂鼓掌。接著下首歌前奏響起:〈自由之鐘〉(Chimes of Freedom)─這是巴布.迪倫(Bob Dylan)關於自由的名曲,而一個月前史普林斯汀在瑞典演唱會上,就在演出這首歌前宣布他將參加國際特赦組織巡迴演唱會。
觀眾聽到了他的訊息。
這本書引述開車橫跨半個德國來聽這場演唱會的三十四歲農夫約格.貝內克說:「每個人都很清楚他說的是什麼─拆除圍牆,那是壓倒東德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從來沒有在東德內部聽任何人這麼說過,那是我們某些人終身企盼聽到的一刻。也有一些來自西方的其他搖滾歌手來這裡演出,然後對我們說:『哈囉,東柏林。』或是這一類的話。但是從來沒有人來到我們面前說,他希望能拆除一切的障礙。
假如我們可以翻越柏林圍牆的話,一定有許多人會這麼做的。」
在1988年的那個夏天,沒有人會想到柏林圍牆會在一年多後崩塌。
1989年9月開始,成千上萬的東德人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大規模群眾遊行在萊比錫、德勒斯登、馬德堡、羅斯托克和波茨坦等地出現,吶喊著:「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
1989年10月東德總理何內克辭職。一個月後的11月9日,人們終於自由地衝過圍牆,柏林圍牆倒塌了。
東德在1990年3月舉行自由民主的選舉,並在1990年10月3日與西德統一。
史普林斯汀的演唱會當然不可能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但它無疑是通往1989年秋天革命的一記鐘聲,自由的鐘聲。
因為這些青年早不願活在圍牆的陰影下,深信東德不能如此繼續,而必須要有改變;看到其他東歐國家,他們也相信改變是可能的。然後,史普林斯汀來了,要他們帶著勇氣逃出這個桎梏的惡地,和被詛咒的命運。
擔任史普林斯汀翻譯的東德女士說,這是一場孕育了改革運動的神奇演唱會,「東德的氣氛在那場演唱會後就改變了。人們興高采烈地離開演唱會回家。有好幾個星期,人們都在談這場演唱會。有這位從西方,從美國來的巨星來到這裡,關切著我們的命運,他說,有一天這裡不會再有任何障礙。成為這樣的群眾的一份子之後,你會覺得自己更堅強了,我們開始不再恐懼。東德當局把史普林斯汀和其他這些西方樂團帶來,想釋放壓力。但這一切都適得其反。不但沒有釋放壓力,還讓年輕人更深入思考自由的意義。」
搖滾樂迷都知道,一場美好的音樂會是魔法般的體驗,是一個集體賦權(empowerment)的過程。你會在音樂的熱力中得到感動、得到力量,並且相信你真的可以和旁邊的人一起改變什麼。
史普林斯汀的演唱會本身是改變中的空氣中的一個因子,它凝聚了那些渴望的聲音,並點燃了更多火花;它讓東德青年更堅信他們每天思考的問題:如何尋找自己的聲音,打破體制的虛妄,並追求真正的自由與反叛─而這正是搖滾樂的精神,及其可以改變世界的力量。
張鐵志
(本文作者著有《時代的噪音:從迪倫到U2的抗議之聲》,
並即將出版《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十週年紀念增訂版)
前言
2002年,柏林,一場絕讚的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演唱會結束後,我搭上計程車回家;突然之間,司機聊到另一場史普林斯汀的演出,那是1988年發生在共產東德的事情。他說,88年7月那一回,是有史以來、空前絕後最神奇的一場演出。史普林斯汀撼動了東柏林,也撼動了這整個共產國家。那場鐵幕後的演唱會,距離我和他偶遇的那個寒冷10月夜晚相隔十四年之久,但那位滿面于思、長髮蓬亂、體格魁武的計程車司機,卻欲罷不能,愈說愈興奮。
「是啊,我知道。」我說著,想閉上眼睛放鬆一下。我才剛提交給路透社一篇新聞報導,是關於史普林斯汀嚴厲譴責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打壓反對入侵伊拉克的國家,像是德國。「我也看過很多史普林斯汀的演唱會,通通都很棒。」
「不,不,不!」司機答道:「不,你不懂。」那場東德演唱會真的與眾不同,沒有任何事情能相提並論。現場觀眾超過三十萬人,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收看電視轉播,整個國家都被撼動了。「那是東德發生過最神奇的事。」他愈說愈興奮,口中的大蒜味往我這邊飄過來。
對數以百萬計的嬰兒潮世代來說,史普林斯汀的音樂彷彿就是我們生命的背景音樂。四十年的歌曲與歌詞,都寄宿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例如〈生而奔跑〉(Born to
Run)中的「那是個死亡陷阱,那是個自殺陰影,要趁年輕掙脫出來,因為像我們這種流浪漢,寶貝,生來就是要奔跑的」。還有〈惡地〉(Badlands)的「慶幸自己活著並非一種罪惡」。那位柏林計程車司機一發不可收拾的熱忱充滿了感染力,他讓我開始設想:史普林斯汀在共產東柏林的那場音樂會,究竟有什麼特別不同之處?
我愈加深入研究,就益發想要了解更多。舉例來說,我還想知道史普林斯汀究竟是哪來的勇氣,居然在東柏林發表反對圍牆的簡短演說,這些都非常有趣;還有,那些肆無忌憚、有史以來數量最龐大的東德演唱會聽眾,估計約超過三十萬人,以及其他數以千計沒有買票的民眾,他們衝破了大門,湧進會場。這一切都令人好奇。
接著,我恍然大悟了。這場演唱會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為舉辦的日期:1988年7月19日,距離柏林圍牆倒塌只剩不到十六個月。史普林斯汀那場演唱會,以及東德隨之而來的騷亂,以及柏林圍牆預料之外的倒塌,這之間究竟有無任何關連?1988年7月19日的史普林斯汀,和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崩落、鐵幕開啟,這兩者之間是否有直接關係?
從此以後,我便一直想著這些問題。對我來說,史普林斯汀與導致柏林圍牆崩塌的東德情緒轉移,這兩者之間一定有某種連結。我對這個想法感到興奮,於是試著想要找出史普林斯汀1988年前往鐵幕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氣氛又是如何。但對我來說,要找到四分之一個世紀前聽過那場音樂會的人,卻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不過,後來這件事卻比我想像得要簡單得多,因為住在東德的每個人,在1988年時若剛好是個青少年,那他或她,要不就在音樂會現場,要不就在收音機或電視上收聽或收看轉播。在東德,時間彷彿停留在那一天─似乎每個人都記得這場演唱會。
我的運氣不錯,史普林斯汀在2012年5月回到柏林,展開他的「分崩離析巡迴演唱」(Wrecking
Ball),許多參加過1988年演唱會的人也到場了,這些人就像舞台上的史普林斯汀一樣,都非常樂意談談這些回憶。我與許許多多的現場參與者交談,包括一些德國與美國的學者,詢問他們史普林斯汀那場長達四小時的表演,以及大無畏呼籲推倒圍牆一事,是否和接下來數週、數月間席捲東德的革命風潮有所關連。如果你相信史普林斯汀那史詩般的演唱會,對推倒柏林圍牆的運動具有貢獻,那取決於你對搖滾樂的力量的信仰。駐德美國大使、同時身兼史普林斯汀死忠樂迷的菲利普.墨菲(Philip
Murphy),就十分確信這份革命力量。雖說1988年時他人不在東柏林,卻相信他那位紐澤西同鄉對東德人民的確有著一種相當可觀的力量:「我理解並喜愛史普林斯汀的音樂,所以能想像現場演唱會對那些東德聽眾、那些處於政權壓迫下亟欲改變的人們,會有什麼樣的影響。」現場成千上萬聽眾之一的約格.貝內克(Jörg
Beneke)表示,史普林斯汀的演唱會對共產東德來說,就像「棺材上的一根釘子」,是倒台的序幕。
毫無疑問地,1988年史普林斯汀的東德演唱會,對那些急欲、並且準備好要改變的人們,正是搖滾樂一份光榮無比的例證。這個特別的故事,是關於東柏林那場千載難逢的演唱會,以及推倒柏林圍牆的反抗行動中,史普林斯汀在無意中所扮演的角色。
艾瑞克.克許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