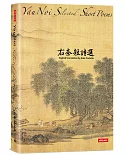推薦序一
雨中更清晰的記憶—《落雨彼日》序
在南洋的午後閱讀,日光中時有風雨,空氣中不時飄來帶有鹽味的潮氣和不知從哪來的汗味。我咿咿呀呀地學怎麼點每日必備的黑咖啡:kopi-O-kosong,摻雜了英文、福建話和馬來話的新加坡式表達,不是Singlish,也沒有人說這是新加坡語。這只是一種自然而然形成的表達系統,要稱為「語言」嘛?似乎還缺少了什麼。此時臉書裡傳來來自東京的訊息:美親的詩集終於要出版了。
六年前,美親把詩集題為《青春ê遺書》,她說:「彼工真緊tō會來。」我在當時寫下的序裡調侃了她,說這紙遺書寫得太早了。擱了六年,美親把這些詩再度集結,放進幾首新作,然後題為《落雨彼日》。瀏覽過新的詩稿,熟悉的語言立刻躍然耳際。沒錯,美親的詩集不光要用讀的,而且一定要念出來。念出來,才有那些「氣口」,才能真正傳達作者的本意。
詩集並沒有太多的新作,也許當初我寫序的時候的判斷是對的,《青春ê遺書》早已完整銘刻了美親青春前期的人生註腳。她對於童年的記憶、家園的描繪、母語的親炙,在多年前早已經固著。但更重要的是「干單欲愛一線風吹/送我遠遠,遠遠飛」的美親,結束了她的愛情「練習」,在「起落ê心湧, 無閣遷徏」的夫婿身邊,潛心做起了語言社會學的研究。
從新竹的清華到東京的一橋,美親已經蛻變為獨當一面的研究者。記得她親手贈予以台語漢字羅馬字混寫而成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日治時期以台語寫作的小說。為了這本碩論,美親進出醫院數次。不出意料,成果質量之豐富精闢,根本就可媲美一部博論。後來美親移居日本,開始學習日文,並成為一橋大學的博士班學生,開拓了台灣的文學和歷史學界未曾熟悉的左翼文學和世界語運動研究。為了這個研究,她甚至學起了世界語(Esperanto)。
這幾年來,我離開文學更遠了。很少讀詩、評論詩,更遑論寫詩。去年冬天我去東京開會借宿美親和威志的宿舍地板。小倆口「攢」了火鍋好料款待。那晚聊了各自的研究和書寫計畫,我聽見美親對更多人事時地物的好奇。只是我看她這幾年,身體更虛弱了。而讓人驚嘆的是,在這幾年之中,雖然得和慢性病搏鬥,但「淡薄仔痠疼,無要緊。」她在研究上的行動力十足,文學之路也不斷開展,嘗試各種文類,而且不斷得獎。
之前,我總是計較詩人寫詩背後的動機,和做為文學行動者的社會責任。詩集裡對台灣歷史的辯證,對普世信條的追求和當代觀點的倡議,比如歷史記憶、土地正義、戰爭、性別平權等等,已無消贅述。但重新讀了《落雨彼日》之後,卻逐漸開始信服一部作品能夠經久不壞,精湛的技藝和美感的追求仍是不可或缺的。
美親對於詩的美感要求,在我看來,一部分源於研究語言過程中的體悟。雖然我和美親的學術路線看似不同,她潛心於語言社會學,我做的是醫學史,但她研究的「世界語」和我所關注的「疾病分類系統」卻有著某種程度的相像。一言以蔽之,都是某個歷史脈絡之中,為了某種溝通或政治目的所形成的共識語言。然而語言在跨文化對譯、挪用的過程中,往往遺漏的是只有從某個地方情境裡才能夠精準命名、理解、賦予意義的。
而這種精準,只有透過我們最熟悉的語言才能獲致。這幾年來,美親對於詩句「音性」的追求和堅持,讓我忍不住用她的詩寫了好幾首歌。幾首發表在《河─賴和音樂專輯》,其他各自發表在不同的場合。我把〈落雨彼日〉這首用二二八口述歷史材料寫成的詩入樂兩次,我大膽地想要用電吉他和鼓組給這首詩加上一點現代感,但美親喜歡的還是原來用鋼琴和絃樂詮釋的小品。做為詩的讀者,美親堅持用母語紀錄的記憶或是寫實的地景,仍然有被淘洗為不同觀點和歷史感的空間。
《落雨彼日》的終於面世,是詩人不斷經過人生試煉,而詩作經過漫長消化、反芻的結晶。我不知道美親將來會在哪裡落腳。研究世界語運動的她筆下除了台灣,還會開展到何地?人在東洋的她,所繼續創作的語言將會如何隨生活流轉?當我跟美親提起南洋混語的耐人尋味,可以想像臉書訊息的另一端,她如何睜大雙眼,隨時準備習得另一種語言來消解她的好奇心。
雨仍然不斷「鬱落」。我喜歡在這種語境裡才能感受到的雨滴速度,雨絲的密度,還有雨水和人皮膚接觸時的清涼感。可以持續期待的是,在成為世界人而仍堅持母語創作的美親,筆下人物的目睭仁會如何更分明,溪水會如何更澄澈,石堆會如何更沉澱,島嶼的位置會如何更準確,記憶的輪廓會如何更加清晰。
吳易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醫學人文助理教授)
推薦序二
未亡,為著見證—《落雨彼日》序
我記得那時我們約在嘉義的一間小茶館,美親要我為她的詩集寫一篇序,那是2007 年的夏天,我一直記得那個畫面,美親將她的詩稿交給我,份量頗厚,揣在手裡沉甸甸的,我笑著說,這就是妳青春的重量。怎知好事多磨,六年過去了,詩集才得以出版,而現在的我們早已不再青春,但我羨慕美親,她還有這些詩作,見證著那些歲月的故事,無論是紀念還是悼念,她始終是個有記憶的人。
美親的文化意識啟蒙甚早,在那個青春色澤仍舊鮮豔的年歲,同齡友人們仍在豪奢的恣意揮霍青春的生命時刻中,美親目光所注視的,心中所思索的,就已是關於這塊土地的文化議題。她是我見過最有實踐力的人,只要她認為有助於喚醒台灣文化意識的任何行動,儘管資源再少,再辛苦,她一定會克服萬難,想方設法的成功達陣。她有一縷早熟的靈魂,形塑了她獨特的氣質,她的雙眼發散著詩人獨有的憂鬱與堅毅,那是我所羨慕且不能及的生命品質。
這一點,讀者們可以從《落雨彼日》這本詩集中清楚的體認到。這本詩集,收錄了美親這十幾年來的台語詩作,記錄了她在這段青春歲月中所體會的、感受的、關懷的以及思考的諸多議題。細心的讀者們必定可以從這本詩集中看到美親詩作中所展現的深度與廣度,從個人的成長記事到家族的記事,從鄉土的關懷到家國的思考,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美親試圖透過這些粗細、深淺不一的歷史線索,尋得自我生命與台灣這塊土地之間最佳的溝通與互動位置。
台語,是美親的母語,她最摯愛的語言,不需轉譯即可表現土地的胎音,透過一個一個音節,將那砰然且躍動的土地情感,毫不扭曲的、直接的傾吐而出。這個語言承載著太多的意義與情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在漫長的歷史中,它咀嚼著台灣人的思考,凝視著種種悲歡與離合,有些故事只有它才能說出真情,它的聲音就是我們的記憶,無論悲傷還是美好,唯有這樣的音調才可以被精準表達。
不久前,我北上參加一個文化年會,會議邀集了許多文化精英以短講的形式傳遞自己的理念與經驗,其中的一個主題,邀請了幾位在傳統工藝領域中堪稱巨匠級的老師傅進行短講,但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這些老師傅們一生懸命的專注精神,反倒是這些老師傅們受限於主辦單位希望他們以「國語」講演,而讓他們精彩的生命顯得冰冷,更甚者顯得「笨拙」。
老師傅們在那十分鐘的演講中「失語了」,讓他們所欲表達的一切,佚失了大部分的意義,在那擠滿千人的會場中,我坐立不安,好幾次我都有一股衝動想起身對台上的講者說:「阿嬤,講台語,我們都聽得懂喔!」在那剎那間,我想起了美親的詩,以及她想告訴我們的關於母語的那些事。
我記得六年前的那個下午,美親怕這些由漢羅符號組成的詩作會阻礙了我的閱讀,主動提出要為我朗讀這些詩作,我拒絕了,因為不是每位讀者都能有此榮幸由詩人朗讀詩作給你聽,我心中的想法是,若我在閱讀上有困難,那麼相信大部分的讀者面對這本詩集都將會有相同的困境,我對美親說,我希望自己讀,如果真的有困難,最少我能夠知道那個「困難」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美親多慮了,閱讀這本詩集一點都不難,我想,或許美親的顧慮並不是「會不會讀」,而更多的是「願不願意讀」。母語文學的創作,這幾年來在文學界開始受到了一些關注,儘管不多,但也不容忽視,而在這些關注中,有著不少質疑的聲音,從文字表現的方式到文學性、美學性甚而文學史的定位與價值,不論這些母語文學的關懷者如何聲嘶力竭的呼籲與論述,就是平撫不了那些彷彿心律不整的懷疑論調。
讀著美親的詩集,我回想著是否過去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員,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而當時的我甚至不曾好好的讀過一篇母語文學的文本,我回想當時那種排拒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是一種偏見?一種因循怠惰?還是一種無由來的驕傲?總之,不論原因為何,這都證明了我沒有盡到一個讀者的責任。
對我來說,文學是一個集合名詞,它同時也是一種集體生產,作家有作家該負的責任,讀者自然也有讀者該有的責任,或許從一個理想的層面來說,身為一個讀者也許對每一部自己所選擇的文學作品,都有著某種隱性的道德義務,那是身為一位讀者最基本的實踐:不帶偏見的去認識與閱讀,對於自己所熟悉的該如此,對於自己所不熟悉的更要如此,是差異的並存而非排除讓文學世界顯得豐富,或許我可以更直接的說,身為一位讀者,我們必須要有跨越邊界的勇氣,嘗試去選擇與認識那些可能被我們習以為常的閱讀品味所忽略的那些其他。
美親的這本詩集,或許可以讓那些憂心母語文學創作前景的人們稍稍的寬心,這本詩集或許沒有前衛的文學技法(或許以母語創作本身就很前衛),沒有華麗的語言風格,但是我從中閱讀到的是一種質樸而道地的情緒感受,透過美親優美的母語吟唱,她領著我去召喚去追尋那些已經逝去或正逐漸逝去的認同與感動,一種彷彿回歸到最初、最初的那種純真。
申惠豐(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自序
紀念彼寡落雨ê日子
以關東人的距離而言,一小時的車程不算遠。但2013年9月8號那天,傾盆大雨竟從天而降,我從國立站搭中央線電車,轉乘兩次地鐵又撐傘走了一小段路,終才進到東京港區那間live house,彼時,全身早已濕透。不久,眼角微微上揚卻非鳳眼那種的阿美族勇士Suming 出場了,他深遂眼眸散發出羞澀純真卻如火的熱情,簡單向台下觀眾打招呼後,就開始專注地用他的母語唱歌。
窗外的雨,還是不停地直直落。但屋內的歌聲如自山裡來,嘹亮且似有迴響。然後,Suming 向日本歌迷們告白,說他在許多地方唱歌,最大的夢想是回家鄉都蘭開演唱會⋯⋯。身旁的Uichi 轉頭過來邊罵我三八邊幫我擦眼淚。其實,也是因前一晚網路MV裡的Suming
那些話還迴盪在耳邊:「⋯⋯出一張母語專輯沒有什麼了不起,但若可以藉著音樂穿透語言的隔闔來告訴你,我是用多少勇氣來決定這件事的。我出生在阿美族,我的歌像浪一樣,聽不懂浪沒關係,海浪每一次打上岸都會有感覺的。我是一個部落的武士,我用創作,當作我唯一的武器,捍衛家鄉原有的面貌,讓每個人都認識這塊土地的美好。⋯⋯」
「我是用多少勇氣來決定這件事的!」我的心如此糾結。用母語創作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別說十年前的氛圍不比今日,連今日都需要許多勇氣。這件事的確沒什麼了不起,但需要多少勇氣才能做下決定,或許只有真正去實踐且貫徹過的人,才能了解吧。而如果,我也能捍衛家鄉原有的面貌,那麼,我想至少我也拿得出來那件,我曾費盡千辛萬苦才挽回的,「唯一的武器」。
提起勇氣的初衷,永遠都忘不了。不過說真的,離開島國赴日求學之後,學術環境的頭腦冷卻機制,早讓我把那些到底是費盡多少「千辛萬苦」的心情,那無數個曾淚如雨下的夜晚,都漸漸淡忘了。回頭探看,其實這本詩集原名《青春ê遺書》,以收錄其中一首詩名為題,當作我關懷面向與階段終結的呈現。只是,在我還28 歲的2007
年秋天,詩集初編完成後,因某些我自己至今也無解的緣故而未能順利出版。我的面皮至薄,無所可謂,後來也因準備赴日而擱置此事;來日後,學習上的忙碌,更讓我幾乎要與詩告別。記得當年,依主題整理了八卷,除了「卷八」那未發表的20幾首,其他50 首都是發表過或譜成歌「唱」過的。現在,雖僅加上來日這五年多寫的5、6 首,但我仍決定把那未發表的卷八刪除,成為如讀者們今天所見的七卷樣貌。
即便如此,我想,那個生長在同時代的年輕人們已幾乎不太講台語、自己也曾厭惡自己母語的人;那個曾也快要忘記母語、後來重新學習母語、努力學習以母語書寫的(還算)「年輕」的女生,她面臨的困境、改變與突破,她這十多年來「某種狀態」的生命軌跡,應該還是能以斷斷續續的節奏,展現在讀者面前吧。是說,偷偷講一下(笑),其實大學以來,我寫的華語詩遠超過台語詩的量,首次得到詩獎還是從台中坐車到台北領的,銀筆獎,〈流民的遺書〉。但我也曾一度認為,詩似乎已不足以承載一個不斷思索殖民地人民該如何前進的生命,其厚度與沉重,特別是用一個「畸型」的語言所寫的詩。然後,況且,我早有放棄用華語寫詩的打算。2001
年發表第一首台語詩〈阿媽ê新衫〉後,也許,是真的有點愛上用台語寫詩的感覺吧。雖然很後來的2013年,根本是為了獎金才寫就〈蠹魚〉,但我想告訴你,我對母語問題的追索從未間斷,即便我學了日語、世界語甚至更多語言,最終都是想要找尋一個可以不被想像被演繹、且能夠最靠近那個真實的自己⋯⋯。唉,而我想舌燦蓮花地大論特論,但突然覺得再講都是多餘。高速變調的媒體平台所致的知識片段化之下,如何「有機」,於今恐怕已非時尚。那麼,我們,我~,直接邀請你來讀我的詩好了。
卷一:「抾骨」(Khioh-kut),家族記事。阿公阿媽留下來的記憶深刻在我的意識底層,成為我前進的支撐。卷二:「青春ê遺書」(Tshing-tshun ê uî-su),成長記事。我年少的嚐試,我的青春思考,我的啟蒙,還有我的叛逆與憂鬱。卷三:「土地」(Thóo-tē /
Thóo-tī)。不同發音就有不同意義,前者指自然土地,後者指土地公。家園記事,捕捉一些早已凋零的故事或正在枯萎的智慧。卷四:「蠹魚」(Tòo-gû),家國記事。理想的走找之前與走找之後的喟嘆,以及我矜持的國族想像。卷五:「失語症」(Sit-gí-tsìng),戀戀母語。我的發音練習,還有我曾近於失聲的吶喊。卷六:「明信片」(Bîng-sìn-phìnn),愛情練習。紀念我已不再有的含蓄、熾熱,以及痴狂。卷七:「落雨彼日」(Lo'h-hōo
hit-ji't),詩寫二二八。我但願,存活下來的,都能成為見證,都能繼續傳承。
多謝林央敏先生推薦火金姑出版基金的助成,多謝前衛出版社社長林文欽先生的成全,多謝有為青年清鴻大力的幫忙,您們讓這本難產了六年的台語詩集,終於得已見到天日。也謝謝2007
年已幫我寫好序,那時還在英國牛津念書而現在已在新加坡教書的易叡,以及當年還是成大博士生而今已在靜宜春風化雨的惠豐,願意重新為他們當初給我的感動再繪上一層鼓勵,他們的序文彌補那已逝「青春」的空洞,也為這遲來的晴天,點綴了美麗的花色。感謝!還有,謝謝阿焜理解我當不成尪姨,只好終日帶著恍如隔世的心情牽引亡魂,感謝他細心的詩評!!也謝謝我大學時代就熟識的藝術家「網友」東橋,謝謝他提供畫作作為詩集封面,給這些近乎窒息的詩文們得到呼吸
這條路很長,願意走的人不多,但我不孤單,謝謝一路以來相伴的親友。而想想,寫了十多年的台語詩,似乎每次書寫,無論是窗外或心裡,都難得晴天。「落雨彼日」,是卷七標題,也是收錄其中的一首替二二八罹難者寄未亡人的詩,易叡曾將它譜曲歌唱,讓許多朋友在每年二二八時,隔空共鳴。倒是,記得那晚,走出那間live
house時,大雨已停,地面竟也乾了。同行的日本朋友還在嚷嚷,「剛剛那陣大雨到底是怎樣!彷彿什麼都沒發生!」想想,我們真的很快就會遺忘一些什麼吧!那,就以此為題,來紀念那些窗外戶內都下著雨的日子好了。
想回都蘭開演唱會的Suming,他的願望已經實現。而我也好希望這本小集子,至少,家鄉的人們,可以看見。
呂美親
2013.10.04,於東京都國立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