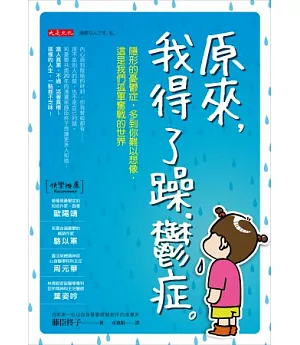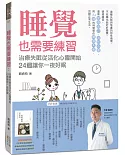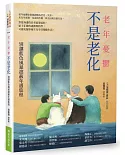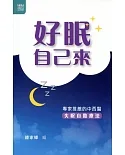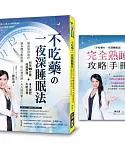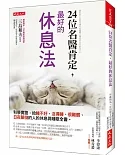推薦序一
用漫畫,了解大多數人不懂的疾病
周元華
憂鬱症是一項重要的疾病,此疾病的核心包括:情緒低落以及無法感受到外界的刺激與喜樂。約有一五~二○%的人,終其一生會有一次憂鬱症的發作。
憂鬱發作時,會令人有生不如死的感受。有許多病人告訴我說:「死並不可怕,但是這種生不如死的感受,實在令人感到不舒服。」
雖然,目前許多報章雜誌,均嘗試刊登憂鬱症相關的報導或故事,想讓社會大眾多了解這個疾病,並且強調憂鬱症並不是一般人口中所謂的「精神病」,但現實社會中,仍然有許多憂鬱症患者,因為害怕異樣的眼光,或是社會上對憂鬱症的刻版印象,而拒絕就醫及服藥治療。
《原來,我得了躁‧鬱症》,第一眼看到這本書的內容時,覺得以漫畫卡通的方式,深入淺出地傳達一項現階段社會大眾不太了解、也不願去了解的疾病,真的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本書中,使用了許多口語話的解釋,及生動的漫畫圖片用以呈現出對於憂鬱症(躁鬱症)的解釋;相信更有助於社會大眾對於憂鬱及躁鬱症的認知。
期望藉由本書的傳達,大家能夠更加了解憂鬱症及躁鬱症疾病,並且有更多的人一起關心幫助這些患者。如此一來,可提升患者與家人或朋友的相處之道,也將會明顯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
這是一本相當值得推薦的好書!
臺北榮總精神部心身醫學科科主任
推薦序二
給困頓中的你,相同語言的熱度及淚水
葉姿吟
個人內在深處湧出的一種極私密感覺,化為言語,該選用什麼詞彙?一個人的生活型態,化為文字,該是直白的敘述文、凝鍊的詩句、抑或曲折婉轉的短歌?
場景拉回鬧哄哄的精神科病房。一個甫披上嶄新白袍、臉上還沒有皺紋卻帶著黑眼圈的第一年住院醫師,如果他想要用最快速度,搞定面前眼神飄忽、自言自語的患者,最好還是乖乖根據精神疾病診斷學,判定一個病名、給他幾顆適合的藥。
「精神疾病的診斷」是一門大學問,集合全球最有學識及經驗名望的大師,歷經數十載,考量患者的症狀、苦惱程度、功能喪失、科學證據、甚至當代的文化社會背景,加以統計、分類、命名。這可以說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當然,也有人認為是自大的人類僭越權限,汙衊了造物主的創意。
因此,在精神醫學養成教育頭幾年,身為醫師的我們勤讀書、多接觸病人、每週開病歷研討會,其中很重要的一個目標,是訓練大家能用共同的語言,定義一位患者的各種症狀。當患者在有限的門診時間,詳細地描述自己的不舒服與生活的改變,我聆聽著,一收集到熟悉的詞語:「叮咚!症狀對號入座。」彷彿在玩賓果遊戲,期待早日連成一條線,宣判結果。
然而,一年又一年累積門診經驗,臉上的皺紋跟著白髮開始等比例增加,我漸漸了解,每個人的心理狀態與行為模式,可以用五花八門的方式來描述。
比方說,有些人會形容:「醫師,我就是典型的雙子座。」(內心OS:那你要不要去找星座專家?)有人說:「我遇到喜歡的事情就會全心投入,不怕任何困難,可是一段時間以後,又會完全提不起勁,最後就放棄了。這樣是不是很大的問題?」(可大、可小,不過,問題是什麼哩?)
還有人說:「醫師,妳知道嗎?我是個水晶小孩。」(什麼?這是什麼?)於是我又從專業的這一端,很緩慢地,學習貼近患者的「素人語言」,感受語言背後的熱度與淚水。
在一般人當中,憂鬱症和焦慮症是最常見的精神疾病,約占九○%,它們不包含嚴重的精神病,常和生活裡的壓力事件有關係,對心理健康傷害很大。
根據中研院鄭泰安博士的研究,近二十年來,臺灣的憂鬱症和焦慮症盛行率增加一倍,這個倍增的現象,正吻合同時期臺灣的失業率、離婚率、和自殺率的提高。隨著醫藥資訊的普及,知道自己的情緒需要幫忙,能夠走進基層診所或醫院,求助於精神科的民眾也增加了,但不可否認,仍有部分受到憂鬱之苦的人,惶惶然蹲踞在黑暗的角落,不曉得該如何是好。
這本書,開啟了另一種機會,或許受到親切可愛的畫風吸引,或許淺白真誠的短文更容易打動人心,我想像一個困在晦澀青春的中學生拿起這本書,我想像一個熱情幾乎熄滅、困在辦公桌的年輕人翻開扉頁……他們終於找到能夠表達自己的語言。
藤臣柊子,根據自身憂鬱的經驗(後來診斷改為躁鬱症),以漫畫方式呈現憂鬱初次來襲的衝擊、回顧習於壓抑又完美主義的個性、細述生活常規如何失調、二十年的就醫經驗、嘗試與憂鬱共存的心境轉換……笑中帶淚、淚中帶笑。
讀者可以輕鬆地跟著她幽默、但貼近真實的圖文,了解一個憂鬱症(躁鬱症)患者,生活中面臨的種種困難,也學習到基本的相關知識。最重要的是,藤臣柊子藉由漫畫天賦,抒發身為患者無法一言以蔽之的痛苦,我衷心為她感到高興。
祝福閱讀本書的每個人,也能找回屬於自己的快樂之道。
林青穀家庭醫學專科診所精神科主治醫師
譯者序
我以為我很懂,卻因此傷了家人
卓惠娟
作為一個長年陪伴重度憂鬱症患者的家屬,有幸接譯這本書,是一大幸運。
我的先生曾是重度憂鬱患者,在日本治療期間,由於醫療費用昂貴及生活開銷龐大等因素,幾年前,我們決定回到臺灣繼續治療。雖然,目前我先生的病況已大為好轉,但偶爾仍有突然陷入低潮,整天臥床的情況。與他結婚以前,我曾經一度接受憂鬱症治療,再加上多年來陪伴先生,我以為已經對此症狀相當了解。但譯了這本書,才知道自己太自以為是了。而這樣的自以為是,很可能在陪伴家人走過憂鬱期時,再度造成傷害。
翻譯這本書時,彷彿再次經歷了先生數次病發的過程。前一刻還精神奕奕地暢談未來的理想與抱負,下一刻意志消沉地表示:活著只會造成旁人的累贅。
尤其,作者寫到過度換氣症候群的經歷時,更令我感同身受。在結婚剛滿一年、居住在日本之際,初次經歷到我先生發生過度換氣症候群。病發前兩週,最後一次陪先生去看身心科時,醫生告知:原本由日本政府補助重度憂鬱的醫療金,將從下一次看診時取消,自付額將由原本的一成,恢復為一般民眾的三成。那次,當吃完所有藥物後,我先生決定暫時不去看診了,「反正有吃藥和沒吃藥都一樣。」
他除了擔心家庭經濟的負擔,也因為當時我對憂鬱症的一知半解,自以為是地告訴他:「心病重要的是解開心結,吃藥只會造成藥物成癮。」回想起來,我實在太過自作聰明了。
停藥的前兩天,雖然沒有發生憂鬱病兆,但失眠狀況相當嚴重,他完全睡不著。失眠第二天,他的精神狀況變得很差,幾乎沒有食慾。到了晚上,才勉強吃了一點東西,但夜裡卻全吐光了,這天仍是一整夜都沒睡。半夜數次他說手腳有麻痺現象,我只能幫他按摩稍微緩解。
直到失眠的第三天清早,他告訴我呼吸困難,手腳冰冷發紫,我連抱帶拖地勉強把他帶到附近的醫院。雖然,醫院距離我家步行只要兩分鐘的距離,但他踏出的每一步,都宛如在月球上漫步。
院方做了檢查,告訴我們確切的病名是過度換氣症候群,建議我們轉診到較大的醫院身心科,做更進一步的檢查。我先生認為如果要由身心科檢查,不如由原先的醫師看診。所以,我們拿了藥便先行回家休息。
回家後,我上網查詢了引起「過度換氣症候群」的病因,和緊急處置方式。讓我非常困擾的是──造成原因不明。只知道這和患者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基本上,壓力過大、容易緊張、焦慮的人,較可能出現這種過度換氣的現象。
因為過度換氣,導致血中二氧化碳過低,患者本身會有吸不到空氣、缺氧的感覺,所以會更加緊張,呼吸也不自主地變得快又淺,形成惡性循環。不過,這種病症發作時,當事人雖會自覺呼吸困難,外顯症狀十分嚇人,但並不會真的因為缺氧而死亡。處理的方式是一旦有自覺現象時,設法安定情緒。
看到作者獨自面對歷劫歸來的經驗,令我更深刻體會當事人處於憂鬱狀態時的痛苦──那是旁人無論如何都無法體會的。
有時看到先生陷入痛苦,自己當然也不好受,苦惱為什麼他不能想開一點?甚至暗地在內心責備他,有那麼多人比我們日子過得更艱難,為什麼他這麼不知足呢?
我一直認為我懂憂鬱症,看完這本書才深深體會到:這些話我雖然沒有說出口,但或許無意間傷害了他。
另外一個身為憂鬱症患者家屬的感受:臺灣在身心科方面的醫療環境,比先進國家日本友善得多了。日本由於醫療負擔昂貴,以及社會大眾普遍仍然認為憂鬱症患者是因為他們抗壓性不足或怠惰,因而在日本治療,除了經濟壓力,還必須忍受旁人異樣的眼光。
非常感謝大是文化能給我機會接譯這本書,也期盼出版後,能夠幫助許多在精神疾患上受苦的人,或是幫助更多像我一樣陪伴罹患憂鬱症(躁鬱症)家人的家屬。
本書譯者,走過憂鬱症並陪伴重鬱家人
前言
我與憂鬱症,和平共處了二十幾個年頭……
好久不見,我是漫畫家藤臣柊子(編按:一九六二年生,日本知名少女漫畫家,現以散文漫畫為主。曾演出NHK特集節目,談論躁鬱症)。距離上一次出版單行本(二○○九年出版的《今天果然又發作了──憂鬱症》),很快地已經過了四年的時光。
雖然,我一直希望這本書能夠儘早出現在大家面前,但是連載期間,我的身體起了激烈變化,甚至出現「呼吸困難」的狀況,只好含淚忍痛停止連載,真的對讀者們感到很抱歉。坦白講,當時我一度以為自己小命不保了(詳情請看書中第一四九頁)。
而且,就在連載《憂鬱轉晴》(譯按:連載於網路電子報《poplarbeech》www.poplarbeech.com/utsu/007395.html)期間,我的病名竟然變了。這一次診斷出的病名是「躁鬱症」(編按:作者罹患第二型躁鬱症,也就是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症〔bipolar II disorder〕。一次或多次的重鬱發作、伴隨至少一次的輕躁所組成)。
是的,我已經不再是憂鬱症患者。
才一年,我從憂鬱變躁鬱
在我被判斷出躁鬱這六年期間,真的發生了好多事(可是,六年也未免太久了吧……)。這些年歷經嚴苛又繁多的試煉,而凝結成這本書。
《憂鬱轉晴》的連載是從二○○七年開始。原本在網路上連載的內容,是曾經罹患憂鬱症的我,從第三者的觀點、透過漫畫,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讓讀者了解如何與憂鬱共處的方法及另一種思考,並藉此提出親身經歷的建議。
一開始我還能遵守截稿日期,在工作上全力以赴。然而,不知為什麼,漸漸地我再也畫不出來,一再拖稿,到了隔年二○○八年,完全跟不上連載的速度。
從那時開始,我便感到自己內心似乎開始有寒風掠過,這股寒風最後終究形成了暴風雨……。
事實上,我已經無法再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談憂鬱症。因此,不得不回到憂鬱症患者的身分(當時仍然是憂鬱症)、治療的最前線,而在垂死奮鬥中,醫生對我正式宣告:我罹患了躁鬱症。
憂鬱症和躁鬱症的症狀不同、處方當然也不一樣。但是,同樣屬於心理的疾病。
目前,日本有非常多人患有心理疾病(編按:根據日本大學醫學部精神醫學系內山真系主任表示:「日本的情緒障礙患者年年增加,其中憂鬱症患者的人數,從一九九六年的二十萬七千人,到二○○八年已增長到七十萬四千人。這數目只代表因心理相關症狀就診的人數,而潛在的憂鬱症患者,可能會是這數目的好幾倍。」),其中多數人的共同煩惱,就是患者外表看起來和健康的人毫無兩樣。若不具知識的專科醫師,便難以判斷是否罹患這方面的疾病,更何況就連醫師在診斷上也有其困難點。
這對患者及其親人而言,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因為外人難以理解其中的情緒,總忍不住心想:「這樣的痛苦,該不會只有自己才了解吧?」抱持著這樣的心酸認知努力活下去,你是不是也覺得總忍不住落淚,感到寂寞無助呢?
內心感到陰暗的時刻,你我都有
憂鬱是一種疾病,任何人都可能罹患憂鬱症(編按:據中研院統計發現,近二十年來,臺灣常見精神疾病如憂鬱症、焦慮症的盛行率,從一一‧五%上升至二三‧八%)。很多人都以為自己絕對不可能有心理上的疾病,然而,能夠確實掌握自己當前心理狀況的人,究竟有多少?
就像是三一一大地震(二○一一年三月一一日,日本發生的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核電廠輻射外洩……這些意外的發生,也沒有任何人可以預測或是完全掌控。
在這樣不可知的情況下,我呼籲大家對任何事都保持平常心……雖然,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我們每個人在面對生活時,多少都會壓抑、忍耐,而這樣的忍耐會對心理造成負擔,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數當然會增加。
二十四歲時,我第一次被診斷出憂鬱症,回想起來,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這段期間,我並非一直處於憂鬱症的病情中,當時曾一度痊癒,然後我賣力地工作畫著連載,藉著取材到日本各地旅行。
心境再次產生變化的那年,我三十四歲。「難不成憂鬱症是十年一個周期嗎?」我忍不住這麼想。從那時到現在,幾乎每天都必須服藥治療。
一如身體的狀況有起有落,心情同樣浮浮沉沉。有時,心情好得不得了;有時卻完全爬不起來,連著好幾天躺在床上……。這樣的情況對我來說,根本是家常便飯。遇到這樣的狀況時,著急也沒用,唯一能做的,只有在暴風雨中等待風平浪靜的到來。
和憂鬱相處超過二十年,這些日子裡我盡可能避開人聲鼎沸的地方、避免和言談充滿消極晦暗的人共處。這樣的控制方法出乎意料地,竟能和憂鬱症建立出和平共存的關係。
要是自己罹患了憂鬱症、或是身邊重要的人罹患了憂鬱症,這並非絕對不可能發生,因為,任何人都有內心感到陰暗的時刻。而這樣的狀況可能加重,甚至惡化。
那麼,究竟該怎麼辦才好?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說不定根本沒有標準答案。
我不敢大言不慚地說自己的經驗能夠對大家產生什麼助益,因為每個人內心的煩惱都不同,就像地球上沒有兩個百分之百相同的人一樣。我認為和別人不一樣也無所謂,沒有必要勉強自己去遵守傳統規範。
所以,我仍是真心期盼能透過這本書,將「和別人不一樣也無妨」的想法傳達給更多人,便感到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