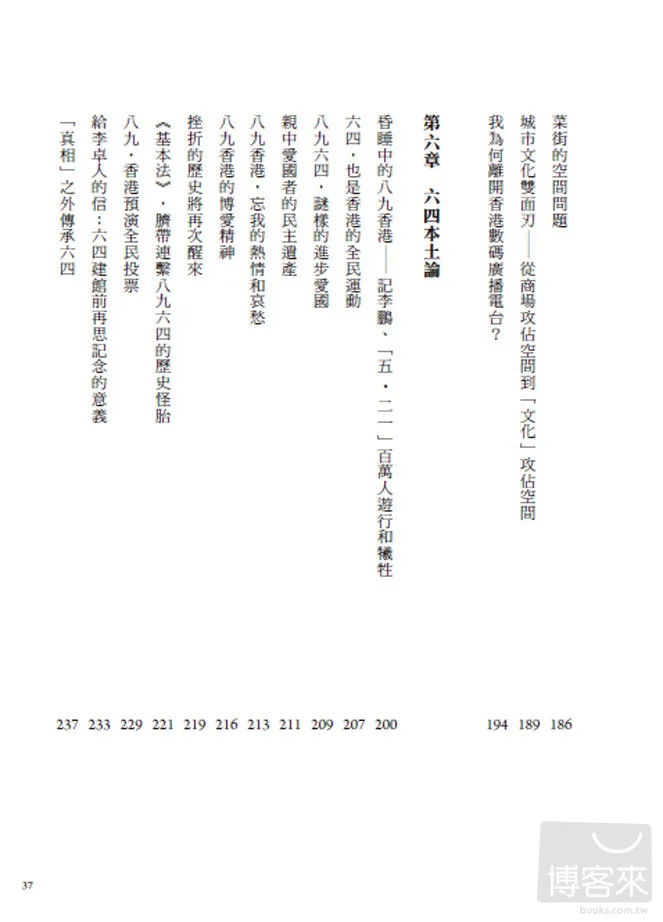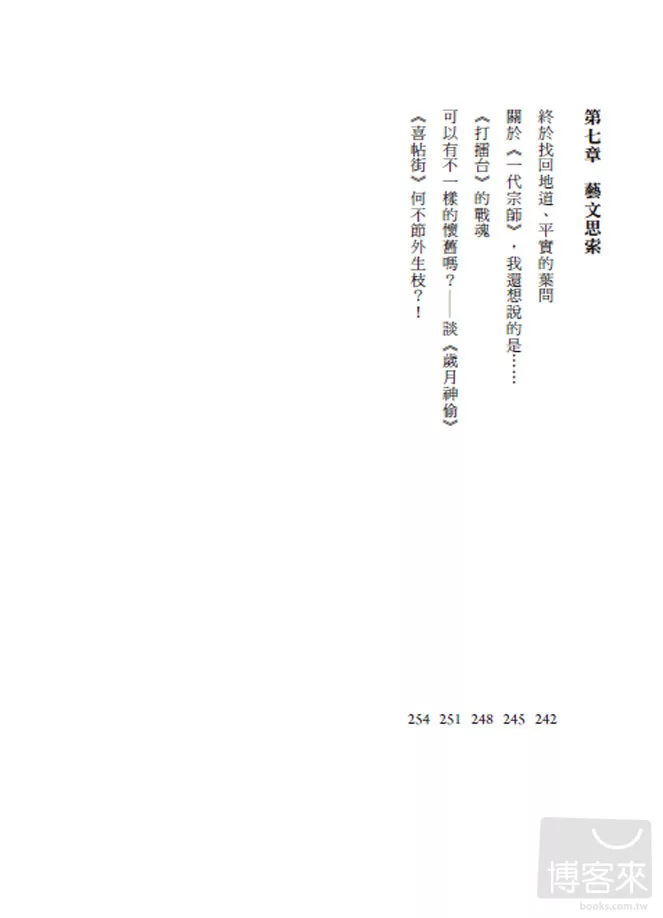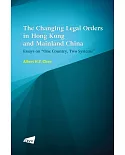自序
草木皆兵,或一個心口寫了「反」字的時代
1
這本文集的誕生,出於一份迫切的需要,就是對當下的政治化浪潮提出分析,以使香港人真的能夠走近她原來要去的政治目的地,而非迷路收場;其次,適逢今年是0371 十周年,筆者也想為這十年的公民社會,下個註腳。本書的評論大都是這十年之間蘊釀和寫成的,內容針對好幾場帶有啟蒙作用的社會運動,以及一些具爭議性的公民社會議題(如蝗蟲論、鬧爆文化和警權問題),因而也不失為一份側面紀錄(註1)。
尚有一部分,是筆者對於香港六四史的整理。有好幾個月,我就一個人坐在圖書館翻看舊報紙的幻燈片,疏理八九年的香港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於我而言,六四從來都是一件很本土的事,而不只是發生在天安門廣場。
這裡的大部分文章得以寫出,很重要是《明報》世紀版願意刊出,這?先感謝馬家輝先生的賞識和支持。
2
2003 年至今,十年來,這個城市的論爭和對抗有增無減,如果要濃縮成一句話,我會說,這是香港社會「反對意識」茁壯成長的十年。在此,我說的反對,預設了權力的不對等,是「民主反對專政」、「無權者反對有權者」或「邊緣反對主流」的那種具批判性的「反對」,因而,愛港力一類替建制護航的所謂反對聲音,並不包括在內。
「反對意識」的成長,基於很多原因,包括中央愈益介入、舊意識形態的殞落(例如地產霸權)或政治體制追不上時代步伐等,凡此種種都引來民間反彈;又或是反過來說,新價值新觀念在本土的橫向擴散,像是地方認同、行動意識或多元精神的增強,加上網絡媒體的普及,也都同樣加速了「反對意識」的萌芽。
可以說,所謂反對,很多時意味?兩項功能:一是防守性質的,例如防止原有的社會腐化倒退;其次是進取型的,由無到有,它為未曾出現的烏托邦而戰,讓社會走前一步。
3
也許,貫穿這本書的其中一點,就是持續分析和思索由這些「反對意識」所構成的社會運動(或相反,由運動孕育並傳播開去的「反對意識」)。畢竟,既得利益者不會自動放棄特權,正所謂民主不是賜予的,反對運動因而擔當了重要角色。
但是,我發現自己的評論位置,早期是一位純粹的「翻譯者」,那時,我企圖將反對運動中隱而未顯的進步觀念,嘗試向讀者介紹勾勒(翻譯)出來。記得大學時一位老師說過,社運在文化和知識的生產上,總是處於落後一方,因為建制資源充沛,而他們的教義早已獲得主導地位。所以,我當初給自己的寫作任務,就是說清楚那微弱暗啞的一點點反對道理。但近兩年,隨?舊體制的意識形態逐漸瓦解、激進政團相繼冒起、網絡鬧爆的渲染擴散、教主教徒的增生繁殖,我就開始不滿足於做個純粹的「翻譯者」,而漸漸走向批判的位置上。
4
近年,反對運動的蓬勃成長,當然綻放出推進社會的光明一面(例如由九十後引爆的反國教運動),但另一邊廂,也有其陰暗一面。
例如,以網絡為基地,活躍於政壇的政治激進派,便終日沉溺於「同路人危機」此一自製稻草人,不斷黨同伐異。網際網絡上,以民主之名發出的惡毒攻擊,層出不窮,甚麼「左膠」、「飯民」、「大中華膠」、「佔領光環」、「賣港賊」、「雲端文化人」或「維穩社運」等,數之不盡。
這就是我所謂的陰暗面,即:敵意,以其最本能的方式爆發,敵人的涵蓋範圍不斷擴大,不僅要打倒舊敵人(如建制派),還將槍口對準所有溫和主義、路線不同者,以及任何對於社會變革反應稍為遲緩的人群、事物或惰性。政治,彷佛成了一樁只有敵人而沒有客觀限制的反對事業,籠罩在一股無根的革命狂熱之中。
弔詭在於,在此消彼長的原理下,當敵人的範圍無限擴大,人民或盟友的範圍就會不斷萎縮。因而近年,我反覆思索的就是此一敵意失控和蔓延的現象,思想它到底出了甚麼毛病。
5
常說,政治是敵友之分,因而,沒有敵對並不構成政治。但其實人們談得較少的是,若然政治上沒有朋友,也同樣成就不了政治。
從朋友一端思考政治,它便意味?友愛、互惠、聯合、團結和結盟。它的政治性格,體現在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上,那就是,反對運動若要成功,它必定是建基於廣泛的社會連結和合作之上。反過來,胡亂樹敵,只會使自己陷於孤立。因而,政治必須為陌生人、朋友、盟友和意見不同者,努力創造出廣闊的政治合作空間,或至少贏取廣泛的支持和認同。
就是說,政治的困難之處,也許不在於四面樹敵,而是如何創造朋友、如何將社會不同力量拉到自己的一邊,建立足以跟統治當局匹敵的反對者聯盟。
其次,那股覺得「當下可以推翻一切」,從而敵視一切的革命狂熱,通常都低估了客觀形勢的艱難險惡,脫離歷史現實。即使今日香港面臨主流秩序日漸瓦解的局面,但它的殘餘碎片和餘溫仍然是舊世界抗拒轉變的一股強大的社會穩定力量。
社運的難題在於,知道社會糟透的人很多,但站了出來、願意行動的人卻不夠多。因而,社運的任務就是進行一場社會的轉化,以一種極其溫柔的力量喚醒人心,叫原來不願意行動的人,最終也都行動起來(當然,這得順應不同的歷史條件和議題特性,作出部署和設計)。因而,難題根本不在於有沒有發起激烈抗爭,不管是拉布、堵路抑或佔領,而是這些抗爭如何才能引發廣泛群眾的共鳴(而非反彈)。這往往需要長時間深入民眾的準備工夫,才可鬆動和轉化社會那股深層穩定力量。
凡此種種,都不靠鬧爆完成,畢竟革命不是打嘴炮。
6
最後談談敵意失控所造成的政治損害,最災難的當是自我毀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當然是法國大革命中的雅閣賓專政,當初的革命同志因為政見不同,幾年內就成了這個共和國的內部敵人。相互殘殺的結果是,他們的下場跟法王路易十六一樣,一個接一個走上了斷頭臺,名字包括這場大革命的重要人物丹東、聖茹斯特和羅伯斯比爾等。
可見,從革命狂熱引發起的「同路人危機」,以至永無休止的自我戰爭,歷史上已有發生。可以說,短短幾年,本地激進政團的不斷內鬥和分裂,並非偶然,而是敵對性失控的正常結果。
其實,破壞已經十分明顯,它導致大量無謂的爭吵、真正敵人的逃之夭夭,並出現厭倦政治的社會暗流等。這令人聯想到現代政治學所說的自然狀態(一個政治學的假想狀態),即每個人反對每個人的戰爭狀態。在這個永不止息的干戈狀態下,公共生活或反對運動都注定難以沉澱發展。
這是因為:活在一觸即發的攻擊威脅下,人們不再願意說出、做出或想像出任何稍具風險的主張、行動和事物。事實上,為了避免遭網絡或政治批鬥(往往上綱上線),不少有識之士也減少發言,或只在政治正確的範圍內說話。荒誕是,在政治化如日方中的今天,公共討論卻是貧瘠得可憐,它既沒幾年前的多樣化,更遑論深度,只聞聲聲表態和鬧爆。
在這種背景下,我開始思索反對運動的另一些向度,包括公共交往的起碼規範、政治作為合作事業,以至從友誼一面反思政治等,這都在本書中可以找到。凡此種種,就是不想「反對」這個概念變得庸俗化,我想,沒有比台灣政治學者錢永祥說得更好的了,讓我引述他一段話:
「『反對』這個概念的庸俗化,比其他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殘忍,因為這代表對抗庸俗化的最後防線也告失守。」
「反對」,既是社會的最後防線,也是進步的希望,因而有了這本書,是為序。
註1 讀者留意,雖云是側面紀錄,但在這次出版過程中,本文集中有小部分舊文章是經過修改的,也有新增內容。文章的修改大多是輕微的,有幾篇則是因本文集的出現,而重寫和首次發表,包括〈題解:何謂全面政治化社會?〉、〈《基本法》,臍帶連繫八九六四的歷史怪胎〉、〈八九年,香港預演全民投票〉和〈快樂抗爭,或政治生活的審美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