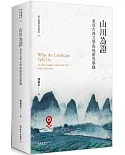自序
台灣文學研究:「豐富和豐富的痛苦」
《台灣文壇的「實況轉播」》是書中評王鼎鈞《文學江湖》的一篇文章題目。借它做書名,是想說明複雜豐富的台灣文學有許多「實況」需要大家去瞭解;台灣作家前赴後繼的創作勇氣、毅力和實績,其中也必有可「廣播」宣傳與研究之處。在網路時代,做「實況轉播」的播音員未免有點古裡古氣,好在本人姓古,故用古舊的方法向讀者及時報告台灣文壇的最新動向,也就心安理得。報告方法沒有後現代後殖民,文體不止掃描、論述、序跋,還有由實地考察寫出來的訪台記,大都發表在北京《中華讀書報》上。
台灣文學於我,可借用穆旦的詩句「豐富和豐富的痛苦」來形容。之所以「豐富」,是因為在我現今出版的四十九本著作中,有十三種在台灣出版;我擁有的台灣文學資料之齊全,據說在大陸學者中是為數不多的一個。之所以「痛苦」,是因為書到用時方恨少,研究台灣文學私人藏書再多也比不上島內的大學圖書館;在工作單位沒有同行可切磋,只好靠頻繁外出開會交流,以至被文友戲稱為「無古不成會」或「逢會必到古遠清」;沒有行政資源的我,搜集資料只能另闢蹊徑,像螞蟻搬家一點一點從境外運回來。當我找到新的學術生長點時,卻苦於來日不多和沒有助手,不能把自己想做的課題在有生之年完成。
進入台灣文學研究領域,原本是一九八八年被花城出版社約寫《台港朦朧詩賞析》拉下水的,至今回憶起來也恍然如夢中一般。在此之前,我研究魯迅,研究大陸詩歌,研究大陸文論,成績平平。可自從深陷台港文學研究泥塘而不能自拔時,這些台港作家幾乎改變了我的人生。竟想不到《台港朦朧詩賞析》在遭到對岸痛批的同時發行了近二十萬冊,為進一步研究逼得我天天在書上和這些台港作家見面,日日和繁體字書打交道,還不常和某些台灣作家進行「私人戰爭」,打完筆墨官司後為補充新的養料便到海內外雲遊裡開會、講學或採購資料。雖然研究華文文學耗去了我大好光陰,放棄了所有節假日,但總算幸運,研究成果基本上能得到發表且從不自掏腰包出版。這次便受到台灣青年學者楊宗翰先生的鼓勵和支持,才使得我近期發表的文章能及時地匯編在一起和讀者見面。
我一生道路坎坷,雙親目不識丁,小時候由人販子賣給地主做過短期的貴族公子,土改後回到老家,放牛砍柴種地挖煤當苦力樣樣幹過。在狗眼看人的喧囂時代,我這種經歷竟被某文化名人在其新出版的自傳中拿來大做文章,稱易中天、古遠清「那幾個『偽鬥士』的惡,大多是因為從小缺少善和愛的滋養,形成了一種可謂『攻擊亢奮型』的精神障礙,其實都是病人。例如那個糾纏我最久的人,小時候居然是被父母親當做物品賣掉的」。吳拯修對此反彈說:「領養小孩就『缺少善和愛的滋養』嗎?余秋雨甚至忘記了,他在《借我一生》中曾經告訴過讀者,他家中就有一個從小被領養的表妹。難道余秋雨他姑姑的女兒也是有精神障礙的病人?」劉中國也說:「古遠清的個人痛史,居然被大言者鍛造成一根敲打不幸者的苦喪棒,但這一不小心卻暴露了『文化學者』皮袍下面那點兒貧血的『人文情懷』」。
我每次到台灣進行學術交流,有關部門都要對我「政審」,要我從「文革」經歷開始「坦白交代」。我敢說如今「組織部」及「台辦」的負責人,大都沒有經歷過那場十年浩劫,不知道我們這代人遭遇之悲慘。以我在「文革」初期而論,作為「五.一六」傳單的報案人,竟陰差陽錯成為作案人,由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關押了半年。接著是不了了之,主事者送給我一朵大紅花下放當農民,邊勞動邊改造邊檢查邊交待,交待不出來便﹁控制使用﹂,倒從此換來無官一身輕。大學復辦後,我在沒有中文系的學校裡邊教邊寫,可說是單槍匹馬,孤軍奮戰。在這個以學術團隊著稱的時代,我顯得不合流,不入流,一直孤寂冷靜地處在邊緣。好在到古稀之年「自力慶生」時,文友為我打氣為我鼓掌,還有七個國家四個地區的一百多位海內外作家寫了《古遠清這個人》同題文章慰惜我,後結集成書出版,其卷頭語有云:
古遠清是誰?他古怪,是牛虻,是老農,是書癡?是常青樹,是「劊」子手,是學術警察,還是古裡古氣的武林人物?綿綿秋雨打濕過他的衣裳,但他仍是翻飛在海峽間的「勞燕」,無論是論戰還是呼嚕均一級水平。
《台灣文壇的「實況轉播」》「個人鋒芒」欄目內「冷眼看李敖『屠龍』」,便屬「牛虻」式文章。給對岸《台灣新文學史》著者及李歐梵挑錯,做的便是互相敬畏、互相監督、互相批評類似「學術警察」的工作。我這位書癡或曰「武(錯!應為「文」)林人物」近兩年在台灣接連出版了《消逝的文學風華》、《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從陸台港到世界華文文學》,現在又有這本新書奉獻在讀者面前,在出書速度上也稱得上是王劍叢教授所說的「劊(快)子手」。至於「實地考察」中所穿插入的「余光中同志」、「兩岸三地作家笑談『匪』」一類「野味文壇」式的段子,是「翻飛在海峽間的勞燕」(□弦)銜來的一花一草,它不似「呼嚕」勝似「呼嚕」,正好給讀者催眠。正如澳大利亞作家莊偉傑所說:「『野味文壇』真正是野味十足。野在古遠清畫龍點睛式地把多位現當代文化界名人的軼聞趣事一絲不掛地公諸於眾,這種勾勒妙在真實和風趣。在這樣一個不太天真的時代,集體庸俗、集體狂歡已被物質奴化,有誰還如此狂野天真?」當有讀者問我這些花絮包括在廣州《羊城晚報》連載的〈文飯小品〉材料是從哪裡來的,取得後又如何加工?這應是「老農」另外一椿「妙處難與君說」的秘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