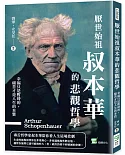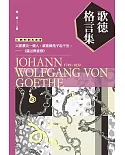新序
在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中,總有人會想要叩問:為什麼世界變成現在這個樣子?而不是別種模樣?其理由何在?這種類型的問題,往往予人以「大而無當」的印象,但卻也是我們能夠超越既定框架,更深一層認識世界的契機。我一直相信,韋伯對於資本主義、宗教文化、支配機制……所提出的無數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把視野格局放大,納進各種貫時性的發展脈絡,以及共時性的泛文化比較,真正勾勒出現代文明波瀾壯闊、浩浩蕩蕩的「理性化」進程。
當然,韋伯有他的知識侷限,又常被貼上「西方中心主義」的標籤。只是將心比心,我們自己是不是也脫離不了某個特定的「文化中心主義」?或如詮釋學所示,每個人認識外界事物,總少不了從自己的「前判斷」(Vor-urteil)出發,不可能完全沒有「偏見」。而韋伯曾經特別強調「價值自由」,提醒研究者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價值判斷」可能會扭曲「事實判斷」,因此時時要把持住學術倫理的底線,不能放任過於主觀的價值立場損害到社會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就此來說,即使經過了一百多年,當代學者有把握比韋伯更服膺於「免於價值判斷的自由」,更認真追求事實與真相嗎?
或許這正是韋伯的思想學說,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不僅僅提供了後世學者源源不絕的問題意識,還在諸多人類社會現象的考察上,奠下了厚實的基礎,成為社會科學不斷超越前進的重要後盾。由於韋伯學說具有「經典性」、「當代性」,以及「現實性」,在出版《韋伯學說新探》一書的整整二十年後,我決定再一次以不同的版本,呈現個人研究韋伯的心得予讀者。
本書主要增加了作者一九九九年後發表的論文,在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九之間有關韋伯的研究成果,另收錄在《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實踐》(顧忠華,1999)一書中,包括〈資本主義與中國文化:韋伯觀點的再評估〉、〈儒家文化與經濟倫理〉、〈孔恩、韋伯與社會科學的典範問題:從經濟學史的「方法論戰」談起〉、〈巫術、宗教與科學的世界圖像:一個宗教社會學的考察〉,以及〈自由主義與德國的命運〉等,讀者可自行參閱。本書與原版本《韋伯學說新探》不同的地方,是刪除了兩篇書評,另外加上了六篇新的論述,並在〈《韋伯全集》的編纂工作〉文後,附上截至二○一二年底最新的出版訊息,其餘篇章皆未作大幅更動。
如前所述,韋伯十分在意社會科學的研究倫理,我個人過去從俗使用「價值中立」來翻譯Wertfreiheit,但愈來愈覺得不妥,因為「中立」意謂「不表態」,這其實不算是一種「自由」,反而相當嬌柔做作。至於有些翻譯譯成「價值無涉」、「價值冷漠」,更是完全偏離韋伯認為研究者也是「文化人」,不可能不受價值影響的主張。他是太清楚價值的「滲透力」,才會像「唐吉訶德」般,要挑戰「價值」與「事實」徹底切割此一不可能的任務。但他絕不會將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對他來說,正因為價值太複雜了,必須好好討論,所以反對研究者過分天真地以自己的價值判斷去衡量經驗事實,如此方能確保知識不會淪於為政治、經濟、宗教或任何「非科學的價值」服務。為了正本清源,我在本書中收錄了兩篇討論「價值問題」的論文,並將以前使用的「價值中立」一詞,全部改為「價值自由」,這是比較大的變動。
另外一篇〈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韋伯學說的當代意義〉,則是因應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探討「資本主義」在中國能否真正發展的長篇文章。我們都觀察到中國在短短三十年間,有效地利用市場經濟制度,大幅度地累積了財富,但是,這代表資本主義已經成功地在中國生根了嗎?表面上看來,中國引進的各種市場機制,已然取代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列舉出來的「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因素」,加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無異於鏟除了根深蒂固的「傳統主義」根基,如氏族、鄉紳、地主及習俗迷信……等,為貫徹經濟改革措施鋪平了道路。
只不過,涉及到韋伯最重視的「精神」要素時,我們可以說,中國幾乎看不到努力與普世價值─如人權、自由、民主─等文明準則接軌的徵兆。現代中國只是由「家天下」統治形態轉換為「黨天下」,對於如何建立民主政治、獨立法治,以及公民社會,始終仍是拒斥多、配套少,以致於經濟繁榮製造出嚴重的官僚貪腐問題,同時也在權力不受制衡的失衡狀態下,「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統治階層只能以超過國防預算的「維穩」成本,勉強維繫政治支配與社會控制。如果用韋伯的概念,這樣的經濟體制不能稱之為「現代、西方、理性」的資本主義,頂多是「內政剝削式資本主義」的新形態,或如西方觀察家冠上的「權貴資本主義」稱號。
中國是否能夠有所突破,朝向一個更長治久安,而非領導者自己承認不肅清貪腐,勢必「亡黨亡國」的境界前進呢?我在這篇論文中,仍是寄希望於「公民意識」的覺醒,因為唯有多數人民體認到,自己的權利應該自己來維護,伸張作為「主權者」的集體力量,才能真正塑造一個具有「現代性」意義的「公民社會」,而這樣的「精神氣質」(ethos)也才能夠支持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以及正當運作的民主政治。
其實這亦曾是韋伯關懷的焦點,回顧韋伯的背景,他出生於一八六四年,當時的德國屬於工業化的「後進」國家,而韋伯一九○四年發表的成名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主要在分析資本主義如何型塑了現代社會的組織原則與發展邏輯。在他看來,德國雖然在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下,走向了「帝國崛起」,但是也因為俾斯麥的獨斷獨行,使得德國的中產階級缺乏了「政治成熟」,無法像英國或漢撒同盟城市中的市民階級般,發展出一種具有公民意識的自治模式。換言之,韋伯認為德國中產階級無法承擔起應有的政治責任,原因不在於它的資本主義性質,恰恰相反,是它還不夠資本主義化!(引自Bendix著,劉北成譯,1998:38)
所謂「還不夠資本主義化」,我們不妨解釋成:雖然韋伯明白指出,現代的資本主義已經是一套「銅牆鐵壁」式的經濟體系,其運作不需要再依靠早期新教徒的宗教信仰,光是「利潤」本身就足以燃起無窮動力。但是資本主義作為決定現代生活方式的一整套機轉,其中的社會成員──尤其是中產階級──仍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志業倫理」或「工作倫理」,資本主義方可能保持創新的活力。在此同時,這些「公民們」更不能忽略了在「法制型支配」下的政治參與,展現民主的成熟度,並要求政治領袖力行「責任倫理」。韋伯一向強調,現代人應該具備獨立自主的「人格」,而不是卑躬屈膝地向權威臣服,或完全受制於官僚機構的繁文褥節,甘於做個小螺絲釘似的「秩序人」。
因此,在韋伯的心目中,現代資本主義釋放出來的自由,是鼓勵個人發展個性,進行全方位的社會參與,包括積極行使公民權利,共同創造公共福祉。假使中產階級缺乏政治承擔,政治領袖爭功諉過,企業家則是毫無節制地攫取暴利,那麼,就如韋伯描繪的「末日景象」:「沒有精神的專家」和「沒有情感的享樂者」盤據了所有資源,一切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錢交易,乃至於暴露出人類最貪婪的醜惡嘴臉。
這種「去精神化」、「無血無淚」的資本主義,可說駛離了原先充滿意義感的歷史航道,變得面目可憎,也是韋伯非常真實的一種預言,因為它不正反映了我們這時代親身經歷的夢魘嗎?二○○八年的金融海嘯,打得原本自認為登上「全球化」頂峰的資本主義踉踉蹌蹌,差點滅頂。許多商學院也才承認「企業倫理」或「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不再一味歌頌不擇手段的獲利策略。
所以,資本主義似乎走過一個循環,需要重新探尋真正能永續經營的「經濟倫理」,而非任由掠奪式的金錢遊戲不斷擴大貧富差距、毀壞了社會連帶。在這樣的氛圍下,「佔領華爾街運動」像是點燃星星之火,誰能保證未來不會形成燎原之勢?放眼全球人類的未來,不只是中國必須改弦更張,歐美國家在重重危機下,除非公民社會能孕育出新的「精神氣質」,壓抑住急功近利、需索無度的營利欲望,否則資本主義無從找到浴火重生的正確路徑。
最後,本書的出版,要再一次感謝內人陳惠馨教授,她致力於學術論述,給了我不少啟發和激勵。另外也感謝開學文化的同仁,特別是執行編輯施榮華。希望不管是新文或舊文,都還能讓讀者一窺韋伯學說的堂奧,並繼續追索我們這個世代又為人類歷史創造了何種文化意義!
作者謹識于思湧齋
2013年1月
原序
本書收錄了作者近幾年來關於韋伯研究的主要論文、書評以及演講紀錄,雖然表達的形式不一,但這些文章共同的焦點都集中在對韋伯學說理論的評介與闡述上,因此以《韋伯學說新探》總其名。韋伯的思想體系可用「博大精深」來形容而當之無愧,不過他的觀點見解除了會受到自己所處時代的約制之外,後世出現的每一種「韋伯詮釋」同樣也烙印著當時流行心態的刻痕。本書論文部分的〈韋伯詮釋的典範轉移與韋伯學研究〉和〈現代性的社會學分析─從韋伯到哈伯馬斯〉,便嘗試運用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探索「文本」和「詮釋者」之間對話主題的遞嬗,同時希望能夠釐清韋伯學說在各階段中所起的啟發作用。至於這個「文本」的全貌以及其間「作品史」(Werkgeschichte)的關聯,在德文《韋伯全集》的編纂計劃下逐漸浮現完整的輪廓,〈《韋伯全集》的編纂工作〉報導了此一計劃的基本構想和特色,或可供作理解韋伯之學術貢獻時的參考。
另一方面,韋伯以「西方文明之子」的身份對世界各大宗教的比較研究,迭引起學者們反覆討論的興趣。本書〈韋伯《儒教與道教》一文的方法論基礎〉和〈經濟倫理與資本主義─從《儒教與道教》談起〉,分別就韋伯宗教社會學的內在邏輯和外部效應申論其層層相扣的問題意識、方法得失,以及我們若欲將韋伯式解釋模型應用於台灣發展經驗時的困難所在。嚴格說來,韋伯和我們今天現實處境的相關性,與其說是直接承繼自《儒教與道教》中的論證分析,倒不如說是間接地、迂迴地透過他對生活在(由資本主義型塑出來的)「現代條件」下之「人類命運」的診斷,才得以突顯其密切程度。亦因此,台灣韋伯研究的社會學意涵,或許不在於強調韋伯的「中國觀」是否有「西方中心主義」的偏差,更重要的任務應該在於汲取他的理論洞見,藉以考察社會文化變遷過程中的各種普遍與特殊質素,進而對現狀「之所以如此」能有多一分的自我認識。這是作者小小的心得,但也是一種期許、一個還有待努力的未來研究方向。
本書〈韋伯學說四講〉的內容,可看作是論文部分的延續與補充,在此要特別感謝政大社研所柯勝文、石計生、梁淑玲、夏春祥和張志浩五位同學的熱心協助,使演講錄音能夠形諸文字。也要感謝唐山出版社的積極配合,內人惠馨的鼓勵,和在學問上提供切磋機會的諸多朋友。最後,記得一八六五年提出「回返康德」口號的李伯曼(Otto
Liebmann)曾說過:「你能夠同康德一起研究哲學,或者,你能夠利用哲學推理去反對康德,但是你離開了康德就無法研究哲學。」作為社會學思想源頭之一的韋伯,在他去世七十年後也因類似的理由經歷了「韋伯復興」的熱潮。即便現代社會學的專業分工愈益精細化,以韋伯為代表的古典傳統畢竟仍舊是孕育和滋潤「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的豐腴土壤,開放給後人繼續播種、耕耘。
作者 謹識
19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