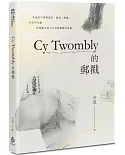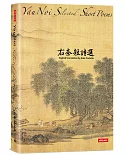推薦序
告別的姿勢∕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星洲廣場》主編、小說家 黃俊麟
明霞的詩作大部份可說是自己的心情記錄和寫照,除了少數幾首明顯涉及現實的課題(如〈不在現場〉、〈如果戰爭不在遠方〉)外,其餘的無論是描寫生活瑣事(〈午後假寐〉、〈獨坐〉、〈人間〉、〈安靜並且緩慢地墜落〉、〈小星星變奏曲〉……)、分別或別後重逢的心緒(〈未竟的姿勢〉、〈消息〉、〈中年對飲〉、〈有一天〉、〈後來的夏天〉……)、傷逝過去時光和理想(〈無題〉、〈大河〉、〈時間的情節〉……),在我看來,都與回首、記憶有關。
也許可以這麼說,這本詩集無疑是一種告別過去的姿勢,而「悼念」是唯一的主題──那些年輕飛揚的熱情理想、信仰堅持、青春情事再也不復返,若非用文字、以詩「留給遺忘一點證據」(送行),埋藏的記憶早已說不出具體的事項,徒留懊惱神傷。
以上所言純屬揣測,雖然從事文藝副刊編輯十餘年,但坦白從寬,至今我仍不懂詩。
總覺得詩人摘取的吉光片羽,就像是靈光一閃的意念,難以捉摸。我只好用斷章取義的方式拼湊明霞的詩句完成這篇言不及義的觀後感,「一個不留神,很容易被誤讀為∕故作姿態底留白」(那些未命名以及未完成的),為免說得太多錯得更多,丟人現眼,還是就此打住,讓「回憶如霧∕漫過傾圮底時間長廊,輕手躡足∕沿過往線索拾階而下」(時間的情節),往歲月的未知處踟躕走去,一轉眼,竟已來到後青年期的末端,感慨青春的尾巴早已失去,接下來要面臨的是過早的中年心境。
今後我們還得「將中年的卑微喝盡」(中年對飲),再次上路,「在逐漸遠行的路上曳成一道歲月∕淡淡爬過的記憶毛邊」(送行),期待下次相逢,可以微笑共話清風明月。
導讀
只有生命才能安慰生命∕作家、紐西蘭國會議員 霍建強(Raymond Huo)
《紅樓夢》借甄士隱解「好了歌」,把現實人生比作暫時寄跡的他鄉,而把超脫塵世的虛幻或理想世界當作人生本源的故鄉。無論他鄉故鄉都是人生必經所在。因此,他鄉故鄉實際上是人生的一種平衡、一份把握和修身養性的一個取向。我就是以這種心態來閱讀明霞的詩集,明霞的詩也正是這樣老老實實又認認真真地談天說地,用文字、用意象、用氣息,將我們帶入她用一種詩的張力所營造的世界,去體會她形神互動、思言並行的某些衝動。
美國鄉土詩人羅伯特.弗羅斯託(Robert Frost)給詩下的定義:詩就是「在翻譯中喪失掉的東西」(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如果把「翻譯」這個詞替換成更中性的「詮釋」,讀明霞的詩,似乎感到她想把詮釋中丟掉的東西再凝結起來,經過蒸餾,再釀成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和作品。
詩四輯,收集了她從1993年到現在的幾十首長短不一的詩。「莫掛串風鈴∕就怕那風∕喚醒我蟄伏已久底,寂寞。」(寂寞的盛夏的窗有三說)似乎欲言又止。這是1993年夏寫的。到了秋天,「今夜,月光溫度恰好∕足夠冰鎮一壺∕陳年相思」(消息),似乎尺度大了一些,也肯讓「陳年相思」被月光的溫度去冰鎮。到2008年,「有一雙習慣凝視深邃如夜的眼睛∕與你長年閃耀灼熱深情底目光∕恰好形成太陽系兩極的∕強烈對比」(我來自冥王星),視野一下子開闊起來,巡航的藝術天地已脫離了地球引力。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可能是經她詮釋或是需要詮釋的內容越來越多,「丟失的東西」也相應越來越多,從「殘酷的四月」綻放的〈花季〉,到〈逃生方向〉)和〈如果戰爭不在遠方〉,探討的話題越來越深邃,透著一種與年齡和閱歷不相稱的深刻,似乎永遠在一絲淡淡的憂鬱煩苦中、在紅塵紛擾的現實裡,品位和思考詩歌和真實人生的交流與銜接。如果「……戰爭尚未開打∕哀鴻已傳遍野八方」(如果戰爭不在遠方)傳導的是一種憂患意識,那麼「面對過去,背對未來∕思索著不知還在不在現在」(逃生方向),品讀起來則頗有一種哲人況味。「提一盞路過的燭火行經最沉底∕黑夜,勾勒出光的海市蜃樓」(逃生方向)。讀到此處,仿佛看了半天暗色調的電影,突然一聲巨響,天地一下明亮起來!她留給人思考的,除了憂患,更是憂患之前、之中以及之後所透出的思考和希望。否則憂患幹嘛?
沒有和明霞交流她寫〈花季〉時的創作心態。依我的揣測,倒是看到這首較長的詩,一半像是作曲,一半像是電影創作。
艾略特(T.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有不少中譯本,只一句「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便一下子把人拋入了那種意象疊加、時空交錯的氣場。全詩充滿比喻,暗示,聯想,對應等象徵主義手法。《荒原》也因此成為象徵主義文學中最有代表性的詩作。明霞在〈花季〉,雖以《荒原》的第一句開場並以「四月是艾略特的深沉與殘酷」收尾,但並不見象徵主義的那份神秘和隱晦。不過很明顯地,〈花季〉著墨多的不是去描述(to
describe),而是通過「曾經盛開」,「紛紛凋零」,「茫茫世道的轉角」,「用異鄉人的身份抵達遠方」以及「風中那棵在時間裡靜止的樹」等等意象和層面,試圖喚起(to evoke)讀者去體味文字以外的意境。
〈花季〉雖然是個美麗的詞素,大學的花季「那時我們腳步如風」,但詩中的沉重是顯而易見的。「多年後,當你在淚眼中與我交換記憶∕才驚覺第一個帶頭起義的∕免不了成為烈士。∕於是選擇流離,用異鄉人的身份∕與年輕時早一步出發的那個自己∕重新會合。」
詩中不但故我和新我之間有這種「悲歡離合」,就是「昔日轟動一時的繁華盛世∕都掩蓋在歲月漫漫風沙之下。」隔世、滄桑、惘然以及「等待下一季落紅∕化做春泥」的那份輪回感覺,在審美空間之外又推出一個精神空間。有趣的是,明霞在詩中還嵌入一些黛玉葬花式的小詩節,在大的段落之間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使全詩讀起來像一部交響樂的總譜。而嵌入的小詩節聽起來又像大樂章中的幾個小和絃。〈花季〉是詩集中很獨特的一首創作。
如果明霞的詩是畫,這些畫都是一筆一畫勾勒出來的。個中既有入地紮舊根的養份,更有上天吐新蕊的靈氣。人和人之間、人和自然之間甚至作品和作品之間都是互動的。真實的生命都有養料,生命之間都可以互相依偎、彼此呵護,因為天生合一、萬物互動。這本詩集是王明霞藝術生命體系中,一個新的元素和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