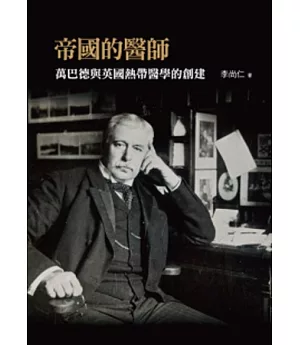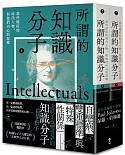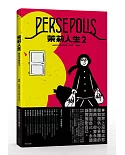導論
為什麼要寫一本關於萬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 )的專書?乍看之下,問題的答案應該很簡單:在西方醫學史上,萬巴德是個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被尊稱為「熱帶醫學之父」( The Father of Tropical Medicine
),顧名思義,自是建立這門專科的關鍵性人物,單憑這點就值得為他作傳。更何況,這位蘇格蘭醫師的生平多采多姿,在家鄉亞伯丁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遠赴重洋到臺灣打狗展開其海外醫學事業。萬巴德是英國人,卻任職於中國海關,成為清政府的僱員。他以熱帶疾病研究的成就在歷史留名,卻未曾在非洲、印度等西方人眼中典型的熱帶地區從事醫學工作,而在廈門取得其最重要的科學發現。萬巴德之後不只成為香港的名醫,其卓越的醫術和聲望更使他和許多重要歷史人物交會:李鴻章是他的病人,孫中山則是他的學生。回到倫敦之後,萬巴德除了繼續投入熱帶疾病的研究與醫學教育工作之外,更協助英國政府擬定熱帶殖民地的醫療政策,並因其成就受封為爵士。如此豐富而精采的醫學生涯,更值得大書特書。不過,就嚴謹的史學觀點而言,所謂某學科「創建者」的說法,經常是對歷史的扭曲。一門學科的建立和一種新知識的發展,必然涉及許多人的作為與努力;其成功也有賴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諸多因素的輻輳。此外,撇開類似「國父」這類帶有神話色彩的簡化稱呼,從嚴謹的科學史與醫學史角度考察萬巴德的醫學生涯,也會發現其醫療事業與科學研究成果,不只和當代醫學與科學相關領域的知識內容與研究方向有著複雜而密切的關係,其對熱帶醫學這門專科日後深遠的影響也需要嚴謹的檢視與評價。
萬巴德的絲蟲病研究和瘧疾研究改變了寄生蟲學的發展方向,為日後昏睡病、瘧疾以及黃熱病等其他重要熱帶疾病的研究奠下重要基礎。早前西方醫學界大多認為象皮病是瘴氣引起的疾病,到十九世紀中才有人猜測此一疾病可能和寄生蟲感染有關。萬巴德的研究不只支持象皮病是絲蟲(filarial)感染所引起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還發現蚊子是班氏絲蟲的中間宿主( intermediate host
),在象皮病傳染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這是醫學界首度發現昆蟲可以是人類寄生蟲疾病傳播過程的一環,為昆蟲病媒( insect-vector )概念的提出跨出重大一步。之後, 萬巴德又提出蚊子可能是瘧原蟲宿主的假說, 並於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八年間和在印度服役的英國軍醫官羅斯( Ronald Ross, 1857-1932
)合作研究,證明蚊子是瘧原蟲的宿主且瘧疾是經由蚊子叮咬而傳播。此一發現解開瘧疾傳播方式之謎,也提出完整的病媒觀念,羅斯更因而榮獲諾貝爾醫學獎。長久以來,瘧疾一直是造成熱帶地區白人生病與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被視為是歐洲殖民、開發熱帶地區的最大阻力。西方醫學向來認為瘧疾是熱帶瘴氣所引起的疾病,瘧原蟲和蚊子病媒的發現帶來一場病理學和流行病學的大變革。然而這場革命不是萬巴德和羅斯所獨力推動,法國與義大利瘧疾學者至少也有同等重大的研究貢獻。但不可否認的是,萬巴德的絲蟲研究所提供的模型以及他提出的蚊子瘧疾理論(Mosquito-Malaria
Theory),對此一研究潮流的最後關鍵階段產生重要引領作用。
除了醫學研究的卓越表現外,萬巴德在醫學政策和醫學教育的領域也展現出高明手腕,其創設的體制與推動的殖民醫學走向,在日後留下深遠影響。他與學弟康德黎( James Cantlie, 1851-1926)在香港創立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是今日香港大學的前身,也是西方醫學教育在華人世界紮根的重要先驅。萬巴德自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二年擔任英國殖民部醫學顧問(Medical Adviser to the Colonial Office),為熱帶殖民地醫療問題提供專家意見,協助打造大英帝國在殖民地的醫學政策和防疫措施。透過和英國政府的關係, 萬巴德在殖民部長錢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鼎力支持下於一八九九年創立倫敦熱帶醫學校( 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該校為前往熱帶殖民地服務的醫療官員和醫療傳教士提供專業課程訓練,替熱帶醫學的專科建制奠定重要基礎,也成為歐美頂尖的熱帶醫學研究機構。萬巴德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熱帶疾病》( Tropical Diseases
)則成為此一新興醫學專科的重要著作,可說在熱帶地區工作的醫師必備的參考書。此書日後多次修訂再版,為紀念萬巴德的成就至今仍以其名出版。
由於萬巴德在現代醫學史上佔有如此重要地位,關於他的研究自然不少。有關他的生平至少已有兩本內容豐富、經常為人引用的傳記。其中,菲利普.萬巴爾(Philip H. Manson-Bahr)與阿爾考克(Alfred
Alcock)合著的《萬巴德爵士的生平與事業》,對其一生經歷敘述最為詳盡,且納入許多寶貴的一手資料,是所有研究萬巴德及英國熱帶醫學史的學者至今仍必須參考的重要著作。然而,這本由親人與同事所寫的傳記,在史觀與分析上不免有所偏頗。該書把重點放在突顯與表揚偉大科學家的功業,卻未能探討其研究的學術脈絡、社會與政治環境,甚至偶爾忽略或貶低其他研究者的貢獻。這些以個別科學家為中心的英雄史觀所遺漏之面向,是一九七○年代開始崛起的醫學社會史的研究焦點。沃博伊斯(Michael
Worboys)在一系列開創性的論文中,探討贊助熱帶醫學研究的不同團體和英國殖民政策,如何形塑英國熱帶醫學在研究發現與預防措施等方面的獨特取向。法利( John Farley)的重要論文則詳述寄生蟲學與細菌學分道揚鑣的歷史,並以相當篇幅分析萬巴德在此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道格拉斯.漢斯(Douglas M.
Haynes)的《帝國醫學》是近年醫學社會史的典型著作,著重從醫學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角度分析萬巴德生平事業。漢斯特別強調英國醫學院畢業生過剩所帶來的專業出路與利益問題,以及帝國競爭和民族主義刺激下英國與其他歐洲強權的科學競爭,如何形塑萬巴德的醫學事業發展。
上述醫學社會史著作的研究視野廣度與分析深度都遠超一般對「偉大醫師」的歷史敘述,讓我們看到熱帶醫學知識的建構與殖民政策、不同贊助者團體的利益考量、醫學社群內部利益競逐乃至個別醫學人物事業策略的複雜關聯。然而,這些研究尚未窮盡萬巴德醫學生涯所涉及的重要議題和豐富的歷史意涵。首先,這些研究焦點多放在大英帝國的中心,不過萬巴德大半的醫學生涯是在中國度過,在廈門的絲蟲病研究帶來他畢生最重要的科學發現。上述著作對萬巴德在中國的醫療與研究活動著墨有限,未能詳細考察他的工作方式與環境,也未能深入探討相關的社會、文化脈絡。就目前殖民醫學史強調對殖民地醫療活動進行細膩探討的研究取向而言,這些研究的焦點幾乎完全集中在萬巴德和歐洲中心的關係,雖有其重要洞見,但不可諱言其視野仍有所侷限。相較於此,萬巴德在中國的醫學活動會是本書的重要主軸。萬巴德所服務中國海關醫療勤務的特色、他對中國衛生環境與疾病問題的觀察與認識、其醫療活動的特色、和中國病人的互動、與醫療勤務同僚以及中國助手的關係等,是本書討論的重點。
本書另一個探討的焦點,則是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概念、研究方法與技術對萬巴德寄生蟲研究的重要性。研究熱帶醫學與自然史的關係有充分的歷史理由:自然史研究在西方淵源久遠,可回溯至古希臘時代。廣義的自然史包含所有對自然事物的描述、分類與歷史探究,其研究涵括今日生物學的研究範圍,也包含地質學、礦物學乃至人類學等學科的主要範疇。在寄生蟲學成為一門專科之前,對寄生蟲的研究原本就是自然史的一部分。再則,自然史研究生物的生長、繁殖、分布,以及生物與生物、生物與環境的關係。寄生蟲學研究在十九世紀興起,上述議題也是寄生蟲研究的主要關切,因此研究方法與概念也就主要來自當代自然史學說。在目前相關文獻中,關於自然史與寄生蟲學的關係,只有法國學者德拉波特(
Francois Del aporte ) 的黃熱病史研究曾提到地理分布(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和適應(adaptation)的概念對萬巴德絲蟲研究的重要性。然而,德拉波特對這點的討論相當簡略,基本上他的焦點是在古巴進行的黃熱病研究,對萬巴德的討論只是要指出古巴醫師芬萊(Carlos Finlay,
1833-1915)對黃熱病傳播方式的理解,受益於萬巴德絲蟲研究以及羅斯的瘧疾研究,萬巴德的研究本身並不是德拉波特關注的焦點。本書則探究寄生蟲學這門學科的歷史淵源,詳細分析當代自然史的重要概念,尤其英國自然史研究對於「完美適應」( perfect adaptation)這個概念的重視與討論、十九世紀興起的超驗自然史(transcendental natural
history)對於物種分布與解剖結構之法則的探討,以及生命史研究所提出世代交替(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s)理論與對生物個體性(organic individuality)的討論,對萬巴德寄生蟲疾病研究的重要性。
在章節安排上,本書第一章介紹萬巴德的早年生活與醫學教育背景。討論蘇格蘭的醫學教育狀況以及亞伯丁大學醫學校的教育改革,兼論十九世紀中英國醫學狀況以及哲學自然史( philosophical natural
history)。本章把萬巴德的醫學學術發展,放在十九世紀英國醫學與生命科學劇烈變革的脈絡中考察。第二章介紹蘇格蘭醫師在本國的出路問題,以及他們在大英帝國海外醫療事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會討論大清帝國海關醫療勤務的起源和組織。此外,此章詳細分析萬巴德在打狗與廈門所從事的醫療活動,包括他對當地疾病的看法,對當地氣候、環境與公共衛生的觀察與討論,同時也探討他對瘧疾、痲瘋、熱帶口瘡(sprue)等「熱帶疾病」的研究。第三章敘述萬巴德在一八七五年前的象皮病研究治療工作,包括他這時期對象皮病病因的理解,以及在外科治療技術上的創新。此章也會回顧當時西方醫學界對此一疾病的瞭解,介紹早期寄生蟲學的發展狀況,並分析萬巴德所閱讀的印度英國殖民醫學文獻對其研究的重要性。第四章則在兩個層次上分析萬巴德在廈門的象皮病研究:一、性別分工概念如何形塑他對中間宿主的理解;二、他研究實作中與中國助手的分工。第五章先介紹萬巴德在廈門對其他寄生蟲疾病的研究,接著討論他在香港從事的醫療與教育工作,最後敘述他返英後在海員醫院任職所從事的醫療工作。第六章探討萬巴德與羅斯合作進行的瘧疾研究工作。此一研究闡明了瘧疾的傳播方式,以及蚊子在瘧原蟲生活史中扮演的角色。萬巴德與羅斯的瘧疾研究是熱帶醫學史上最重大的發現之一。此章介紹他們研究工作遭遇的國際競爭,以及國內外醫學界對其理論與研究成果的質疑,並釐清他們兩人在研究過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第七章敘述萬巴德如何讓熱帶醫學成為一門專科,包括他與英國醫學界及英國政府的關係如何促成倫敦熱帶醫學校的建立,並克服部分醫界對設立此校的反對聲浪。本章兼論萬巴德所寫經典教科書的內容,並述及他和羅斯的決裂。另外,在這一章也會描述萬巴德的晚年生活和對熱帶醫學未來發展的關切。
在順時性的傳記架構下,本書從科學實作( scientific practice)的觀點考察萬巴德的醫學研究。科學史學者謝平(Steven Shapin)和謝佛(Simon Schaffer)在分析波以耳(Robert Boyle)與霍布斯(Thomas
Hobbes)之自然哲學論戰的重要著作《利維坦與空氣泵浦》,將波以耳的科學實作所運用之技術區分為「物質技術」(material technolog y)、「書面技術」(literary technology)和「社會技術」(social
technology)。其中物質技術指的是「氣泵的建造和操作」;書面技術指的是透過文字敘述和圖像,「將氣泵所產生的現象傳達給未直接見證者知道」;社會技術則「整合實驗哲學家在彼此討論及思考知識主張時應該使用的成規」,像紳士言談舉止的禮儀和互信尊重的傳統,以規約實驗研究者的互動方式。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新成員的入會、會員的論述方式及對爭論的處理都必須符合這套規範,從而建立並維持此一科學社群的運作。這三種技術的區分並非絕對,彼此可能重疊,但無損其在分析上帶來的便利。鑒於此一分析性區分對釐清科學實作的內涵非常有用,本書便借助上述「技術」概念與分類,在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與第七章分析萬巴德在不同場域的科學實作。近來,有學者呼籲醫學史研究方向應如同科學史和科學與技術研究(S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般走上「實作的轉向」(the practice turn),本書可說是對此一呼聲的具體回應。
最後,本書也可說是對早期熱帶醫學的物質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近年來,關於科學的物質文化研究指出,科學家其實生活在一個特殊的物質世界,他們直接鑽研的對象常常不是一般所謂的「自然」,而是在特殊條件下,由人工處理過的材料和各式各樣儀器所構成的物質世界。早期許多重要科學史研究重視的是科學的理論與概念,著名科學史學者夸黑(Alexandre
Koyre)就認為,「科學儀器只不過用來闡明邏輯推理所預先達到的結論」;法國哲學家巴舍拉(GastonBachelard) 則宣稱,「儀器其實是物化的定理( r e i f i e d
theorems)」。此外,一九七○年代之前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的主流往往認為科學知識是自然真貌的反映、再現(representation)。從這樣的觀點出發,科學儀器就只是「自然訊息的傳遞者」,本身是個透明的媒介。近年來,科學的物質文化研究則闡明儀器本身用途的範圍與多樣性,探討讓科學儀器能夠發揮作用的相關操作,進而指出儀器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性遠超過上述傳統看法。這些研究顯示,「由於儀器決定了什麼是能做的」,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科學家能夠想到什麼。此外,儀器所提供的可能性常會開啟新的研究,這是因為儀器的用途和發展往往超出原先構想。在這樣的研究旨趣下,近年關於科學的物質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實驗科學(experimental
science)。此種研究偏好也很容易瞭解:實驗室是個特殊規劃下專門配置的空間,充滿包括科學儀器設備在內的各種人造物(artifacts)。因此,實驗室是個有別於日常生活與外界「自然」的特殊環境,這也使得實驗室成為研究科學物質文化的絕佳對象。實驗科學的物質文化研究不只拓廣科學史的研究領域,也是重要的研究轉向,標示著歷史學家對科學活動的性質有了截然不同的認識。
然而,科學研究的物質文化並不僅限於實驗科學以及「實驗室」這個場所。從研究材料入手探討科學研究的物質文化,若運用在實驗科學以外的學科,同樣可帶來深刻洞見。地質學和生態學等田野科學(field
sciences),乃至理論物理和數學等學科也都有其獨特的物質文化;即使是不需要實驗儀器、被認為最抽象、最抽離物質世界的數學,其物質文化也對其研究成果有深遠影響。歷史學者渥瑞克(Andrew
Warwick)的研究指出,十八世紀中期劍橋大學數學考試方式從口試改為筆試,導致該校的數學教學與研究產生巨大轉變。從口試改為筆試使學生的學習重點從背誦公式轉為鍛鍊演算技藝,紙張的普遍使用讓複雜的計算得以進行;黑板則在十九世紀開始成為老師傳授數學解題技巧的重要工具。紙、筆和黑板這些看似簡單的物品,實則構成了數學物理學在十九世紀後半於劍橋大學崛起的物質文化條件。本書除了借助近年科學史的物質文化研究所帶來的新洞見,也將此一研究方向拓展到實驗科學之外的殖民醫學和田野科學,從物質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萬巴德製作玻片、蒐集病人與寄生蟲、和其他研究者交換資訊與標本等科學實作。
過去人類學的「物質文化研究」常狹義地專指研究博物館內收藏的民族學文物。近年來,人類學界對物質文化研究的定義和研究範圍有擴大的趨勢。同樣地,科學史的物質文化研究對此一概念也採取較為寬廣的界定。科學史學者嘉利森(Peter Galison)指出:「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對『物質文化』一詞有各式各樣的使用方式,從研究所謂物的本身(objects taken by
themselves),到把物與它們的用途與象徵意義放在一起分析。」本書對萬巴德醫學研究之分析,可說同時在狹義與廣義的兩種物質文化定義下進行。從狹義的物質文化角度,萬巴德的寄生蟲學研究具有醫學史學者皮克史東( John V. Pickstone)所提出的「博物館式科學」(Museological
Science)特徵。本書第三章、七章與結論將對這點作進一步闡述,指出蒐集、分類與比較、分析等博物館式研究活動在萬巴德熱帶醫學研究中所佔的重要位置。就廣義的物質文化定義層次而言,第六章與第七章則探討研究材料取得與操作的技術,以及病人、標本與資訊的交換與象徵性,在萬巴德醫學事業乃至當時醫學界的運作與政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就形式而言,本書採取的傳記書寫形式似乎保守而不合時宜;就探討焦點來說,本書側重於萬巴德的科學研究內容,似乎又回到老式的科學內史傳統。然而,筆者希望也相信讀者在讀完此書之後,上述初步印象會隨之消散。相較過去的醫學社會史研究,筆者在這本書中以更大的篇幅和心力探究萬巴德科學研究的概念內涵與實地操作,然這並不意味本書忽略過去三十年來醫學社會史與殖民醫學史對權力、政治與利益等因素在知識生產過程之重要性的探討與強調。相反地,這本書要進一步推展這個研究取向。從現代初期(early
modern
period)以來,歐洲強權的自然學者在海外的研究活動,往往是帝國資訊蒐集活動的重要一部分;探索熱帶醫學的自然史淵源與研究取向,可說是深入探討歐洲帝國擴張與現代科學知識生產之間關係的絕佳入手處。萬巴德的醫學功業固然值得大書特書,但他的事業生涯更是理解英國殖民醫學史的絕佳入手處。寫這本書不只要補足過去學者忽略之處,更大的企圖在於,透過細膩考察萬巴德的醫學工作,對十九世紀英國醫學與生命科學的關係、對大英帝國擴張與醫學知識建構、對現代西方醫學進入中國的過程,提出新的分析與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