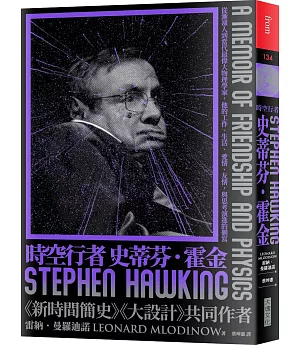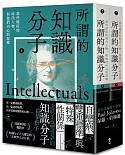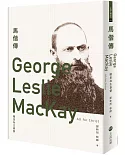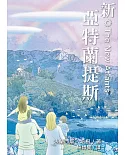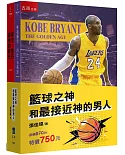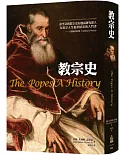前言
在劍橋市中心,擁有五百年悠久歷史的大聖馬利亞堂(Great St. Mary’s church)裡,我與霍金做了最後的道別。二○一八年的三月,我坐在走道旁,就在他經過我的身旁,近在咫尺的那最後一瞬間,彷彿有種和他再次重逢的感覺,儘管有棺木把他和我們這些哀悼的人隔開,然而,也是這個棺木,在七十六年後的今天,終於可以保護他免於人世間的種種危難與挑戰。
霍金相信,死亡是一切的終點。身為人類的我們,創造建築,發明理論以及繁衍後代。雖然時間的長河會載著它們繼續前進,但我們終會有跟不上而被遺留下來的一天。這也曾是我的信仰,然而,在棺木通過我身旁的那一瞬間,我似乎感覺到,在這個木頭盒子裡,他仍然跟我們在一起。這是一種恐怖而奇異的感覺。我的理性告訴我,霍金所存在的短暫瞬間已經過去了,就像我自己的短暫存在,也會在幾年之後就結束。物理學教會我的,終有一天,不僅僅是所有我們珍視的東西,更包括我們能意識與感知到的所有事物,都將消失殆盡。我知道,所有的時間,包括我們的地球、我們的太陽,甚至連我們的銀河系,都只是借來的,當時間用完時,所有的一切盡歸塵土。然而,我還是默默地向霍金獻上,我對永恆未來的愛與美好祝願。
我低頭看著在霍金生平傳略封面上那張知足的臉。我回想起他的堅強,也想起他在讚賞人時的燦爛笑容,以及在反對你時的可怕鬼臉。我也回想起那段我們沉浸在同一件熱中事物的愉快時光。當我們在討論一些美好的想法時,或是我從他那裡學到什麼新東西的寶貴時刻—當然還有我試著說服他某個想法,而他卻紋風不動的挫折時刻,也都一一浮上心頭。
若要論及在物理學世界裡攪動風雲的能力,以及書寫表達物理的能力,霍金的成就都是世界知名的,特別是這些都是透過他那副殘破身軀做到的。然而,對一個癱瘓而無法自由行動,特別還是一個無法言語的人來說,想要維持長時期的友誼,發展出深厚的關係,以及找到愛情,都是極具挑戰性的。霍金知道,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是愛,而不僅僅是他的物理,在滋養著他。也是因為這些,讓他贏得了超乎預期的成就。
某些悼詞隱喻地諷刺了生前不信上帝的霍金,死後卻在教堂裡舉行葬禮。但對我而言,這完全沒有矛盾。儘管在智性上,霍金堅信科學法則統領了所有的自然現象,但他本身卻是一個深具靈性的人。他相信人類的精神。他認為,在情感與道德的本質上,所有的人類都具有一些異於其他動物的特質,這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理由。他認為靈魂不是一種超自然的存在,而是大腦的產物,這樣的信仰絲毫無損於他的靈性。為什麼這麼說呢?對霍金而言,這樣一個動彈不得又無法言語的人來說,他的精神不就是他所擁有的全部嗎?
霍金總是把「固執是我最好的美德」掛在嘴邊,這點我無法反駁。固執讓他可以去追求一些眾人只會翻白眼,難以置信,而且似乎是看不到結果的想法。也是固執,讓他禁錮在這個寸步難移身軀中的靈魂,可以盡情的舞蹈。霍金的生命,完全違背了當初醫生的預測。然而,在二○一八年的三月十四日,霍金這顆恆星,終於還是燃燒殆盡了。現在,我們所有的人,包括家人、朋友、護理人員以及同事,大家齊聚一堂,與他道別。儘管他較我年長十三歲,本應於數十年前就過世,即使在他成年後,疾病纏身,並數次經歷可能致命的肺部感染。但在我心裡總是覺得,他應該會活得比我久。
與霍金合作的開始
我與霍金認識,是從他在二○○三年聯絡我之後開始的。他問我是否願意和他一起寫作。他讀過我的兩本書:關於曲度空間的《歐幾里得之窗》(Euclid’s Window),以及《費曼的彩虹》(Feynman’s
Rainbow),關於我與一位傳奇物理學家之間的故事。他說他喜歡我的寫作風格,也喜歡我是一位可以了解他的研究工作的物理學家。我感到受寵若驚。在隨後的幾年裡,我們一起寫了兩本書,也成了好朋友。
我們合寫的第一本書是《新時間簡史》(A Briefer History of Time)。這本書不是原創作品,而是改寫自霍金的著名作品《時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他的原意是希望把《時間簡史》變得更親切易懂些。然而,加州理工學院的理論物理學家索恩(Kip
Thorne),也是霍金的一位好朋友,他曾對我說:你知道的物理愈多,你對《時間簡史》的了解就愈少。霍金的說法稍稍有點不同:「大家都買了這本書,但真的有去讀的人並不多。」
《新時間簡史》於二○○五年出版。我當時正在加州理工學院服務。定居在英格蘭的霍金,每年都會來加州理工學院研究訪問,每次停留二到四週。他的到訪,以及我們之間的電子郵件通訊,已經足夠讓我們寫完《新時間簡史》。至於他的其他著作,例如《胡桃裡的宇宙》(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多是基於他在一九七○與八○年代的研究工作。因此,在《新時間簡史》出版之後,我們決定開始《大設計》(The Grand Design)的寫作計畫,這是一本關於他最新研究內容的書,介紹他從未在科普領域裡發表過的新理論,而且我們也計畫要涵蓋一些相當複雜的議題。例如平行宇宙(parallel
universe),宇宙可以從一種空無(nothingness)狀態中誕生的概念,以及自然法則似乎是經過微調而使生命得以出現的事實等等。顯然,這是另一個層級的遊戲了!我們必須要有更多面對面的時間才可以。因此,我開始從加州「通勤」到劍橋與霍金一起工作。我一直通勤到二○一○年,直到我們終於把書寫完。
黑洞與初期宇宙的探索
霍金的生涯大部分都花在接替愛因斯坦遺留下來的工作。一九○五年時,愛因斯坦發明我們如今稱作「狹義相對論」的理論。當年,他只有二十五歲,物理研究只是他在專利分析員工作之外的興趣而已。相對論揭露出許多自然界裡詭異的祕密:時間與空間的測量是相對的,取決於觀察者;物質是能量的一種形式;沒有任何物體的速度可以超過光速。然而,這裡有個問題:狹義相對論並沒有直接討論到重力,它對速度的限制,明顯地違反牛頓的理論。牛頓認為重力的傳播是瞬間的,也就是說,重力傳播的速度是無限大的。
愛因斯坦對於這個矛盾感到很困擾。相對論需要修改嗎?還是應該放棄牛頓的重力理論?事實證明,這兩者都是必需的。愛因斯坦在這問題上花了十年的時間,他辭去專利局的工作,輾轉在伯恩(Bern,義大利)、蘇黎世、布拉格與柏林等地的學術機構任職。終於,在一九一五年,愛因斯坦完成了他的新理論:廣義相對論。他大規模地改寫了狹義相對論,明確地考慮了重力的效應,延伸了狹義相對論的適用範圍。
廣義相對論異於牛頓理論的眾多內容之一是糾正了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即重力是瞬間傳遞的:根據廣義相對論,引力與光波類似,都是以波動的方式在空間中傳播,並且是以光速行進,因此遵守相對論的速度限制。諷刺的是,儘管得出一個令人滿意、而且能完整描述出重力波的傳播方式,是愛因斯坦最初在發展廣義相對論時的一個重要驅力,重力波卻是廣義相對論中最後一個獲得實驗證實的理論。由於在驗證這個理論上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索恩獲頒二○一七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牛頓以一個想像的力來解釋行星在軌道上運行,以及物體掉落的原因,他稱之為重力。物體之間存在著重力,彼此互相吸引,使得運動的軌跡偏離原本的「自然運動」;牛頓宣稱直線是物體運動的自然狀態。愛因斯坦向我們展示,這只是一個近似的圖像。如果我們以不同的方式來描述重力的現象,還有一個更為深層的真理存在。
根據愛因斯坦所言,物質與能量之間的相互吸引並不是憑藉力的作用。相反地,它們會引起空間彎曲,而這個空間的曲率會反過來決定物質該如何移動,以及能量該如何傳播。物質作用在時空曲面上,同時,時空曲面也作用在物質上。正是這個反饋迴圈,讓廣義相對論的數學變得相當困難。為了要發展這套理論,愛因斯坦必須學習並掌握一套當時還相當晦澀、專門討論彎曲空間的數學領域,稱為非歐幾里得幾何學(non-Euclidean
geometry)。在艱苦奮鬥的十年歲月裡,愛因斯坦必須一再地嘗試錯誤,不斷地猜測理論可能出現的形式,計算每一個可能理論所導出來的結果,並批判它自己的想法,藉此打造完美的廣義相對論。
在一般情況下,牛頓的理論提供一個很好的近似解,這也是為什麼數百年來,沒有人注意到它的缺點。但是在高速度,或是物質與能量在高度集中的情況下,也就是在重力極大的情況下,牛頓的理論便失效了。
今日,狹義相對論已廣泛應用於物理的許多領域。然而,理解廣義相對論所需要的情境,仍然相當有限。其中兩個最重要的現象就是黑洞與宇宙的起源。數十年來,這兩個現象對於實驗來說,似乎顯得遙不可及。一般認為,早期的宇宙因距離我們過於久遠,很難研究出什麼有意義的成果;至於黑洞,則是由愛因斯坦自己把它否定掉,認為黑洞只是一個數學上的奇異點,而非自然界中真實存在的物理現象。結果,在愛因斯坦一九一五年發表廣義相對論之後的半個世紀,這些想法大都被忽視,而廣義相對論也就像科學界裡一攤安靜的死水,死氣沉沉。
其他物理學家的想法,並沒有讓霍金卻步。事實上,他的第一本書,就是與人合著的大部頭巨著《時空的大尺度結構》(The Large Scale Structure of
Space-Time),在書中,他花了很多篇幅討論彎曲的空間,以及描述這個空間所需的數學方法。我在大學時就讀過這本書的一大部分,也覺得很有趣,這真是一本引人入勝的書,讓人忍不住想翻到下一頁,不過,前提是你得翻得很慢──理解消化一頁的內容可能得花上你一個小時,甚至是更長的時間。
黑洞與初期宇宙是讓霍金著迷的兩個主題,這兩個系統的物理學也成了他主要的研究領域。他早期的工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為喚醒沉睡已久的廣義相對論,指引了方向。再者,相對論與量子論之間一直有著難以相容的隔閡,霍金稍後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發現,催生了一門新的領域,我們現在稱為量子重力論。
霍金一生致力於探索這些觀念與現象。他向世人展示它們的相關性,他從未停止從中再發掘出新的發現。當他決定要寫《大設計》時,他已經在這些問題上,思考並努力奮鬥了四十年的時間。對於他剛踏入研究生涯時的那些最為棘手的問題,例如宇宙是怎麼開始的?為什麼只有一個宇宙存在?以及為什麼物理定律會是它們現在的這個模樣?霍金覺得他終於弄懂了這些難題,而我們一起撰寫《大設計》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解釋他的這些答案。
我從霍金身上學到的東西
當你與某人一起合作一個你很感興趣的專案時,你們的心智是相連的。如果幸運的話,會連心意都是相通的。在合作的過程中,我們成了朋友。從單純智性上的夥伴關係,逐漸發展成一個在人性底層相通的連結。這份連結讓我感到訝異,但其實這很自然,因為霍金不僅在尋找宇宙的奧祕,他也在尋找可以跟他分享這些奧祕的人。
童年時期,霍金曾遭到其他小男孩的霸凌。曾有位高中同學羞辱他:「他個子小,看起來像隻猴子一樣。」成年之後,他被囚禁在一個失去功能的軀殼裡。然而,他以幽默來對抗霸凌,以堅強的內心來對抗癱瘓的身體。每一位熟識霍金的人,都會受他堅強的個人特質或是科學觀所影響。在接下來的篇幅裡,我分享我與霍金一起合作的工作經驗,以及結識他這麼一位朋友的過程。我希望讓大家理解,是什麼讓霍金成為一位特別的物理學家,以及特別的人。什麼是他真實的模樣?他如何面對他的疾病?而他的殘疾又如何影響他的思考?他對於生活與科學的態度有何不同?有哪些東西啟發了他?他這些原創的想法又是從何而來?什麼是他主要的科學成就?這些成就又與整體的物理知識有何關聯?理論物理學家真正的工作內容是什麼?他們都是如何工作?以及,他們為什麼做這些工作?所有這些問題,甚至包括我原本就有的一些想法,在與霍金共事的這段時間,我都有了新的觀點。在我回憶我們相處的時光,細數他生命中的一些亮點時,我的目標,是希望與大家分享我所學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