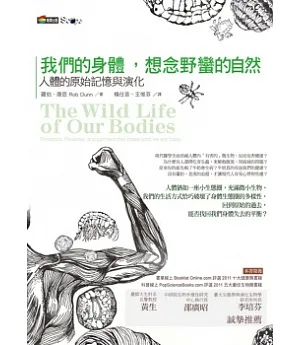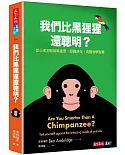推薦序
@人體就像一座野生動物園@
人類長年企圖根除體內每一隻寄生蟲,改變人類與微生物的共存關係;也長年企圖破壞熱帶原始雨林,改變人類與大自然的共存關係。循著這樣的趨勢演進,越接近文明的人類就越遠離了自然,這該怎麼辦? 我們的身體要和大自然痛癢相關呀!
在生命世界裡,生物之間存有寄生、共生等關係,寄生蟲對人畜有害無益的話我們從小就聽多了,要是您或我知道了您或我的腸道裡總趴著那麼幾條寄生蟲,那一肚子不舒服的感覺是怎麼樣也說不清楚的。因此,一聽說科學家們為了人類的健康、牲畜的健康(也是人類的健康) ,正要建造一個沒有寄生蟲的文明世界,那可真太美妙了!至少,我們在孩童時期都可能這樣期盼過。
今天,我們都知道那樣想太天真,但卻找不出甚麼比較有深度的說詞告訴別人「殺死細菌!殺光寄生蟲!」之後,人類必定將更不健康。我們頂多告訴人們說「在文明世界裡,腸道的寄生蟲已清光了,可是,免疫系統的發展過程需要寄生蟲,這又該怎麼辦?」我們要是總把寄生蟲當成是敵國外患,當思「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之警句。
我們正面臨著物種遺失,生物多樣性急速減損的問題,保育和永續已是這一代文明人的基本素養了。可是當你問到在生物多樣性保育這張大傘下,細菌、真菌,原生生物和寄生蟲的「保育」觀念建構在那一個角落裡時,卻沒幾個人答得上來。
我們需要一本為寄生蟲平反的書,這本書應該是一本故事書,講一段白蟻腸道的冷暖存亡;一段紅火蟻與DDT;講一段詹姆斯的「無菌生態圈」和12歲男孩的「無菌泡泡」,再加一段恐怖的潛水艇裡割闌尾;講原牛與歐洲人的共生演化;拿破侖、蝨子、體毛、戰爭與和平。此外,還要講人類免疫系統為您而戰的戰史;而且一旦戰局逆轉,你的免疫功能失調,你要如何請救兵,你會不會前進非洲,到喀麥隆這個「鉤蟲聖地」去,打著赤腳在處處有新鮮排遺的街上散步,尋回演化途中遺失的寄生蟲?期待「鉤蟲救兵」穿過你那層細嫩的「文明肌膚」,順利進入體內救你。這些都是很另類的想法,《我們的身體,想念野蠻的自然:人體的原始記憶與演化》這本書裡的每一段故事都很另類。
人體是不是必須像一座野生動物園,收容大自然的、演化路程上失落的一小部分,讓它們進入體內。這些體型雖小卻舉足輕重的微生物細胞對人體而言,扮演什麼角色?後果又是什麼?人體該不該扮演「域外保育」的角色,把這些瀕絕和極絕的,細菌、真菌,原生生物和寄生蟲引入體內照顧,盡一份保育責任?答案竟是確有必要。我的天吶!不過您也不必太緊張,這些都是在人類本身的福祉和永續生存的前題下設計好的。
@@黃 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名譽教授@@
譯者序
@我們的身體,想念野蠻的自然
你是否曾經在某個悲傷痛苦、幾近絕望或不知所措的時刻,渴望過徹底切斷與生命軌跡連結的大腦記憶,如同電影《王牌冤家》(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裡男女主角的嘗試一樣?事實上,儘管有一天腦神經醫師真的有能力辦到電影情節中的記憶操作,我們依舊無法完全擺脫歷史。
因為歷史是悠久反覆、層層堆疊而成的,因為歷史已深深植入我們的基因中。回顧這段宏偉的歷史,我們熟悉的名詞是「演化」;更精準地說,是「共生演化」。
我相信曾翻閱過數本談論演化書籍的讀者,看到「共生演化」一詞,腦中便浮現出天擇、蓋婭、全球氣候變遷、生態環境復育、永續生存等關鍵字。也或許,諸如此類的關鍵字對我們而言,畢竟有些「抽象」而「遙遠」。這也的確忠實地反映出近代生物醫學科學發展中,一個普遍的思維框架。直到有一天,我們自己的身體開始出現傳統西方醫學束手無策的各類症狀時,人類才終於對共生演化產生「具體」而「切身」的感受。
本書正是以每一個人感受得最具體而切身的這副身軀,從內而外、從近而遠,深入探討共生演化的意義。
作者羅布‧鄧恩(Rob Dunn)由人體消化道—克隆氏症及闌尾炎—的故事說起。而上述的健康議題與類風溼性關節炎、紅斑性狼瘡、乃至於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壓、憂鬱症、恐懼症等新型態的「瘟疫」皆可謂一體多面。除此之外,這些新型態的瘟疫使得「只要掏出錢,便能輕易獲得解藥」的美夢幻滅;恰恰相反地,此類疾病偏好造訪的族群,往往都居住在公共衛生系統相對健全、坐擁多數醫療資源的先進國家。
因此,長年投身於對抗相關疾病的基礎醫學家或臨床醫學家,一方面廣泛使用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抗生素,以及望著四周定期消毒滅菌的「文明空間」與其中充斥叮嚀民眾勤勞洗手的標語時,另一方面卻隱約感到哪裡不大對勁。而在苦尋不得治本的解藥後,他們決定從解謎著手。
其中一位解謎的科學家是喬.溫史達克(Joel
Weinstock),他因受邀參與編輯審核一本有關寄生蟲與宿主的著作,而意外地對腸道發炎醫藥學的「本行」有了一個靈光乍現的新點子。主流的病原理論認為人類罹病是因為新品種的病原體入侵身體所致,但溫史達克從截然對立的角度思考:「疾病或許反而是起因於現代人將其他生物消滅得過於徹底所致。」就腸道而言,被消滅過度徹底的是寄生蟲與細菌;就人體內外的其他部分而言,被消滅過度徹底的物種更是不計其數、「多采多姿」。
隨著愈來愈多科學家接受類似觀點,並以堪稱「撼動主流醫學基礎」的革命性視野為出發點,解謎各種好發於已開發國家的「文明病」後,當初溫史達克靈光乍現的點子逐步受到證實,答案也更為清晰地拼湊成型。
人類汲汲趕盡殺絕自身判定為有害的物種,還引以為豪的「成就」,竟同時成就了當初始料未及的健康問題。
我在翻譯本書時,適逢李惠仁導演之《不能戳的秘密》一片引發台灣社會熱烈討論;在完整版中,片頭刻意擷取的授粉採蜜、清道夫等生態角色以及片尾引言於我是相當動人的:「有些生物密切共生,不能分開。強行分開,他們就無法生存。或許可以這樣說,共生是推動演化的力量。」
「共生是推動演化的力量」,與本書引用的多項學術論文之內容不謀而合,亦是不同領域的醫學研究者共同的修正方向。事實上,迫切的真相是:我們在慣以人類為中心的狂妄立場環顧大地,進而衍生出「殺光所有『有害』物種」(Kill Them All)的行動之後,才驚覺到「原來我們正在集體自殺!」(Somehow, we are killing ourselves
too);眼前,這已是不得不前進的修正方向。
身為提倡消滅飲用乳及食物細菌(巴氏殺菌法)之微生物學研究先驅巴斯德(Louis Pasteur)本人也相信微生物與人體之間是相依相存的;他認為缺少了共享演化歷史的微生物,人類將無法存活。換言之,不是吞下一包保健益生菌我們從此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因為微生物是人類「絕對型互利共生」(obligate
mutualist)的夥伴,其中「絕對型」的涵義為不可或缺的,而「互利」則代表彼此之間的雙贏關係。
平心而論,這些革命性的醫學理論在生態學家眼中只能算是後見之明。生態學家們早知演化是無法阻止的力量,而今日我們的樣貌,是人類祖先的共生夥伴一步步雕刻而成的。如「叉角羚通則」中所提出之論點,每一個物種皆擁有「回應」共處物種(無論是寄生蟲、微生物或天敵)的基因與遺傳特徵,即使具有互動關係的物種已經絕跡,這些特徵仍然不會消失,卻極可能會成為一種過時的存在或負擔。叉角羚背負的演化包袱是逃離絕種天敵(美洲獵豹)追逐的奔跑速度,我們人類呢?是否是失控的免疫系統、錯亂的大腦神經迴路或發狂的腎上腺素?彷彿處在我們親手為自己量身打造,現今這個生物多樣性驟降、原始棲地殘破的生活環境裡,依舊藏有一度共生物種的鬼魂般。
攜帶著這套歷經漫長演化適應、形塑而成的基因與遺傳特徵,人類終究拋棄好不容易找到的最佳生態位置,選擇徹底切斷過去,進入接受種種「淨化儀式」洗禮的「美麗新世界」—一個缺乏與原始共生物種相處經驗的美麗新世界,一個只剩鬼魂的美麗新世界。
在「美麗新世界」中,人類失衡的身體與心理,簡直是失衡蓋亞的鮮明縮影。失衡之初或許肇始於祖先面臨重大天災或飢荒時所採取的終極求生手段—當年沒有回頭路的唯一選項;但在今日,加速失衡的藉口顯然無法成立。如果昔日人類犯下的是無知的罪過;現在再不行動,即是有知的罪過,殃及子子孫孫的罪過。
基礎醫學家跳脫框架的修正方向,提供我們一個可彌補罪過的機會與可期待的未來;他們牽起生態學家的手,懷著謙卑的態度站在蓋婭之前,重新省思,而我們每一位地球公民亦應如此。如蓋婭假說創始人之一琳.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定義的:「所謂的「蓋亞」,不過是從地球之外看到,共生所交織成的生命之網罷了。」同樣地,從人體之外看到的生命之網是每一個人的「小蓋婭」,唯有和諧對待,才有機會化趨於混亂的歷史包袱為新的演化力量。借用英國詩人約翰.克雷(John
Clare)的一句話來形容:「沒有生命,也沒有歡樂…一切珍貴,盡如沈舟。」如今這艘沉舟超出以往認知、環保專家口中的「待復育棲地」,這艘沉舟已然包含你我的身體。
最後,我想以一句土耳其諺語作為翻譯本書的心得總結:「世上沒有不帶刺的玫瑰,也沒有少了對手的愛情。」 (No rose without a thorn, or a love without a rival)
當我們忙著置對手於死地、深怕「縱放任何一個敵人」之際,卻忘了刺是玫瑰身上的一部分。那些「錯殺千萬的」或許從來不是敵人。甚至不僅是朋友,而是我們的一部分;就像我們是他們的一部分般。
這綿延的共生歷史,終將不滅,每每騷動著現代人的身與心。
「少了你們,我們根本活不下去。」(And without you, we cannot survive)
@@楊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