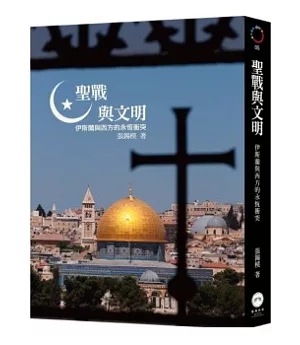導讀
張國城 台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
張錫模教授的《聖戰與文明》一書,堪稱對伊斯蘭世界政治史和國際關係史的經典著作。充分詳盡的史料與邏輯精潔的敘述,讓讀者能夠一窺伊斯蘭世界和西方勢力衝突和消長的經過與原因。要了解本書的架構及作者所要表達的真意,可從以下幾大脈絡來進行:
一、伊斯蘭教的起源、伊斯蘭法與伊斯蘭世界的出現,以及穆斯林的世界觀。
許多人都對中東問題的產生感到迷惑,這相當程度是緣於對伊斯蘭世界的誤解。本書第二章和第三章詳細敘述了伊斯蘭教的興起,伊斯蘭世界的地緣政治環境及伊斯蘭世界的形成過程。從所處的地理環境和地緣政治,可以理解伊斯蘭世界的形成特質--不是先天排他的宗教。作者在導論中就提到伊斯蘭的歷史大都對異教徒採寬容態度,向少出現西歐中世基督教世界那樣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
穆罕默德在西元601年在麥加創立伊斯蘭教之後,「伊斯蘭法」的觀念漸次形成。伊斯蘭法將世界分為「伊斯蘭之家」(Dar al-Islam,意指伊斯蘭世界)和「戰爭之家」(Dar al-Harb,非伊斯蘭世界),「聖戰」的意義就是促使非伊斯蘭世界整合到伊斯蘭世界,重點是傳播信仰。穆斯林世界認為若一個穆斯林依據伊斯蘭法生活的權利遭到否決,「聖戰」就成為責任。
所以「聖戰」不是外界想的那樣,只是穆斯林不惜犧牲自己生命去攻擊非伊斯蘭世界異教徒的行為,本書充分解說了伊斯蘭教的起源與穆斯林的世界觀,打破了伊斯蘭世界封閉排外的傳統觀念,值得讀者仔細挖掘深思。
以伊朗來說,長期在媒體中呈現的形象就是一個反美反西方的國家。事實上伊朗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在文明的發展上相當早,也並不是一開始就是穆斯林國家。西元637年穆斯林軍在卡迪西亞戰役打敗波斯薩珊王朝的軍隊,攻佔其首都泰西封,開始了伊斯蘭對波斯的征服,接著又被突厥人與蒙古人又相繼入侵,16初的薩非王朝才開始以回教什葉派為國教。18世紀初贊德王朝(Zand
Dynasty)、卡加王朝(Qajar
Dynasty)相繼崛起,但因長期戰亂,國勢衰竭,長期被英國、俄國甚至阿富汗侵略,1722年伊朗的薩法維帝國就被阿富汗進攻之後滅亡。19世紀又歷經兩次與俄國的戰爭和一次與英國的戰爭,因此長期存在反抗外來勢力的觀念。有趣的是,今天以色列和伊朗勢如水火,事實上在猶太歷史裡,薩珊王朝是猶太人信仰擴張的重要時代。猶太教重要的宗教文獻《塔木德》是在薩珊王朝時期完成的,多所以猶太人為定位的學術機構在伊朗的蘇拉、蓬貝迪塔(Pumbedita)等地建立起來,這些學術機構在多個世紀以來在猶太學術方面是最有影響力的。
今天要理解伊朗問題,不能忽略這一國家長期身處伊斯蘭世界下的所經歷的歷史經驗。伊朗如此,阿富汗與其他伊斯蘭國家亦然。《聖戰與文明》一書恰可提供非常豐富的歷史敘述和思考基礎。
二、近代國家體系論理、體制和伊斯蘭世界的互動和衝突
就作者的見解,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若以杭廷頓的「文明衝突」來解釋,顯得粗糙。作者認為的「文明」,事實上是指18世紀下半葉以降,源自西歐的國家體系論理及體制。這和「聖戰」所追求的政治秩序(伊斯蘭共同體的建立和伊斯蘭法的統治)在「權力」、「和平」、「秩序」及「正義」等概念,存在本質的差異;19世紀歐洲國家用以合理化對外擴張的「文明開化」觀在伊斯蘭世界引起的反抗,形成了衝突的原動力。今日所謂的中東問題,相當程度起源於這種歐洲國家體系中強國對伊斯蘭世界的侵略,及「主權國家」概念和伊斯蘭世界觀的衝突。
在第四章「西歐國家體系的衝擊」中,作者詳細介紹了西歐「國家」體系成立的過程。並且說明了當代國家行為與國際關係的政治哲學基礎。本書雖是國際關係方面的著作,但這一段的解釋即使拿來和專業政治思想史與政治哲學著作相比,也絲毫不遜色。近代,西方發展出的國際體系係建立在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原則之上,以權力平衡政策作為體系成員彼此互動的最核心考慮及外交活動的中心,在這一體系中,沒有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的一個強大中心,至少就法律形式上是如此,這也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英俄之後用以干預進而分解伊斯蘭世界存在的帝國(蒙兀兒、土耳其)的基本原因。這種主權國家為國際體系基本單位的觀念,導致英法在一次大戰後在伊斯蘭世界創設主權國家,並視本身利益需要對這些伊斯蘭世界的主權國家扶植、打擊或是削弱。時至今日,反倒是伊斯蘭國家屢屢堅持本身的「主權國家」地位,先是在二戰後到1970年代作為擺脫西方控制,追求伊斯蘭國家政治獨立自主的動力,如今也以此抗拒「普世價值」的滲入,實在是非常有趣的發展。
三、石油、「普世價值」「阿拉伯之春」與伊斯蘭世界的未來
伊斯蘭世界是石油的主要產地,也是石油改變了近代伊斯蘭世界的面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戰時科技帶來的「石油經濟」發展讓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互動增加了資源掌控權的合作與爭執。伊斯蘭世界發現主權國家身分有利於和西方世界爭取和控制於本身領土內的石油。因此強調對主權的控制,這時候西方國家對伊斯蘭世界存在敵友兩種角色;敵的部分來自於過往歷史的侵略,友的部分在於對石油的需要所傾注的財富。
到了1990年代,超乎國境的「普世價值」逐漸成為西方國家和伊斯蘭國家新的互動動力。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被聯軍消滅,理由是維護主權國家疆域完整獨立的「普世價值」;2011年茉莉花革命的出現,又一定程度呼應了另外的「普世價值」--民主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西方的國家論理和國際關係體系歷史上每每衝撞伊斯蘭世界,但近10年來,伊斯蘭國家並未完全以「反對西方」為思考原則去重建中東的政治架構。在作為一強的伊拉克被削弱之後,出現的是類似西方自由主義者所倡議的集體安全組織。在2000年12月31日在巴林首都舉行的第21屆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理事會首腦會議上,作為伊斯蘭國家的成員國領導人就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強調海合會成員國決心共同抵禦任何威脅。該條約包括成立聯合防務理事會,隨後衍生出「最高軍事委員會」,制定特殊的組織結構和行動機制。2009年12月在科威特召開的第30屆首腦會議上,海合會領導人又一致通過了海合會防禦戰略,確立了海合會國家的戰略思想,協調和加強防衛一體化,發展維護主權、獨立與利益的防禦能力,抵禦侵略,聯手應對挑戰、危機和災難。2010年12月6日,第31屆海合會首腦會議再次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首都阿布扎比舉行。這次的主要議題擴大到包括伊朗問題,制定反恐戰略,打擊滋生的基地組織,在周邊國家邊界建立控制和監視機制等。
顯然,當前伊斯蘭世界認定的威脅不是西方國家。從軍備採購到提供基地,合作日漸明顯,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上一定程度也被認為符合伊斯蘭世界(至少部分)的利益。事實上對伊斯蘭國家而言,他們的核心關切之一是如何與美國這樣的唯一超級強權打交道。面對區域外的強權時,每一個國家都有兩種很自然的傾向。第一種傾向是「權力平衡」,各自連結起來打造有力的同盟體來牽制區域外強權(在這裡是美國)的力量,並據此控制該強權的行為。第二種傾向是「西瓜靠大邊」,即和強權維持良好乃至繁密的關係,藉以促進本國的利益。這種雙元性的反應傾向,連同強權的回應,構成推進當代國際政治體系變遷的基本動力。
若依「聖戰」與「文明」長期衝突的觀念,美國單一超級強權的壓力,會促使伊斯蘭國家很自然地想要尋求結盟來反制美國。但是,由於權力的差距是如此地巨大,權力的不對稱是如此地明顯,因而同盟體的締造顯得極為困難,至少蘇聯解體迄今以來是如此。畢竟,要締造一個力量足以和美國相捋的同盟體,是一項非常艱困的工程。在這個過程中,又有兩種力量會構成嚴重阻力。其一是美國的介入,採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來破壞反美同盟體的形成;其二是伊斯蘭各國的自利行為,即利用締結反美同盟體的威脅來向美國爭取更多的利益,反美為假,對美求婚為真。然而,西方和伊斯蘭體系的不對稱現實並未獲得消解或緩和,不對稱仍繼續存在,甚至因此而加深。
從2010年開始出現的「阿拉伯之春」,出乎很多人意料。事實上,阿拉伯許多思想家、文學家幾年前就已作出預言。這其實是源於穆斯林社會的反思傳統;他們除了指出存在於阿拉伯國家中政治、經濟、社會的積弊外,更通過分析阿拉伯世界深重的文化與社會危機,判定阿拉伯大地正在醞釀巨大的變革或革命。2011年美國《外交政策》推選為全球百位思想家之首的埃及小說家阿斯旺尼,在2008年接受美國《紐約時報》採訪時談論起埃及的處境,就表示「專制統治者誅殺了埃及的精神,遮蔽了埃及的光芒。」「…人民一旦憤怒,一切都會改變,革命就是這樣自發地、無人策劃地爆發的」。
很多阿拉伯知識份子認為,僅從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的角度分析阿拉伯民族面臨的危機依然不夠,有必要從文化與思想角度深刻審視阿拉伯危機的根源。這一點,北京大學的阿拉伯專家薛慶國教授說的最為透徹。他認為阿拉伯社會的問題在於:「第一,具有膜拜權威、壓抑個性的專制主義傾向,對權威的順從與膜拜,與對神靈絕對權威的信仰糾結在一起,使專制主義在阿拉伯社會大行其道。
第二,神本主義、宗教蒙昧主義盛行,不少人對宗教的理解本質上依然沒有走出中世紀之囿。第三,對西方缺乏理性認識,認為西方世界是腐敗墮落的,因而排斥西方現代先進價值,思想趨於保守與封閉。第四,宗派主義思想根深蒂固。國家、社會的概念並未深入人心,族群利益被置於國家與民族利益之上。第五,男尊女卑、歧視女性的痼疾難以消除。」
事實上,從《聖戰與文明》一書中所敘述的伊斯蘭世界歷史,可以發現伊斯蘭世界原本不是如此。筆者認為,由於伊斯蘭世界一再被作為西方文明圍堵俄羅斯和蘇聯的基地,蘇聯為了制衡西方進而爭奪和西方影響力,也要拉攏伊斯蘭世界作為緩衝區甚至結盟,對外在強權而言,一個穩固的獨裁者最適合需求,因為較可以保證緩衝區和同盟的安全不變。若緩衝區國家出現民主產生的領袖與自由思考的社會,「為單一強權提供緩衝區甚至結盟」的國家路線可能就會受到衝擊。所以無論蘇聯或是西方,對於屬於自己的緩衝區國家和同盟國家之中由領袖操作,利於鞏固統治的專制主義或神本主義都聽之任之。
今天西方和俄羅斯 / 蘇聯的二元對抗架構已經逐漸緩和,反恐戰爭並非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的對抗,因此筆者比較樂觀的認為,在緩衝區的概念逐漸從伊斯蘭世界淡化之後,這一地區的政治民主與社會開放是較可預期的。但「阿拉伯之春」是否能緩解西方和伊斯蘭體系的不對稱現實?仍需要彼此更多的了解和智慧來決定。
張國城
澳洲國立新南威爾斯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曾任行政院反恐辦公室專門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