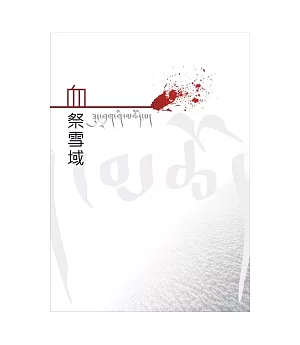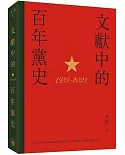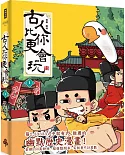推薦序1
茉莉:歷史不能任由勝利者塗抹──讀達瓦才仁的《血祭雪域》
達瓦才仁出生太晚,沒來得及親眼目睹四十多年前,西藏高原那一場悲壯卓絕的抗暴起義。當他還是一個流鼻涕的小男孩時,佇立村頭,看見西藏湛藍美麗的天空下,野地裡四散著當年留下嶙嶙白骨–村裡家家都有人被打死或餓死。西藏人沒有土葬的習慣,死去的人沒有墓碑,只有骷髏、腳鏈與野草雜生的一片淒涼,告訴他那裡曾有厚積的鮮血被時光沖刷。
夜間的篝火旁,家鄉老一輩悄悄談論著四水六岡游擊隊浴血抵抗漢人的戰爭,小小的達瓦挨著父親和伯伯坐下,靜靜地聆聽著那些不許被文字記載的故事。一曲西藏民族屈辱哀痛的長恨歌,就縈繞在他幼小而沉重的心靈裡。
我認識達瓦時,他已經不是昔日聽故事入迷的小男孩,而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年輕官員了。在我1998年訪問印度西藏流亡社區期間,他負責做我的翻譯,我們因而成了姐弟般的好朋友–這是我的人生幸事之一。達瓦曾誠懇地告訴我:他有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想把西藏人五十年代那一段悲慘的抗爭史記錄下來,傳給後代。
作為一個精通漢語的藏族知識份子,達瓦非常清楚地瞭解,那一段血染的歷史在漢族勝利者手裡,其真相是怎樣被嚴重歪曲,其史料是怎樣被存心隱藏。不少漢藏雙方的當事人和目擊者都被迫緘口,中國官方出版的西藏當代史,其中撰寫的「平叛戰爭」,竟然拿弱小民族的血淚塗抹自己的偉大輝煌,歷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而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寄人籬下生計維艱,顧不上做這項搜尋整理歷史的工程。
但達瓦堅信:失敗者應該書寫自己的歷史。如果失敗者沉默,勝利者墨寫的謊言,就會徹底掩蓋血腥的真相。西藏的歷史絕不只屬於過去,它與現在的西藏的處境有直接而複雜的關係。追尋歷史、直面歷史不是為了撫摸傷口哀吟,而是一種頑強的現實抗爭。只有失敗者不肯遺忘,那麼,勝利者永遠不可以說:他們征服了一個民族,他們獲得的真正的勝利。
達瓦的恐懼是很深的:參與那場抗暴起義的西藏戰士已經垂垂老矣,他們那無比珍貴的歷史記憶,就要淹沒於荒涼的山野與江河,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失去痕跡。
因此,達瓦經常向朋友訴說他的「心病」,不知感動了何方神聖,一位台灣女記者來到達蘭薩拉,被達瓦這份深沉的心願所吸引。從此,台灣女記者林照真和達瓦才仁展開了長達幾年的合作。他們拿出自己的積蓄,花費了大量休息時間,遍訪流亡在印度、尼泊爾山區的年邁西藏戰士,在艱苦的條件下做負責細緻的調查訪問。根據上百份採訪實錄,林照真撰寫了她那著名的《喇嘛殺人》一書,達瓦在那個基礎上繼續採訪,蒐集資料,終於完成了這本藏文的《血祭雪域—西藏護教救國抗戰史》。
達瓦這本書出版之際,正好碰上達賴喇嘛派遣特使訪華,漢藏關係的解凍,看來有了一線亮色。那麼,仍然執著地書寫一部被人拋在腦後的血戰歷史,對今天以及未來的中國和西藏,又有甚麼用呢?
對西藏人而言,這本書的重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漢藏關係有怎樣的進展,一個民族必須正視自己的歷史創傷。對我們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重新審視本民族罪孽的機會。為了使不忍卒讀的歷史不再重演,使施暴者與受害者得以和解,直面歷史,是群體改變的第一步。
推薦序2
林照真:還原歷史原貌,誠實面對西藏問題
儘管西藏問題已經停滯近半個世紀,但有關西藏問題的媒體報導不但未曾稍減,更常占據國際輿論的焦點,彷彿一直在提醒世人,在失去地平線的那一個角落,有一個愛好和平的西藏民族,一生追求不殺生的佛教境界,卻在政治高壓統治下,被迫遠離家園,成為人數漸減的黃昏民族。諷刺的是,流亡藏人失去回家的權利,卻獲得國際媒體最大的眷顧。他們在控訴中國政府布正當的統治時,雖可以現實的西藏問題為本,內心更遺憾中共入藏後,那一段歷史真相的斷裂與殘缺。
這是達賴喇嘛非常關心的一個使命,達賴喇嘛多次呼籲流亡藏人應努力記下中共解放軍入藏後所發生的真實經過;這同時也是已近衰老的老藏人,內心難以放下的沉重負擔。在中共極力宣傳治藏五十年的豐功偉業中,是絕不會提起當初入藏時,與藏人發生的血腥屠殺的;而藏人一連串的救護行動,導致許多藏人枉死家鄉的不幸,自然也不會寫入中共的正史中。然而,在中共粉飾太平的資料之外,流亡西藏始終難於提出一套完整的中共入藏史,以讓西藏新生一代領受上一代藏人,曾經發生的衝突與犧牲。
令人感歎的是,藏人或是因為流亡,或是在印度寄人籬下時為三餐奔走,實在沒有多餘精力去記載這段傷心史。以致,幾十年下來,即使有極少數藏人能夠克服最大阻力,以口述歷史方式完成當初入藏時的驚悚,卻也難有系統性的呈現。而多數藏人更是只能在自家屋簷下向子孫輩感歎,又或者最多只能在流亡藏人的私領域中流通而已。
這樣的焦慮一直存在達瓦才仁心中。它是西藏流亡政府中負責中文期刊《西藏通訊》的主編,其中文能力甚至超過一般漢族知識分子許多。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是他未曾一日中斷的西藏民族意識,以致與他接觸的人,都能深刻感受到他的急切心情。記得我第一次以台灣中國時報記者身分前往印度達蘭莎拉採訪時,達瓦是當時外交部秘書長丹巴才仁指派給我的翻譯。當時雖是第一次見面,但達瓦很快體會到我希望深入了解西藏議題的決心,因此,他給了我許多幫助,而且,他必定僅守翻譯者的立場,除了忠實翻譯外,絕不會刻意誤導或是提供偏頗的訊息。
記得,有一回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簡易餐廳吃飯時,達瓦叫了「饃饃」吃,「饃饃」其實就是中國人的小籠包,很容易就吃飽,不講究美食的達瓦,一向是一盤「饃饃」就了事,很少變化。
達瓦很快吃完,他隨後談起他的「心事」。他提及曾與一個朋友打算完成中共解放軍入藏時的口述歷史紀錄,以讓這段重要的史實能夠突破中共的粉飾,並讓歷世藏人永遠記得當時西藏因為抵抗而發生慘烈的戰鬥與犧牲經過。但是,這個心願由於公事忙碌,以及經費困難,一直無法達成。
達瓦的困難對我而言並不是問題,當時我對西藏問題才剛入門,也很希望能夠透過有意義的採訪更深入掌握西藏問題的精髓,因而,我便建議由我來克服物質上的困難,兩人一同設法遍訪流亡在印度、尼泊爾的年老藏人。於是,我多次前往印度、尼泊爾,與達瓦尋遍當時曾經參與戰鬥與抗爭的西藏重要人士。記得為了採訪「四水六領護教志願軍」的右翼指揮官然楚阿旺,我們在德里的藏人定居點然楚阿旺住處,與他的訪談次數約達十餘次,最後總算能清楚釐清事件的原貌。此外,我們也坐了三十餘小時的火車到達大吉嶺,去訪問當時負責美國情治單位秘密接觸的拉莫才仁。以及,我們到了尼泊爾,試圖訪問當時木斯塘游擊隊總指揮根益西,在等候多時、一再說明解釋後,終於得以訪問他,以印證當時的反抗經過。
更令人驚奇的是,大多當時勇敢的游擊勇士與護教義勇軍,在我們訪問時,都已是年近黃昏的獨居老人,常常我們的造訪令他們萬分驚喜,更高興這段歷史能有重見天日的一天。已不只有一名藏人對我們兩個人說,他們非常高興我這個外國記者能幫藏人把這些歷史真相帶出去;同時他們也希望能透過達瓦才仁的努力,讓年輕的下一代藏人,不忘回憶歷史的慘痛。
在訪問中,達瓦一方面是一個採訪人,同時也要扮演翻譯者。因此,他的辛苦更甚於我。而且,我們在多次採訪時,都是住最便宜的旅館,吃也非常簡單。一些搭乘飛機可到的地方,我們卻得坐著火車踽踽前進。偶爾我還會哀怨地抱怨幾聲,達瓦卻覺得這些都是小問題。因此,當我在前往大吉嶺的火車上欣賞兩次日出,或是住在地下室得便宜房間,忍受印度刺骨的寒冷時,都會想起達瓦的幽默與一笑置之。當然,當我在抱怨伙食不佳時,達瓦依然是只要有「饃饃」就覺得是人間一大享受。果然,當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時,我們才能突破印度、尼泊爾廣大領土的限制,多方採訪到重要的藏人。
在我們的採訪計畫中,原本是建議由我以中文撰寫,達瓦負責翻譯成藏文,分別提供台灣與西藏不同的讀者。但在實際採訪後,卻發現我們兩人的採訪重點經常不同,加上台灣讀者與西藏讀者對西藏議題的了解基礎完全不同,興趣與宗旨意不相同,因而兩人決定,我依然負責我的部分,但西藏讀者的部分則由達瓦須責撰寫。
我們前後花了約兩年的時間陸續採訪,在我於1999年3月出版《喇嘛殺人》一書後,達瓦的採訪工作仍在進行,因為他又發現許多重要的採訪對象而不忍放棄。因而,現在由他負責出版的著作必然比《喇嘛殺人》更加充實,目前除希望有朝一日能翻譯成藏文,讓更多的藏人了解這段歷史,畢竟,這是當初達瓦起意進行這段口述歷史的最大用意所在。
身為一個台灣人,在與藏人有更多的接觸後,我除了感嘆藏人不幸的歷史際遇外,更會讓我感受到自己擁有的竟是這麼豐富,因而我學習到更加惜福,更加努力。達瓦在他流亡之後,目前已多年無法與他的父親見面;儘管他天資優厚,但西藏流亡的命運卻讓許多優秀的年輕一代無法獲得更多的栽培,達瓦才仁雖然只有警察學校畢業的學歷,私下卻非常用功,我深知如果他能一如我般生長在自由開放的社會,相信必然會有更多的發揮。每每想到藏人流亡後民族失落的命運,只會讓我在面對台灣問題時,更加態度慎重。
達瓦能夠完成這本書,是他在工作之餘的第一本著作,這本書必須專心閱讀,才能體會作者的用心。然而,對達瓦而言,之所以致力還原這段歷史原貌,更重要的並不在於宣傳與攏絡人心,反而是對中共治藏正當性進行最嚴正的批評與抗議。而在西藏問題亟待解決的今天,認真看待中國政府的功與過,也是還原當時這段歷史的主要用意。
翻開本書,可以由衷體會到西藏問題的千頭萬緒,竟都是從中國入藏後談起。者一段多數是發生在西藏境內的民族抗爭史,現在終於因為辛勤的口述歷史紀錄,而得以完整呈現。基於多年來關心西藏議題的謹慎態度,我向還不認識達瓦才仁的朋友愷切介紹他的民族熱忱,也願向更多關心民族人權的中文讀者,鄭重推薦本書。尤其,細細閱讀本書,人們必然可以從字裡行間,感受到近代西藏民族最深的傷痛。
前言
對先輩永恆的銘記與感恩
西藏民族的屈辱
我從小就聽過無數有關這場戰爭的故事,可以說我是聽著這些故事–包括我父親和伯父的故事–長大的。每當大人們聚在家中或原野的篝火旁聊天時,我總喜歡擠在他們中間悄悄地聽他們談論。因為幾乎每一個成年男人都參加過那場戰爭,因此大家談論最多的自然是各自在這場戰爭中的經歷。可惜我無法將我所聽過的故事寫進這本書裡,因為本書只記錄當事者的親身經歷,而我只記住一些情節,也不可能將兒少所聽的許多故事不相混淆地分清楚並記住講述者的名字;而且我對故事中的地點、寺院、邦酋等的名稱毫無概念──兒少時西藏已無寺院,我對西藏地名的認識僅止於某某人民公社或生產隊。因此,本書中我所描寫的情節要比我當時聽到的要輕鬆許多,因為我採訪的絕大多數是流亡到印度的人,他們大多是最先逃離西藏的,而更多的西藏人卻留在自己的家鄉奮鬥,所以戰爭更加激烈,鎮壓更加殘酷。可是我卻無法採訪他們,也無法紀錄最悲慘、最屈辱的歷史。這是本書最大的缺陷。
本書另一個缺陷是:未能全面、完整地描述西藏的反抗運動。由於西藏武裝反抗具有強烈的地方性,但我沒有能力採訪西藏所有地方的人,更主要的是,在很多地方根本就沒有參加過戰鬥的藏人活著逃離西藏!因此,實際上本書所描述的僅僅是整個雪域大地護教救國武裝反抗運動中的一部份而已。比如衛藏的西部──中共曾在那裡進行一號戰役,還有康區木里也發生過慘烈的戰鬥,這一切都未呈現在本書。即使是我的家鄉,根據《中國人口.青海分冊》記載,在戰爭結束後的1964年,六縣總人口比戰前的1956年減少23%,相當於損失所有的成年男性。其中如巴甘寺保衛戰,數千名僧俗參加戰鬥,雖然其中的情節我也聽說過許多傳說,但因找不到親身與戰者,所以也只能留下空白等待其他人來填補。
本書的第三個缺陷是:對於戰後接踵而來的大逮捕與飢餓沒有全面的描述。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早早逃離西藏的流亡藏人並未親身經歷過這一切。
對於當時的苦難,我聽到的實在太多了。記得一次曾問我的至親:「當時您是怎樣活下來的?」他想了想後告訴我:「當我吃著草糠時,中國人問我們好不好吃,我高叫好吃;我餓得眼冒金星雙腿發軟,中國人問餓不餓,我說不餓;他們問我新社會是不是很幸福,我說幸福得很;親人被綑綁批鬥,上邊問我該不該鬥,我說該鬥;中國人叫我拆寺院我就去拆,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我就是這樣活下來的,大家都是這樣活下來的。是的,當時西藏民族就是這樣被迫屈辱、苟且地勉強存活下來。然而我卻沒有辦法把那些苦難的歷史記錄下來。
少年時期的我,每當聽到長輩們回憶起這些屈辱和悲慘的往事時,總是希望自己快快長大,並發願將來一定要成為一名游擊隊員,為他們報仇雪恥。
墨寫的歷史掩蓋血寫的歷史
多少抱著這樣的願望,我來到了印度。然而,當我在印度聆聽達賴喇嘛尊者的教誨,拜讀他的論著後,我從開始的茫然逐漸地轉為釋然了。我記住了達賴喇嘛尊者的教誨:我們的努力不是為了清算過去,而是為了給西藏民族的未來爭取自由與幸福。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忘記這段屈辱的歷史──更何況這樣的屈辱仍在持續中。從1727年滿清將軍年羹堯在西藏安多的屠殺,到嘉戎和康區的屠殺等,無論是滿清、趙爾豐、國民黨、或共產黨,中國人的輝煌都是伴隨著西藏民族的屈辱和血淚而載入中文史籍中。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西藏民族在紀錄本民族的這些歷史時,卻選擇了集體迴避或遺忘:從西藏史籍中,我們很難看到祖先們曾經經歷過的屠殺與屈辱;人們記住了歷史上顯赫的達官貴人、修行聖人的姓名,卻少有人知道那些抵禦外侮之民族英雄的名字。甚至對五十年代這場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剛剛發生的戰爭,人們可以累牘連篇地看到中共政府歪曲編造的有關記載及對罪行的掩飾,卻很難看到西藏人對此所做的系統記錄。當然,我們這一代藏人都知道中共所說的是假的,可以不屑一顧,但是我們的下一代會怎麼樣呢?如果我們沒有把上一代人身上發生的歷史悲劇真實記錄下來,想想國民黨在他們的檔案中放置一些假資料,然後由中共供上「歷史資料」的殿堂並作為侵佔西藏之根據的歷史事實,我們藏人的後代面對中共製造的「歷史資料」,可能也同樣無法說清事實真相。
翻閱有關的中文資料,可以不斷看到中國政府在告誡下面的人,有關西藏這段歷史要「宜粗不宜細」、「不要糾纏細節」。再看看周圍同時代或更年輕的西藏人,他們在談論諸如印度史、中國的歷史、世界史、納粹暴行之類時,可以旁徵博引侃侃而談,但談到西藏歷史乃至於他們父輩的悲慘經歷時,卻顯得極為陌生。面對這一切,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可以相信:墨寫的歷史就一定不會再一次地掩蓋血寫的歷史呢?
為子孫留下真實的歷史
作為雪域的後人,我們當然要永遠銘記、敬仰和感恩那些為西藏民族的生存和自由而犧牲或戰鬥的人們。
由於感恩他們為西藏民族的生存而做出的犧牲,由於敬仰他們為雪域民族的自由而表現出的勇敢,同時也為了給雪域子孫後代留下真實的歷史,為使他們瞭解先輩為民族自由和尊嚴而戰鬥、犧牲及所經歷的屈辱,我一直希望將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但在流亡中生計艱難,微薄的工資尚不足養家餬口,遑論負擔此一工作的開支。因此眼看著那些老人家帶著他們的珍貴回憶一個個辭別人間,徒呼奈何而外束手無策。
1997年達賴喇嘛尊者準備訪問臺灣,有許多臺灣記者前來採訪,許是因緣成熟,當我和記者林照真談及此點,她竟立即非常認同其重要性,並表示願意協助寫成書。最後我們約定她寫中文版我寫藏文版,由她提供採訪與寫書的一切費用。此後一年多,林照真先後多次來印度由我陪同至各地採訪。1999年3月10日,林照真的《喇嘛殺人》在臺灣出版。
曾有兩回,採訪後第二次去核對一些問題時,受訪者已經與世長辭。經歷這段歷史的倖存者眼下很多已是耄耄之年,來日無多,如不及早將他們的經歷記錄下來,這些史實也許就永不為人所知。本書盼能拋磚引玉,有更多人將這段史實記錄下來留諸後世。
由於只能利用下班後與假日來寫書,因此我的藏文版未能與林照真的書同步完成。之後,我也以自己一點積蓄陸續補充採訪了一些人,然因難民財力不足,許多問題無法如願,只能留下這些無盡的遺憾了。
因為我慣用中文,去年林照真建議我先以中文書寫出版,再譯為藏文。可以說沒有林照真的幫助,就沒有本書。衷心感恩。
雖然我很清楚無數和我同一時代的西藏人為了民族的自由和尊嚴正承受著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代價,我作為雪域後人,本應和他們一起共同承擔民族的苦難。但,惶惶然,我還是選擇了流亡的安全。本書的完成,也算是對我愧疚負罪之心的一絲安慰吧。
最後,感謝前妻札西黛措的支持,每當我拿走家中僅有的一點積蓄外出採訪時,她從無怨言,總對我說:「達賴喇嘛尊者都這樣辛苦,我們當然應該。」此外,西藏博物館提供歷史相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幫助承印了本書,在此一併致謝。
跋熱.達瓦才仁
2002年8月26日(印度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