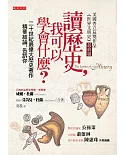序言
黃興濤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潘光旦的重要地位大約毋庸置疑。韓明謨先生在《中國社會學名家》一書中,就將他列為中國社會學「較突出並有代表性」的四大名家之一(另三家為孫本文、陳達和費孝通)。與此同時,他還是現代中國首屈一指的優生學家、性心理學家,有成績的民族學家和重要的社會史家。作為學者的潘光旦,可以說既學有專攻,又博識多能,屬於那種思想敏銳、特色獨具而又積極用世的「學術大家」一類。
記得1980
年代,中國社會學開始「重建」、社會史研究潮流剛剛興起之時,我和許多青年學子一樣,都經歷過一個熱心「悅讀」潘光旦和費孝通著作的時期。潘氏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兩書和費氏的《鄉土中國》等書,堪稱那個時代社會學與歷史學互相滋養的代表之作,它們曾帶給無數雄心勃勃的學子以學養的積澱、研究的激勵和方法的啟迪。後來,在探討民族性改造思想和「中華民族」觀念形成認同的過程中,潘氏那種介於種族和國家之間的獨到「民族」界說,以及在《性心理學》譯注中所體現出來的中西文化融會功夫,又曾激起自己由衷的贊佩和敬意。像他那樣有社會關懷、富思想能力、輕學科界限且底蘊深厚的學者,得到學人喜愛、漸受學術史家重視和研究,實在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若要將潘光旦放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去看,或選擇潘光旦作為思想史研究的專門對象,人們的觀點則可能會有所不同。我不得不坦承,在閱讀呂文浩這本《五四啟蒙思想的延續與反思─潘光旦社會思想研究》之前,我是從未認真思考過潘光旦算不算一個重要而有特色的思想家、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地位或代表性這一問題的。但讀過此書之後,或者說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我卻又有了一些新的認知和想法。
長期以來,我們的近現代中國思想史書寫,主要以政治思想史為主、文化和經濟等思想史為輔,關心和敘述的都是精英人物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近些年,葛兆光等先生提倡「一般思想史」研究,呼籲人們重視那些對現實社會生活發生了切實影響的普遍思想觀念,我是深表贊成的。不過在我看來,這種「一般思想」不僅要具備普遍的「社會性」,還要能體現打破各門學科、各個領域專門界限之思想的「基礎性」;同時,其思想者主體也不能只局限於某個特定的階層,如葛先生所提到過的「一般水準的普通知識份子和普通文化人」,而更需考慮「精英」與「大眾」互動的複雜情形。
特別是在近現代中國傳統社會及其觀念發生重要轉型的特殊時代,此種一般思想觀念形態的形成,顯然無法漠視精英分子的思想參與和作用過程。
在閱讀呂文浩此書的時候,我忽然感到,如果出於上述思路,那麼那些精英人士在大眾媒體上,就戀愛、婚姻、家庭、性、生育、民族、國家、文明等社會生活的「基本問題」所發表的有特色有影響的「社會思想」,是否也應該成為近現代中國「一般思想史」所關注的對象,並程度不同地構成其可供選擇的思想內涵呢?這的確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在此書中,文浩雖沒有明確談及「一般思想史」,但通觀全書,他無疑十分重視這些「社會思想」的內容,甚至可以說,他正是將這些「社會思想」視作潘光旦思想的核心部分而加以深入闡述和精心分析的。在「導言」裡文浩還曾強調,潘光旦「捲入時代思潮的程度既深且廣」,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在上述許多社會文化問題上,他多參與過公開的討論和論爭。我不知道像這樣從「社會思想」重要性的視角來理解潘光旦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獨特意義,是否與文浩一致?或者說至少能為文浩所認同?
當然,文浩主要從「後五四時代知識份子」突出代表的角度,以知識、學術與思想的關係問題為方法論意識來揭示潘光旦的思想史地位,也是別具見解、很富啟發性的。誠如他所言,以潘光旦為突出代表之一的後五四時代知識份子,他們大多是依託於學院體制的職業學者,其充當思想界的重要角色,往往在思想論述中打上深深的學術烙印:「也許他們的主張多具書生意氣,但其優勢也是很明顯的,他們的西學知識不再是支離破碎的、一知半解的,他們對於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判斷,往往經過科學的盤詰,具有更加紮實的學理依據。」(見該書「導言」)。因而他們對傳統和西方文化往往採取較為平靜與理性的態度,對五四一代知識份子激進的思想批判,亦多能予以雙重的反省。這在某種程度上,毋寧說也正體現了時代思想水準的總體提升。
潘光旦留學時所學專業為優生學,回國後又長期任職於社會學界,在他身上,那種經由優生學訓練和社會學薰陶而形成與強化的「社會選擇」(他有時又自稱為「人文選擇」)的獨特思想方法,可以說是牢不可破、自覺到家的。他以此觀察和思考各種社會和文化問題,也以此評斷世間諸事。這是他作為學者型社會思想家的一個突出的特色。因此當他讀到胡適主張對西方文化取「Wholesale
acceptance」(全盤接受)態度時,便忍不住要起而辯論,因為「Wholesale」乃好壞不分、整個「批發」,恰是要省略掉那萬萬不可省卻的「選擇」功夫。後來胡適雖接受潘氏批評,承認自己的說法有「語病」,自嘲即便是99%也不能算作「全盤」,但其實他卻未見得真正領悟了潘氏所批評的要領。
正因為重視「選擇」,潘光旦對主張改造中國民族性的思想同道張君俊也要嚴厲批判,指責他對自然選擇和社會選擇說缺乏瞭解,強調「民族素質的改造,除去選擇,更無第二條路可走」。為此,他主張「婚姻要選擇,生育也要選擇」,一切的一切都要選擇。而為了選擇,控制和引導的功夫實在又必不可少。
這種主動「選擇」的運思方式既成習慣,也就有力地保證了潘光旦總體思想的理性品格。比如對於中國古代經書,他既反對那種「完全唾棄不講」的簡單態度,也並不贊同「談不上整理、談不上選擇」地去讀經;他強調中華民族「有過幾千年的閱歷與經驗」,這「整個民族的生活經驗」,的確值得「當代人的一盼」,但又認為只有用現代眼光加以「選擇性整理」,它們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為「轉移世界環境」作出應有的貢獻,等等(可參見文浩本書第八章「潘光旦的中西文化觀」的有關論述),不一而足。
「選擇」既是自然的、又是社會與人文的;既是歷史的,又是當下的,它是一種需要、一種本能、也應該是一種自覺的生存狀態與方式。潘光旦特別將「選擇」與英文中的「adaptation」過程緊密聯繫起來,把「adaptation」苦心孤詣地譯成「位育」而不翻作「適應」,真的是耐人尋味、啟人深思。在他看來,翻作「適應」,很容易使人狹隘地誤解為是對環境的一味「遷就」,這樣人的能動選擇性就不免要被忽視和輕視,這是他所最不能容忍的。
「位育」一詞的靈感來自《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位育」又被稱之為「中和位育」,它體現著一種自然與人道的動態合一境界。這樣的翻譯是否準確姑且不論,但它卻無疑凝聚了潘光旦融會中西的旨趣與精神。那種學者自是的「書生之氣」,也在這一創構之詞中一併彙集,彰顯無遺。
「位育」之道提醒人們在做選擇時,不僅要有一種自然適度的節制,還務必保持一種平靜無偏的心態。自大的態度和自卑的情結,都容易導致錯誤的判斷和選擇。在這個問題上,潘光旦對「早婚」話語的論析很有典型性。清末以降,以梁啟超為首的啟蒙思想家總愛將早婚與國家積弱聯繫起來,認為早婚傷身弱種,罪大惡極,以至人人以為至理、信奉不移。而潘光旦卻從優生學原理出發,並引證當時大量的科研成果指出,早婚遲婚其實各有優劣,早婚既不必與傷身有直接關聯,也並不必然導致缺陷較多的產兒。梁啟超式的論調之所以流行,不過是國人積久的自餒心理作怪罷了:「自餒心之所至,至認種種不相干或不甚相干之事物為國家積弱之原因,從而大聲疾呼,以為重大癥結端在乎是,早婚特其一例耳」。這種近代中國少有的「異見」,對我們理解「禁早婚」的主流話語之特性,意義不言自明;而潘光旦思想的反思特質,也可以由此略見一斑。
作為一個社會思想家,潘光旦關於「社會選擇」或「人文選擇」的思想還有待於人們去作進一步的揭示與闡發。而這種思想有時來源於或體現為他對社會日常生活的深入觀察和批判意識。比如他對中國人遊藝生活中「麻將」的流行及其社會效應的分析,就頗有些發前人所未發之妙論。在他看來,「中國人的民族性與麻將牌中間,實在有一種固結不解的心理因緣在」。麻將牌與外國紙牌的玩法不同,它完全用不著「合作的功夫」,不僅用不著合作,而且合作還要不得。玩家一定得假定「其餘三人無一不是你的敵人,要對他們鉤心鬥角,一刻不可懈怠。……他無時不在想佔便宜,或至少叫別人也占不到便宜」。他的意思是說,中國人對麻將牌的酷愛與民族病態心理有關,而反過來,此種日常娛樂方式的社會選擇,又不斷固結強化著此種民族心理。諸如此類的社會批評,在潘光旦的文字中並不少見,文浩此書中也多有論述,它實際上反映了「後五四時代知識份子」在力圖超越此前啟蒙思想家的同時,對其啟蒙主題也有一種深沉的延續與自覺的繼承。
關於潘光旦的思想,認知的視角自然很多,其豐富的內涵,也絕非淺學者所能盡揭。文浩研究潘光旦多年,又受過社會學與歷史學兩種學科的訓練,故在綜合認知和整體把握其思想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通讀該書,我覺得他對潘氏思想的重要內容、特點與意義等問題,都有出色的闡述和深入的論析。在解讀潘氏思想的過程中,他注意揭示其思想的「學理」依據一點,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我與文浩是同道也是朋友,對他的為學態度和認真勁頭向有感觸。他劬學覃思、不喜「花槍」、重視資料、講究表述,這種風格也是我所喜歡的。蒙文浩信任,命作序言,因得以先睹大著為快,並草此讀後之感,以與作者和讀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