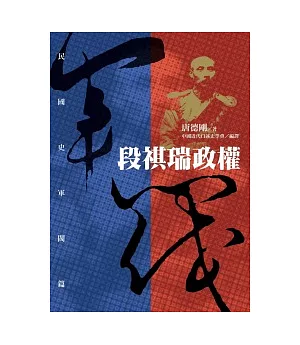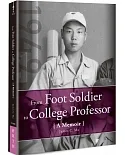編者序
唐德剛教授長期鑽研民國史,數十年如一日。他的早期著作和晚期作品的重點頗有不同。早期的著述都是專著,主要是口述傳記,以五十年代後期參與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史學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的訪談為基礎,如《胡適口述自傳》和《李宗仁回憶錄》,都是傳誦一時的經典之作。晚期作品則特別著重撰寫民國通史,氣魄恢宏,觀點獨到;而且極力打破繁瑣、枯燥的學院派傳統,以「唐派新腔」的散文下筆,幽默、流暢,亦莊亦諧,妙趣橫生;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提倡「務求其通俗」的主張,以期實現雅俗共賞的目的,為兩岸千千萬萬的讀者所熱烈歡迎。
一九九一年夏唐教授從紐約市立大學退休,剛放下教鞭,便潛心撰寫民國通史。先後出版《晚清七十年》(一九九八)和《袁氏當國》(二○○二),前者是晚清導論篇,後者是北京政府篇,二者是互相銜接的。二○○○年修訂了撰述計畫,打算分為五篇,除上述兩篇外,還有國民政府篇(一九二八~一九四九)、人民政府篇(一九四九~二○○○)和國民政府在臺北(一九四九~二○○○)等三篇。二○○五年《毛澤東專政始末》面世,就是撰述計畫中的人民政府篇;但是這個計畫的主軸──國民政府篇,卻始終沒有出現。
二○○一年底唐教授害了一場重病,差點不起,體力恢復很慢。直到二○○五年,健康狀況稍有起色,便與吳章銓博士重新審議撰述計畫,再次修訂計畫大綱,分為軍閥篇(一九一六~一九二八)、五四運動篇(一九一九)、北伐篇(一九二七)、國民政府篇(一九二八~一九三七)、抗戰篇(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和中國近代轉型論等六篇,顯然比二○○○年的大綱較為細緻。可惜重病之後,年高體弱,終究心有餘而力不足,很難再振筆直書了。修訂計畫無法落實,董狐之筆從此封塵,民國通史計畫不幸中斷。
但是他對民國通史始終未能忘懷,在閒談時常常流露出無限悵惘。自二○○七年起,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同仁常常結伴到唐府拜訪,有時七八人,有時兩三人一同前往。除了正式訪談外,也陪兩老閒聊,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他老人家談得高興時,就不斷鼓勵大夥分頭撰寫民國史。二○○九年初我們最後一次到唐家探望,他還是苦口婆心,舊事重提,並且一再講述四十年前(一九七一)推卻撰寫蔣總統全傳的往事,感到萬分遺憾。看來民國通史沒有完成,撰寫蔣傳的難得機會悄然溜走,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在過去兩年,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同仁分頭整理他留在紐約的手稿、論文、詩詞、書信等資料,現在總算有一點頭緒,希望為中斷的民國通史計畫做一些補充,《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正是我們的初次嘗試。他多年前以英文寫成的《中國革命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的翻譯工作也快要完成,希望不久可以付梓。但願能夠按照他的修訂大綱,整理現有資料,逐步編輯成書,以慰良師的期盼於萬一,並聊表無限懷念的微意。
其實《段祺瑞政權》一書,遠流出版公司早在二○○四年就差不多編好了,後來把初稿送唐教授過目,不料出了亂子,郵寄回臺灣的訂正稿不幸遺失,一去無蹤。直至今年初,游奇惠主編舊事重提,寄上原出版計畫,建議我們把遺稿重新編纂。遠流的建議與我們的構想不謀而合,可謂求之不得,因此立刻表示贊同。我們馬上著手整理資料,除已在《傳記文學》發表的幾篇有關軍閥的文章外,又從他的遺稿中挑出〈談談打打的護法戰爭〉(此文太長,現在拆為兩篇,按原來小題,分出〈再造民國,段閣復起〉一文)和〈論桂系〉兩篇未刊長文,並翻譯了早年在哥大的英文講稿〈民國軍閥概述〉以作補充,終於使本書劫後重生,能夠與讀者諸君見面。
不過,復查修訂大綱,他顯然有意全盤探討軍閥史的種種問題,並非僅以皖系軍閥為限。但是。遍翻遺稿,沒有發現直系的文章,也沒有討論粵、滇軍閥的稿子,所以本書基本上還是以皖系及黎(元洪)、段的府院鬥爭為主軸。
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繪袁後中國的狀況,闡述北洋軍閥和政客的爭奪,實力派段祺瑞脫穎而出,掌握大局的經過,其中〈王綱解紐,軍閥割據,政客縱橫〉一文深入分析了軍閥時代出現的原因,不斷互相砍殺的現象,憲制混亂,黎、段寵臣的纏鬥造成府院之爭的經緯,可以說是全書的綱領。此外,〈民國史軍閥篇四圓四方圖解〉一文,簡明扼要地闡明軍閥時代的分期。民初大小軍閥三千多人,縱橫捭闔,朝秦暮楚,史實紛繁,使人眼花撩亂。唐教授抽絲剝繭,條分縷析,並附上圖表,把軍閥時代(一九一二~一九二八)分為四期,每期四年,井然有序,化繁為簡,一目瞭然,清楚闡述了軍閥割據時代的梗概,難能可貴。
第二部分專論段祺瑞政權,說明黎、段上臺後不久,就爆發嚴重衝突,勢成水火,鬥爭極端激烈。袁世凱死後,黎、段兩頭馬車走馬上任,恢復《民元約法》和舊國會,行「虛君實相」的責任內閣制,其實是非牛非馬的混亂制度,既非總統制,也不是真正的內閣制,因此政府運作極度困難;同時人事問題複雜,黎、段的「二爺」(寵臣)孫洪伊和徐樹錚纏鬥不休,結果一九一七年竟藉參戰案而爆發激烈的府院之爭,黎聽信政客胡言,昧於時勢,悍然拉段下馬,引起北洋軍閥群起反對,結果舉國騷然,天下大亂,終於造成統一的中國一分為二,禍延至今,兩岸分裂狀態依然無法解決。
第三部分「餘緒」中,〈論桂系〉是唐教授的未刊遺稿,只有前半經過整理、繕正,後半篇是未經修飾的初稿,然而全篇深入淺出地探討桂系的特徵,綜論其在民國史中所起的作用,觀點獨到,言人所未言,值得細讀。桂系雖有相當獨立的武力、地盤和財力,卻始終不能入主中樞,充分反映其地方軍閥的特性。不過新桂系統一廣西後,能夠認清大局,加入國民黨,成為支持革命軍北伐的最重要力量,而國民政府的確立,桂系的歸附也決不可少。北伐後李、白勢力迅速膨脹,如日中天。但是一九二九年二月武漢事變爆發,竟然不堪一擊,土崩瓦解,不但充分暴露桂系的弱點,而且也加強了蔣介石削藩的決心,引發中原大戰(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同時張學良於一九三○年秋應召率師入關參戰,翌年日寇便乘機炮製九一八事變,最終造成全面侵華之局。因此武漢事變與西安事變同是近代中國國運的轉捩點,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一文是唐教授的力作,扼要闡述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勢力迅速膨脹的經過。這時張作霖擁有三十七萬雄師,打算以武力統一全國。不到一年便控制黑、吉、奉、熱、冀、魯、蘇、皖八省,天津、北京、上海三市,擁有半壁江山,傲視群雄。稍後老帥更應孫傳芳之邀,出任安國軍總司令,一九二七年又在勸進聲中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儼然以國家元首自居。然而由於抗拒日人無理要求,結果難逃皇姑屯事變的厄運,粉碎了奉系一統中原的宏圖。
從整體而論,軍閥也有賢與不肖,不能一概而論。「張作霖,『軍閥』也,然作霖竟以拒簽『五路』條約而死國。吳佩孚,亦軍閥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據說,最後亦以誓不事敵而招殺身之禍。張宗昌,軍閥中之最下陳者,然濟南慘案前,亦嘗堅拒日軍化裝直魯軍以抗南軍之要求。大節無虧,均足垂名青史。」(見〈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另一方面,段祺瑞掌權之初,根據《民元約法》,實行責任內閣制,基本上還是依法行事的,並非後來無法無天之輩可比;而且「黎、段二人都還算是正人君子,有節操、識大體而清廉可風的、難得的政治軍事領袖」。問題出在民初根本沒有實行現代議會政治的條件,因此「形勢比人強,非兩個老軍閥的二『人』之過也」,可說是持平之論。(見〈皖系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不過,唐教授深信我國最終必將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他說,「我民族要做到把法律當皇帝的這一步,最樂觀的估計,恐怕最少還要等四十年。」(見〈再造民國,段閣復起〉)只是四十年的推斷,說不定還是有點太樂觀吧。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改朝換代總不免出現藩鎮割據現象,昔日的所謂藩鎮,就是近代的軍閥。如果我們從西漢算起,藩鎮割據之局先後出現不下三十次。從宏觀史學來看,軍閥割據是我國轉型期中一個偶然現象。「我國史上第二次轉型,從帝制向民治轉去,這個總方向是必然的,不會變動的;但是在各小階段中的變動,則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覆無常的。這個偶然出現的軍閥階段,就是個很標準的說明」(見〈王綱解紐,軍閥割據,政客縱橫〉),相信是十分客觀的推斷。
在編輯本書期間,蒙各方友好大力協助和匡正,特此一併申謝。
禤福煇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於加州灣區寓所
【編者簡介】禤福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學士,哈佛大學碩士,劍橋大學研究。紐約文化工作者,近年從事抗戰史研究,現任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會長,著有《地獄證言:抗戰時期被強擄赴日中國勞工的血淚口述》(香港:利文出版社,二○○五年)。
他序
人文親切──唐德剛史學著作的獨特魅力
唐德剛教授逝世兩周年之際,遠流出版公司決定出版他的《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幾位同仁,協助該公司編輯整理唐教授的書稿,我也藉此機會再次重讀唐教授的這部民國史及其他史學著作。《段祺瑞政權》付梓在即,我們口述史學會的會長禤福煇寫了編者序介紹本書的整理過程,並命我也寫一短文,談談我閱讀唐德剛史學著作的體會。
唐德剛教授生前便文名遠播海內外,他的史學著作和其他著作廣受歡迎,擁有眾多的讀者;他逝世之後,他的著作成為海內外華文世界的寶貴人文財富。這是唐教授的非凡成就,早有識者論之。
如果我們問,為什麼唐德剛教授的史學著作會有那麼大的魅力,在海內外華文世界長盛不衰地擁有眾多熱情的讀者?最簡單的回答,是唐教授寫得好。好書自然有人讀。如果我們接著問,唐德剛教授的史書寫得好,好在什麼地方呢?這就不是三言兩語便講得清楚的。我願在此短文之中,不揣淺陋,談談我對唐德剛教授史學魅力的認識和體會,求教於喜讀唐氏作品的讀者朋友們。
我是專業歷史工作者,喜歡讀唐德剛教授的史學著作,有些著作是一讀再讀。綜合多年的閱讀體會,我最佩服唐教授的是他有非凡的本領,將個人興趣、當代顯學、大眾經驗及心理恰到好處地融合在一起,寫出既有卓越見識、又讓一般讀者讀來倍感親切的歷史著作。
唐德剛教授治史的個人興趣是中國近現代史;他在他的著作中數十年「曲不離口」地討論中國的「轉型」(transformation)問題,本是當代顯學;而唐教授反覆申述的中國「轉型」的長期性、「一轉百轉」的複雜性,經他老人家那枝健筆深入淺出地闡釋描繪,則表現為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日常經驗,有具體真實的人物故事可供參證、回味、思考。試問當代中國人,誰沒有生活在「轉型期」酸甜苦辣百味雜陳的體驗和觀感?當代中國,變化之快,真使人有十年已一世,滄海變良田之慨。在此「一轉百轉」,越轉越快的「轉型期」,常被轉得暈頭轉向、有滿肚子委屈、困惑的中國人,抽空坐下來翻一翻唐教授的歷史書,讀他那些對中國轉型特殊經驗獨具卓識的歷史分析和他的具有濃厚中國人情味的文字,自有一種親切。
「轉型」學成為當代顯學,原是人類經驗的自然反映:歐洲、美洲、中國,以至全世界,由「前現代」「轉型」到「現代」,自然有無窮的問題要研究,於是有各種理論應運而生。唐德剛教授生於一九二○年,在祖國度過青少年,親身經歷過中國的「轉型」,目睹了中國人的奮鬥追求、挫折失望。他在大學、研究所的專業是歷史學,受教於顧頡剛、郭廷以等名師,對中國「舊史學」向「新史學」的「轉型」,也有真切的認識和體會。二十世紀四○年代末、五○年代初,唐教授在當時的美國史學重鎮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讀博士學位,更是廣泛研讀當代社會科學的新理論新方法,對各國之「轉型」,有所比較;他將這些新理論、新方法,以比較的方法應用於研究中國之「轉型」,並將自己的親身體驗觀察融入於歷史分析,數十年如一日地以通俗清新的文字呈現自己的研究結果,終於成為獨樹一幟的史學大師。
唐德剛教授沒有創立任何「轉型」理論,但他卻將中國的「轉型」歷史寫得精采萬分,因為他善於博採眾家之長,同時又極清醒地避免各種門戶之見。唐教授是一位虛心而又自信的學者。他在念博士期間,虛心學習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由衷讚歎西方現代歷史學引進社會科學理論方法之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唯其虛心,他也能看到西方理論的局限性。比如說,他很早就指出,西方研究「現代化」及「轉型」的許多理論、方法,注重人類經驗的「通性」是其長處;但忽略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則是其短處。揚其長避其短,是唐教授很早就得出的結論,也是他多年撰述中國「轉型」歷史的具體寫作實踐,我們讀他老人家的書,時時便會看到他在不同地方對此問題的討論和提示。
唐德剛教授是一個有抱負的史學家。他既有對西方學術界顯學各派識其長亦見其短的眼光,隨之而來的便是他要超越各家各派的自信和雄心。早在一九六二年,正當壯年的唐教授便和一家美國出版公司(Crowell-Collier,一九六五年後改名,通稱麥克米蘭〔MacMillan〕)簽過約,擬以英文寫一部中國現代通史。此書後來因故未能完成,但唐教授撰寫一部有特色的中華民國史的雄心始終未泯。據汪榮祖教授回憶,唐教授於一九八○年發起組織「北美中華民國史學會」(一九八三年正式成立時改為「北美二十世紀民國史學會」),「唐德剛原意要大家合寫一部『民國史』」,「他有鑒於當時中國大陸與台灣研究民國史都不免受到政治的干擾,所以認為我們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可以「搞一個民國史研究的第三勢力」。(《唐德剛與口述歷史》,遠流版,頁一一七~一二○。)
現在回頭去看,唐德剛教授當年雄心勃勃,是因為他對這「第三勢力」的諸項優勢(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史料)有清醒的認識和充分的自信。唐教授熟讀中國傳統史學、當代西方顯學,對中西、新舊各派均知其長短,由此而發展起來的比較史學、宏觀史學的眼光和方法,就不是當時遵循官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教條的大陸學者,或恪守傳統史學清規的台灣學者所能具備的,更不用說那時候兩岸學者都仍受制於政治干擾。至於史料,試問有誰比唐德剛更有優勢呢?他老人家不僅對傳統史料如數家珍,更得天時、地利、人和,對李宗仁、胡適、顧維鈞、張學良等民國期間的黨政要人和文化教育界領袖進行過口述歷史訪問,和他們有過長時間的交往,對他們有近距離的觀察。當然這些口述史資料後來都已公開,並翻譯成中文供研究者及一般讀者參考閱讀,人人都可使用。只是沒有唐德剛教授那種親自長時間地進行口述史訪問並下工夫核對史實的實踐,要達到唐教授對這些口述史資料的領會、消化和恰到好處地使用的那種水平,不是不可能,但是難乎其難。
試舉一例。本書「餘緒」所收〈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一文,將一九二○年代中期中國軍閥混戰的一團亂麻,作剝繭抽絲的分析,主旨是運用「轉型」理論架構,把「軍閥混戰」作為中國現代轉型的一個階段處理。唐德剛教授寫這段歷史,固然把有關文獻資料翻遍,而他居然見過、訪問過至少兩個當年打得死去活來的軍閥──張學良和張發奎,這種經歷,與唐教授同輩的學者就很少有,更不要說老軍閥死後,年輕一輩的學者連見一見軍閥的可能性都沒有了。當年見過張學良、張發奎的學者也許不止唐德剛教授一人,但張學良只信任唐德剛,只願意跟唐德剛談往事,所以只有唐德剛能在他的歷史著作中將活的史料信手拈來,將往事寫得鮮活生動,也把軍閥寫得惟妙惟肖。唐德剛教授在該文中先敘述了張學良、張發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豫南之駐馬店、郾城、周家口的一場惡鬥:
奉軍以其國際馳名的「七十尊重砲」,排轟張發奎。六十餘年過去了,去年(一九九○)張漢公與筆者談及此役猶眉飛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嘗與張大王(張發奎在軍中的綽號)詳談駐馬店之戰。
數頁紙之後,唐教授則記述六十年後「談及此役猶眉飛色舞」的張學良的另一面:
據張學良將軍近年告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鄭州班師時,便決定力諫老帥,停止內戰。蓋連年殺伐,他耳濡目染,覺得內爭太無意義而老百姓受禍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鄭州登車返京時,在車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帥細詢之下,竟與之相對流涕。張學良那時不過二十七歲,還是個血性青年。這位老人的故事,觸發了他潛在的良心──他自覺不能再做個禍國殃民的青年軍閥。回到北京之後,乃泣諫老父全師出關,內戰是絕對不能再打了。
這種筆法,將人物寫得有立體感,亦將歷史的複雜性層層呈現,到收篇時唐教授對「軍閥」所作的「反思」討論,便有說服力。這時,雖然他不再提張學良,但上引張學良與家破人亡的老者相對流涕的故事,仍是他「反思」討論「軍閥」的依據之一。我們看唐教授寫來,一氣呵成,彷彿全不費力氣,但我相信,沒有他那樣得天獨厚的口述史訪問經驗,縱然有他那種才氣,也寫不出他這種生動的歷史文章。
當年「第三勢力」諸項優勢俱在,卻終於沒有建立起來。我想,這大概是唐德剛教授他老人家在文章中不時提起的,「天朝棄民」海外謀生「滿腹辛酸」的一部分。(順便說一句,這種辛酸亦是「轉型期」種種辛酸之一種。)唐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超越辛酸,在七十歲退休之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做一個倔強的單幹戶,單打獨鬥地寫晚清、民國史,在八十歲中風生病之前,完成了《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毛澤東專政始末》等著作。這些書出版後大受歡迎,居然還有盜版!唐教授當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勢力」雖然未能拔地而起,最後無疾而終,但他晚年所寫的史書在普通讀者「民國史閱讀書單」上卻恐怕是排在「第一」!
讀者的愛戴,對晚年的唐德剛教授應該是很大的安慰。我們不知道,這種安慰是否能與唐教授成功地當了一個學術團體的龍頭老大、成為「第三勢力」寨主而有的滿足感相比。我們也不知道,若是「第三勢力」申請經費、建立學術地盤成功,在現代知識生產體系、學術管理體系之下,它會不會被引導誘導或被迫走進學術象牙塔中的一個牛角尖,一小撮人在那裡自說自話,顧影自憐,書也許是一本又一本地出版,但出版之後大多沒人讀。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唐教授建立學術地盤的努力前功盡棄,付諸東流,但他不自棄,不氣餒,晚年將他的個人園地經營得繁花似錦,觀者如雲,這種成就,試問蝸居於學術牛角尖中的學者多少人能比?
「第三勢力」作為學術團體無疾而終,但它的「魂」,卻由「第三勢力」的倡議者和靈魂人物唐德剛教授帶進了他的作品中──換句話說,「第三勢力」學術取向的諸項優勢都在唐教授的民國史著作裡充分展現了出來,這大概是唐氏作品在華文世界廣受歡迎的原因之一。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將唐德剛教授的史學著作和其他歷史著作相比,便會看出唐氏作品中處處有「第三勢力」的精、氣、神──那寬闊的視野、宏偉的氣勢,和時時刻刻超越黨派之爭、門戶之見的自覺。
有人會說,海外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環境,為唐德剛教授寫出超越黨派之爭與門戶之見、具有獨立見解之歷史著作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這自然不錯。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唐教授是少數自覺地運用這一自由優勢並取得巨大成就的學者之一。學術自由、免受政治干擾之優勢本身並不保證學術事業的成功。只有像唐德剛教授那樣自覺善用自由環境,一輩子追求自由的人,才最終達到那超越黨派之爭、超越門戶之見的境界。
唐德剛教授已成一家之言的高超境界,專業的歷史學家欽敬不已自不待言,一般讀者亦能欣賞,這是唐教授自覺追求並已達到的另一境界:寫出雅俗共賞的好書,讓歷史著作幫助盡可能多的人理解過去和前人、認識當下和自己。唐德剛教授的文章享譽海內外華人世界,實在是因為他品味高,知道那雅俗共賞的境界,而且他功夫深,仔細鑽研過古今中外雅俗共賞的經典名著,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話來說,他認真「啃」過《史記》、《資治通鑒》和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終於鍛煉出一枝健筆,用精采的文字表達精采的見解,在新的時代將雅俗共賞的人文傳統發揚光大。
人文傳統在當代面臨巨大挑戰和種種危機,唐德剛教授對此有深切的認識。他早就指出,歷史著作如果不繼承「文史不分」的優良傳統,不注重文字的可讀性,則歷史會變成「枯燥無味的東西」,沒有人看的。但他老人家並不悲觀,堅信「真金不怕火煉」,因為歷史中有文學,「史以文傳」,寫得好的歷史書總會有人讀,會流傳下去。什麼樣的歷史記述是寫得好看、寫得巧妙的呢?且看唐教授對邱吉爾文字造詣的點評:
譬如《邱吉爾回憶錄》曾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定有它特別好的地方。我讀這本書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有一次邱吉爾與希特勒約期見面,由於邱吉爾講話不小心,批評希特勒,希大為生氣,取消了約會,從此以後,丘與希再也沒有見過面。這件事如果由我們來寫,可能秉筆直書「邱吉爾某年某月某日,應與希特勒在某處碰頭,後來希特勒取消約會。所以兩人一直未曾相見。」但《邱吉爾回憶錄》卻是這樣寫的:「希特勒自此以後就失去見到我的機會了!」(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 !)這個事實和「自此以後我們兩個都沒有見過面」沒有兩樣,但在《邱吉爾回憶錄》中的筆調卻一直強調"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 !",比一般人的寫法精采多了。這也就是把歷史作品的文學性加強以後,可讀性增加了。(《史學與紅學》,遠流版,頁五六。)
唐德剛教授對《史記》和《資治通鑒》,也有他自己的見解。他指出《史記》是出色的歷史著作,亦是漢代以後公認的一流的文學作品,是「文史不分」的上品。唐教授將《史記》與《資治通鑒》相比較,認為《史記》筆法是「天馬行空、大而化之」,而《資治通鑒》「遍存諸史之真,廣納百家之言」,是融會貫通的大家手筆。(《史學與紅學》,頁二七四~二七五。)我們若將唐德剛教授這些品評文字和他自己的歷史著作對照著讀,自可稍窺唐教授勤勉聰明的治學軌跡和他精湛深厚的學術功力,以及他見賢思齊的胸襟抱負。他那些廣受讀者歡迎的歷史著作,在人文傳統備受挑戰、有心人將要進行或正在進行反挑戰的今天,起著承前啟後的示範作用。
人文傳統,要有「人」有「文」。書中無「人」,史中無「文」,便是今日危機所在。時下許多專業的歷史著作和文章,不僅文字難讀,連標題也難以卒讀。這種時候,我們讀唐德剛教授既有「人」又有「文」的歷史著作,自然倍感親切。和古今中外的偉大歷史學家一樣,唐教授心中有人、目中有人、筆端有人,而且他有一枝文采斐然的彩筆,將歷史人物描繪得栩栩如生,將歷史事件敘述得萬分精采,為讀者呈現了美不勝收的歷史長卷。
若有讀者在享受閱讀好書的樂趣之餘,掩卷長思,也可體會出,那寫出處處有「人」有「文」的歷史著作的唐德剛教授,亦是一有心之人──他心繫祖國文化、人民命運,去國五十年,初衷未改。唐氏作品中,許多獨特的史識,固然是基於他扎實的史學訓練、精湛的學理研究,然而也反映了他對祖國人民命運前途的關心思考。比如說,這本《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中對現代政治制度中「制衡制」的討論和中國歷朝「內在的制衡制度」的回顧(見「『制衡制』在中國的折磨」一節,頁一八○~一八二),就有對中國古代文明的持平之論,亦有對「制衡制」在民國初年的部分實踐、終遭失敗的仔細檢討,對這一失敗對後來中國政治的巨大消極影響的中肯分析,以及「制衡制」之建立是中國政治轉型關鍵之一的評論。我們細細品味體會這段文字,既看到一個「秉筆直書」,「無徵不信」的史學高手唐德剛,也看到一個博採眾家之長、善於融會貫通的文章大家唐德剛,還看到一個對民族文化一往情深、對祖國前途無限關懷的有心人唐德剛。
有心人唐德剛,對讀者有尊敬亦有期待。他說過:
中國將來之國運原不能專靠少數聖哲的智慧,它要依靠我們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認知、好惡與取捨。(《史學與紅學》,頁四五。)
這是一段極其平實親切,而又韻味無窮的文字,它表達了唐德剛教授畢生努力撰寫有人有文的歷史著作的終極人文關懷:人類對過去的認知理解、對未來的選擇取捨,還有他從「絕大多數人」的立場出發,為「絕大多數人」寫作的自覺選擇。像他這樣親近大眾的歷史學家,受到眾多讀者的喜愛,原是極其自然的事。讀者不見得會同意他老人家的所有觀點和評論(絕大多數人的認知、好惡與取捨之事,必然是眾說紛紜的),但是捧讀唐德剛教授的書,看他以圓通的智慧、親切的口吻、充滿人情味的文字,評點古今、知人論世,真是人生一大樂事。
于仁秋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於紐約
【序者簡介】于仁秋,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碩士,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為紐約州立大學珀切斯分校歷史系教授、亞洲研究計畫主任。專業是歷史,研究領域包括美國與亞洲關係史、美國華人史,歷史專著《救國自救》(英文)獲美國亞美研究學會「優秀歷史著作獎」。愛好是文學,所寫小說、評論曾在美國《美洲華僑日報》、《世界日報∕世界周刊》及上海《小說界》等刊物上發表。長篇小說《請客》二○○七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從一九九一年起,在紐約華美協進社(由胡適、杜威等於一九二六年創辦)協助培訓中學教師,教授中國通史、中美關係史,現為該社資深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