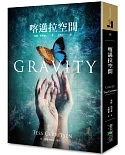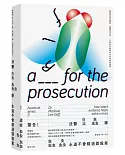導讀
多年後,當我們面對福爾摩斯
最近電視上出現一支新的球鞋廣告影片。影片中打球的全是沒人認得的尋常小鬼,甚至還跨性別的包括女生和跨國族的包括東方人,球場也是寒傖的,一般小學校的體育館或街頭水泥地鬥牛場等等;可是鄭重的、彷彿要分解時間停駐時間的背景音樂及其節奏卻是熟悉的,再看下去,就連這些小鬼的動作、表情和比賽狀態也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包括背著身子伸直右手單掌抓球準備過人的樣子,包括眼神堅定防守不讓對手越雷池一步,包括後仰在封蓋者的一線時間差和空間差隙縫中跳投出手,包括終於打入總冠軍戰對湖人的那個右手扣籃轉左手下塞挑籃經典鏡頭,包括運球急停拉回讓爵士羅素滑倒再挺挺射入壓哨取勝兩分,包括吐舌頭單臂挾球側向騰空這每兩場就會來上一次的已成註冊動作,包括在Doctor
J.建言下穿越了整座球場由罰球線起身並拉桿續航灌進擊敗多明尼克.威金斯那五十分的決定性一球──最後,在擊破拓荒者半場六記三分球「我怎麼這麼準」的氣死人聳肩畫面中,場邊赫然站著這一切一切的始作俑者麥可.喬丹,這位已然離開的籃球之神一身微服,笑吟吟的,彷彿欣慰江山有人,更像回來檢視他所創造的要有光就有光成果,是否豐饒地、春風吹又生地仍在人間被遵循並無盡地傳頌繁衍下去。
所以,已故的古生物學家古爾德是對的,這位達爾文進化論的堅定信仰者解說者跟我們講,所有的演化個別來說都有所謂的「右牆」,是會撞上無可逾越的極限,超越的真正意思其實不是取勝、壓倒、替代或一定更好,而是另闢蹊徑、是開拓、是探試其他的可能。因此,多才多藝同時還是頂尖棒球迷的古爾德建議我們,不妨好好坐下來欣賞每一種、每一次已達極限右牆的驚心動魄演出,九○年代的中外野手安祖.瓊斯和六○年代的威利.梅斯沒必要說誰比誰更好,當然要吵也可以,只是忙著吵架,你很容易錯過每一次完美的、自我完美藝術精品的神奇接殺動作內容及其特殊性、無可替代性,你損失的是最好的那一部分。
在這本書裡,始作俑者的亞瑟.柯南.道爾爵士沒像已慈眉善目老去的喬丹般袖手站球場邊,編書的人找來他昔日一篇〈側寫福爾摩斯〉的短文,讓他以板凳球員之類的身分在倒數第三章替補上陣。這或許還多提醒我們心智和身體的某一樣有意思不同,心智成果一旦被創造出來,它總是更輕靈更不被時間磨損折耗,直接放進去就行了,看不出來有長達百年歲月的接縫痕跡,更不必煩擾那些做電腦影像特效的人辛苦去修去合成。
可從另一面來說,心智上的再創造卻很可能更難欺瞞更無法造假。這裡另一處顯著的不同是,能在這本書上場的可不是隨便誰都可以,文章的最後頭附有他們每一個人的簡介,個個都是推理小說界大有來頭的人物,小說也是他們一筆一字寫出來的,絕對沒任何一篇是電腦合成的請放心。
像福爾摩斯
這裡,我們先聽個傳聞,一個因為有想像力有豐碩隱喻姑且信其為真的傳聞──據說,卓別林生前有回心血來潮跑去參加模仿卓別林大賽,結果拿了第三名。
如果也隨便抽一篇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短篇真蹟,大家蓋起名字,你猜,柯南.道爾又會排第幾名?
這麼說,不是要自打嘴巴地倒回頭去比誰寫得好,而是想提醒,在這些後來的仿作小說中,它們究竟是怎麼想福爾摩斯的?他們如何安排他的出場?如何讓諸多也熟讀福爾摩斯每一部探案的讀者相信這一樣就是那個福爾摩斯?除了簡單重抄福爾摩斯的相貌、身材描述和獵帽、菸斗這些不變行頭,以及仍讓他居住在著名的貝格街二二一號B座而外,他們認為什麼才是福爾摩斯最如假包換、最一看一聽就確定是他沒錯的特質?
依眼前這十一篇小說做統計,我們發現獲勝的是福爾摩斯那不無可疑之處的第一眼觀察∕推論法,也就是他算命先生一般在初見面時就帶著唬人意味地講出你兩、三件私密之事那一套,我們誰都曉得,福爾摩斯這招的第一位顧客或說首名受害人正是華生醫生自己,「你從阿富汗來?」
有趣的是,日後長達百年時間的反覆懷疑和挑眼下來(多疑和找人麻煩本來就是推理小說此一族裔的不可讓渡、亦無法戒除惡習),福爾摩斯這套毋庸更像江湖術士的老把戲早已拆穿大吉了,人身上的衣服、帽子、鞋子、戒指等等配件乃至於軀體上的種種痕跡從來不會只有一種原因、一種答案、一種可能,容許人如此鐵口直斷。事實上,這個漏洞並不只你我知道,就連柯南.道爾自己當時也知道,因此曾在某一探案的末尾特別安排福爾摩斯出糗的一幕;還有這十一個重寫福爾摩斯探案的推理小說老手也一定知之甚詳,我們相信他們在創造自己的偵探、真正寫自己的推理小說時絕對不會也不敢再重複這個已有定論的「錯誤」,只有在重寫福爾摩斯這特殊的遊戲時刻(如本書編者丹尼爾.史塔蕭爾所言),他們感覺擁有這個言論免責權。這應該是對的,理由之一是,這部分的犯錯責任已由柯南.道爾本人全數概括承受並清償完畢了;理由之二是,百年下來,這個漏洞常識化已無誤導的風險,遂得到特赦,完全豁免於真偽的爭辯之上,而成為一則充滿美學意味的單純神話,屬於推理族裔全體所共有的甜蜜神話。誰無聊到今天去計較神話的真偽呢?正因為超越了真假糾纏才稱之為神話,不是這樣子嗎?
然則話雖如此,這裡的比例之高仍不免讓人驚訝。我們看,在這十一篇小說中居然有超過半數的書寫者「認定」,還是得讓福爾摩斯這麼賣弄一下才像福爾摩斯,這樣的比例已遠遠超過柯南.道爾的原版。原來的福爾摩斯本尊,正如洛伊.蘿絲在〈福爾摩斯登場一百年〉一文所指出,這個裝腔作勢的唬人技倆只集中於前期的、猶輕飄飄不具真實重量的福爾摩斯,始於邂逅華生醫生來自阿富汗的問候,到和他哥哥那段你一嘴我一語比賽誰看出更多到達高峰;而當福爾摩斯的面目逐漸清晰起來,「無數生活化的小習性給了他令人驚嘆的真實性」之後,福爾摩斯不再需要用這個來證明自己是福爾摩斯了,呃,或者應該說,柯南.道爾可以放手讓福爾摩斯表現自身的才智而無需用作者的討巧手法來裝飾他了。
如此,便出現了卓別林和模仿卓別林比賽的問題了。這兩者其實是有差別的,所謂的「像」是某種既成的「形象」,集中於眾人對他最印象深刻的少數幾樁特殊表演,因此和本質無關,而是取決於集體認知的公約數,無需深刻,但非得清晰淋漓不可;也就是說,儘管卓別林不論做了什麼都還是卓別林沒錯,可不見得就符合集體認知的那個卓別林,你要像卓別林,其實只要抓緊那寥寥一、兩樣表演就夠了,但你得適切地誇張它、放大它,如此你便大有機會在模仿大賽中擊敗卓別林本人。
由此我們便看出來了,這十一個後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書寫者其實同時做兩件事,一是不慚前人地寫出一篇福爾摩斯級的精采推理短篇,另一是如何像福爾摩斯;我們讀者這一側於是也生出了兩個視角,兩重的樂趣,一是讀原來以為不可能有的福爾摩斯小說,另一是還可以欣賞它們如何擬真地、並盡可能天衣無縫地嵌入原福爾摩斯探案的各個可能縫隙中,像擬態的尺蠖或變色蜥蜴巧妙地融入甚至消失於現地現物之中。
如此,和「正常」的推理小說書寫和閱讀不盡相同,書寫的成敗有相當大一部分得取決於書寫者對原福爾摩斯小說的體認理解;同理,閱讀的樂趣多寡遂也無可避免有相當大一部分取決於我們對原福爾摩斯小說的熟稔程度,有另一個奇特的對話、另一組無關犯罪的知識之謎在此發生,你知道愈多,愈能心領神會比方說為什麼理性探案的嫌犯會跑出吸血鬼來,比方說莫里亞提教授究竟何許人也,為什麼他可以從頭到尾不露面而且還能不被逮捕歸案,甚至,你也可以從狀似不經意引述到的原探案人物姓名和往事,猜出來這樁新探案大致發生於哪個時期的福爾摩斯云云。還有,這十一篇小說中乍看最「不像」的兩篇〈福爾摩斯召喚的雙座馬車〉和〈黑暗之金〉何以會這麼寫、敢這麼寫、以及書寫者夾雜了致敬和對抗的微妙心思,還有他嘗試達成的效果──前者以類似「補遺」的方式,通過一名馬車夫的記述彷彿多年之後又搜尋到一則福爾摩斯的失落探案,而我們可能也因此想起來原福爾摩斯的探案記錄並非全然出自於華生醫生之手,柯南.道爾自己都率先試用過不同視角來呈現探案不是嗎?後者儘管有點挑戰了福爾摩斯輕蔑女性的這一通俗印象,而且也沒讓他真正一展神探身手,但原來福爾摩斯小說中本來就不乏這樣奇遇式而非解謎式的小說,而且,整個福爾摩斯探案中唯一真正擊敗過他的,不正是那個又聰明又美麗、福爾摩斯寧願用一枚寶石戒指換她一張照片的可敬女士嗎?這種寫法不是很合理而且敏銳的重現了福爾摩斯的某一側面嗎?
這部分我們只提示至此,更細膩更微妙的部分是閱讀者不容侵犯的權益,All rights reserved。保留給一個字一個字讀小說的人。
哥倫布雞蛋
好,我們再來問,這樣子既要專注寫推理小說、又要兼顧原福爾摩斯樣子的一心二用,重寫福爾摩斯探案會不會比較難呢?合理的答案是不會。這裡我們先只說一個很自然、很普遍的心理狀態:所有後柯南.道爾的小說書寫者(我們可以假設他們每個人都讀過福爾摩斯探案這部推理必修教科書)心裡都存有一、兩篇成形不成形的福爾摩斯探案,像某種讀書心得報告,差別只在於有沒有真正把它寫出來而已。
福爾摩斯已透明、人人知之甚詳到成為公產,成為每個書寫者皆可各自擁有、可使用於自身書寫的人物。
據說在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後的一次宴會裡,有某人甚不服氣哥倫布的功勳,哥倫布順手拿起一枚雞蛋(顯然是一枚煮熟的蛋、歐式早餐吃的那種),問他能不能把蛋給豎立起來,在此人屢試不成之後(當時顯然並非端午節正午時刻),哥倫布敲破蛋殼氣室一頭,簡簡單單就讓雞蛋直立於桌上。「早說可以這樣我也會。」「是啊,問題就在於你不是第一個會的人。」
把這個故事和福爾摩斯小說置放在一起,可告訴我們許多事(故事的好處便在於它總是寓意豐饒,不會只講一件事,所以在德黑蘭讀《羅麗泰》的女學者阿颯兒說小說是民主的),這裡我們特別要指出的是,即使威名赫赫到已成不可逾越高牆的福爾摩斯小說,那些徘徊牆邊瞻仰讚歎的人們,仍相當普遍流漾著某種不服氣、某種這其實我也會的心思,尤其在你比方說更熟知其創造者柯南.道爾並不出奇的人生和思想言行之後,更容易生出余生也晚、算他運氣好的浩嘆,相信這裡頭有著某部分歷史機緣甚至命運神秘作用使然(「漢王殆天授,非人力也。」)。諸如此類的桀傲心思並不必要視為幽黯不正常,它往往和人對福爾摩斯小說的真誠敬意並存而且相容,事實上,諸如此類的心思其實往往還是個可信的徵兆,代表著你對福爾摩斯小說一定程度的穿透和心領神會,你的更深一層心思已被啟動,你不僅熟知其然,而且開始可以窺見有形文字後頭的思維種種,窺見其所以然的部分。這裡,你已不僅僅是個無言的、純接受者的讀者而已,你大大跨前一步成為對話者,而拌嘴異議正是對話裡必定會有也極其必要的一部分不是嗎?
這個「早說我也會」的彆扭心思,如果我們試著把其中帶情緒的部分去除,像仔細洗去亂七八糟黏著其上的雜質,好得到其精純的核心,那它將成為「原來可以這樣子來」──一種欣喜莫名地發現,一種眼前景觀的豁然乾淨明朗,最重要也最好的,一種開始,馬上可動手實踐的開始。這對那些本來就不思不想的笨蛋一族當然殊無意義,但對於那些認真的人、焦頭爛額努力想突圍的人、滿心意志滿手力氣惟不知從何下手的人而言,他們所真正需要的就是這個,而且這樣就夠了,以下的長江大河部分他們完全可以自己來,也喜歡自己來。他們會把它每一份潛力全用出來,每一滴汁都榨乾,甚至過度使用過度開發到聲名狼藉、人人喊打的地步才不得不停下來,並焦躁等待下一個「原來可以這樣子來」。
有時候你真的會想找諸如「火種」這樣子的實物性字詞來說這原本無形無體無聲無嗅的概念揭示及其傳送,如果你看過那種光景下人們眼睛裡彷彿被反射被點著起來的熠熠火輝的話。它好像會把一整代人(某些笨蛋除外,或說唯上智下愚不移)瞬間變聰明。
當然,從概念的啟示到宛如風吹花開的具體實踐之間,一定少不了一個必要的轉換過程,不只得辛苦揮汗,還牽涉到森嚴不僥倖的專業技藝問題,並不是哥倫布雞蛋般伸個手照樣豎立起來即可。但每一回諸如此類的歷史經驗結果從無例外過的告訴我們,懂得原來可以這樣,事情就底定一大半了,總是有夠多的人、多到讓你感到意外的人一個一個冒出來。像被譽為某種繪畫終極性、集大成性技藝的拉斐爾並沒那麼難模擬難重現,畢卡索說他十二歲時就全會了;揮灑於宣紙上不容猶豫更無法修改又如此強烈個人風格的齊白石,你曉得坊間有多少亂真的膺品假畫?甚至更硬碰硬的、你身體條件不練到一百年都沒用的喬丹,廣告影片為考慮成本和效率可能用電腦來處理,但喬丹每一個曾經做過且反覆呈現於電視畫面之上的神蹟動作,每天每時都在街頭籃球場上、學校體育館裡被模擬被重現,其實就跟廣告影片講的一樣。
所以,寫一篇福爾摩斯式的小說難嗎?我們只能說會者不難,一點都不難。
米蘭.昆德拉的疑問
在小說書寫和閱讀的世界中仍有素樸的正義問題──很多時候,我們會期盼乾乾淨淨回到小說成品本身,不要受到時間裡充斥的各種雜質所干擾,能把它們從烏煙瘴氣般的人們偏見、誤讀、莫名其妙的偶然機運(包括好的和壞的)云云拯救出來,甚至連它短期的、一時的所謂「現實意義」都能予以去除,讓作品完完全全以它的內容和讀它的人直接相遇,是好是壞,是偉大是垃圾,都毫無僥倖由它的內容而非任何內容之外的因素來說話來決定。
某種程度這是做得到的,靠什麼呢?靠夠長的時間。用夠長的時間來清洗短時間的種種污染,把真正的本質給沉澱出來。
然而,敏銳且心思縝密的米蘭.昆德拉逼問到一個直指核心的問題,在他《簾幕》這本探索小說之書的一開頭不遠處──事實上,他是從音樂作品這更直接訴諸人感官感受的東西下手的。在講了他音樂家父親的一段有趣往事後,昆德拉說:「我們不妨想像:有這麼一位當代作曲家,他寫了一首奏鳴曲,不過它的形式、和弦、曲調都和貝多芬的類似。我們還可想像:這首奏鳴曲寫得精采絕倫,假設它出自貝多芬之手,那也配稱得上是他最傑出的創作。可是,儘管這個作品再如何上乘,既然它由一位當代作曲家寫成,那還是會引人訕笑,如果大家仍然對他鼓掌叫好,那頂多也是讚美他的雜燴做得出神入化而已。……什麼!我們聽貝多芬的奏鳴曲能感受到美感的愉悅,可是如果這類作品是出自我們同時代作曲家之手,我們就沒有類似的愉悅感覺了?這不是最虛偽的事還是什麼?如此看來,我們對美的感受便不是自然發生的,聽命於我們的感受性,反而是受制於對作品完成年代的認知?」
可想而知,這一問所引發的麻煩可深遠了,甚至就連我們直接的、第一時間的、理論上任何思維都尚來不及滲入的感官感受都可疑而且可嘲弄。昆德拉自己怎麼回答這討厭的問題呢?他先以這段簡單的話安撫住我們,然後用一整本書展開探索──「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在我們對藝術的欣賞過程中,歷史意識必然伴隨而生,因此這種時代錯置的事(今天寫的作品卻是貝多芬式的)『自然而然』(沒有半點虛偽成分)會被認為是可笑的、造假的、格格不入的,甚至是醜怪的。我們心中對歷史延續性的知覺如此強烈,以至於它甚至介入我們對每件藝術作品的觀感裡。」
解鈴繫鈴,昆德拉惹出來的問題由昆德拉自己去收拾,有追根究柢好習慣的人建議你直接去買《簾幕》這本書來看(坦白從寬,其實我們正是想誘惑一些人讀《簾幕》才順勢把話題帶到這裡來的,抱歉)。這裡,我們藉由昆德拉想指出的,是所謂的「歷史意識」「歷史知覺」云云,並非只存在我們後代欣賞者的心裡而已,它原本就藏放於作品之中,不全然是外加的、黏附的;它既是原作品「內容」的一部分,也是原作品成就的一部分,不管原來的創作者、書寫者本人意識到多少或甚至有沒有意識到。麥可.喬丹意識得不多,基本上這個好勝的傢伙只專注想打贏每一場球或更專注的只想投進這個球,昔日寫推理小說的柯南.道爾亦然,他也只認真的想寫篇讓他看起來比別人聰明的小說而已,就如同昆德拉指出的,「拉伯雷根本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小說家,而塞萬提斯志在對他前一代風行的奇幻文學為文加以諷刺。他們兩位誰也沒以『創始者』的地位自居。只有到了後代,小說逐漸流行起來,大家才把這個頭銜加在他們身上。小說藝術把他們看做老祖宗並不是因為他們是率先寫作小說的人(其實塞萬提斯以前就有不少小說家了),而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更清楚讓人理解這種新的動人藝術其存在的理由;因為在後繼者的眼裡,他們的作品包藏了小說藝術最重要的價值。一旦大家在一部小說裡察覺某種價值,特殊價值、美學價值,那麼後世完成的小說便可以以一段歷史的形態出現。」
這樣的價值,並非只以閱讀者領受者一己的孤獨感受呈現而已(儘管這是它最豐碩也最實在的源頭所在),而且還以它所啟示所誘發的後代一部部作品以為無可懷疑的鐵證,因此絕非純粹的溢美、錦上添花或人家說什麼我們信什麼的集體騙局。事實上,你愈是內行(對籃球、對推理或對小說藝術),愈能察知它的好和勃勃力量,察知它對一個時代的顯示力量和穿透力量,對一個時代某個核心問題或需求(不一定當時就清晰顯露眾人面前或意識之中)的回應和開展,以及因之潑灑開來的啟示力量和創造性力量。那種讓人們油然生出「原來是這樣」「原來可以這樣子來」的效應如此實在如此具體成形,因此,是它找上歷史還是歷史找上它的呢?這恐怕不是簡單能說清楚的,大概也少不了某種程度的幸與不幸成分不能太樂觀(如昆德拉所說,在一堆無價值作品的遺忘墳場裡總還躺著被低估、被誤判、被不公平遺忘的有價值作品),但從過往在在的歷史經驗我們起碼敢於如此斷言,某種埋下頭來的精純專注認真遠比希冀遠方鴻鵠將至的望風追逐更重要。最典型的實例便是那種制式左翼的書寫方式,他們急於改變時代、催趕著進入未來,結果既無心認真書寫作品本身(這是常識),其實亦無法真正專注於真實的當下(這很容易被忽略,包括他們自己),最終總甚為合理的只能寫出工具性的假作品,並甚為合理的一用或用都沒用就直接被扔進遺忘的大墳場裡去。
真正的價值和力量,由於係通過專注認真所獲取的,往往不會也不必以誇張的樣式和姿態呈現出來,像賈西亞.馬奎茲《一百年的孤寂》開頭那幾句:「多年後,奧瑞里亞諾.布恩狄亞上校面對槍斃行刑隊,將會想起父親帶他去找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麼簡單,這麼自然,但從此大半個世界的小說書寫者彷彿獲贈了一部最新型的時光穿梭機器,一扇時間的任意門,讓小說更恣意在過去和未來、預言和記憶中飛翔起來不是嗎?
未來,不管事後我們所看到的,是以劇烈改道或緩緩成形的方式完成,總有一道時間之流貫穿其中亦可回溯,這是昆德拉所說「以一段歷史的形態出現」的大致意思,因此,它出乎意料,卻又是可理解,可以和此時此刻的當下恍然大悟聯結起來。我們可不可以如此猜想,如果未來如此真實的就藏放於現在,那它只能以此時此刻真真實實的東西去把握去窺見,或更謙遜的說,去希冀它們的偶然相遇?
話說回來,這樣一本仿福爾摩斯的短篇合集,會不會如昆德拉所說被認為是可笑的、造假的、格格不入的、甚至是醜怪的呢?答案是完全不會,因為它們是帶著致敬之心的謙卑模仿或應該說重現,而不是掩人耳目的意圖竊奪那個不可重返的「偉大」。於是它簡單成為一場嘉年華,一次淋漓盡興而且高水平的化妝遊行,我們全知道這是「假的」,因此它們便栩栩如生而且只有溫暖乃至於體貼的感覺──多年後,當我們面對這個戴著福爾摩斯假面的興高采烈謀殺行列,只會把我們帶回那個我們沒能趕上的、福爾摩斯帶著華生醫生去找凶手的歷史時刻。
唐諾
Introduction by Daniel Stashower 引言
「我可以肯定地說,」亞瑟.柯南.道爾曾經指出,「優秀的短篇故事比優秀的長篇故事還要罕見。製作小型浮雕需要擁有比人物塑像更為精巧的手藝。」
這是作家的經驗之談。早幾年,在一八九一年四月時,柯南.道爾的醫師生涯跌到了谷底。在這之前不久,他放棄了他在南海區(普茲茅斯附近)還算不錯的執業成績,跑去眼科研習。舉家搬到倫敦後,這位三十一歲的醫生宣稱他已經準備好要「投入眼科領域」。
急於重振事業的柯南.道爾在上溫波街二號設了一間診所,附近的哈利街則是名醫匯集的地區。「我知道很多大醫生不太有時間做驗光服務,」他寫道。「我對這方面很在行,而且很喜歡,因此我希望能爭取到一些業務。」
但是沒有。這位年輕醫生租賃的房子包括一間診療室和一小間候客室,可是就像柯南.道爾令人同情的自白,「我很快就發現,這兩個房間都變成候客室了。」
即使如此,柯南.道爾還是每天清晨從他位在蒙特古廣場的公寓,步行大約十五分鐘到上溫波街。他在辦公桌前坐到傍晚,「耳朵清靜得就快長出繭來。」
由於此時柯南.道爾已經是個擁有相當知名度的作家,他的思緒便自然地往寫作這件事集中。他獨自坐在診療室裡,推敲著某個或許是他作家生涯中最偉大的靈感。
有一陣子,柯南.道爾幾乎將所有的精力傾注在長篇小說的寫作上,因為他早期那些不連貫的短篇作品並沒有為他的事業加分。如今,隨著經濟狀況的緊縮,他決定改變寫作方向。他靈機一動,心想若是圍繞著某個固定人物創作一系列小說,或許會帶來較好的收益。比起那些常見的傳統連載,讀者不會因為漏掉了某一篇而失去興致,這樣的作品應該會更占優勢。當然,柯南.道爾也明白,像狄更斯這種大作家寫長篇連載小說照樣會受到歡迎。只是現在的書報攤上陳列的雜誌多如牛毛,小說的閱讀人口雖然也增加不少,但並非每個讀者都有耐性或時間持續追蹤長篇故事的情節。
「在物色新小說的核心人物時,」他寫道,「我覺得,曾經在我之前的兩本小書裡現身過的夏洛克.福爾摩斯,應該非常適合擔任這一系列短篇故事的主角。」
這項決定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柯南.道爾不單擬定了極其精明的行銷決策,同時還替夏洛克.福爾摩斯找到了足以揮灑才華的最佳舞台。在已經出版的兩本福爾摩斯探案小說──《暗紅色研究》和《四個人的簽名》裡頭,這位偵探必須不時退到幕後,讓位給冗長的解說文字。至於短篇小說形式所提供的較為凝聚、緊湊的情節和節奏,顯然更能夠凸顯柯南.道爾獨具的推理敘事才華。在夏洛克.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的六十篇故事當中,有五十六篇是短篇。夏洛克.福爾摩斯擅長的是短跑,而非馬拉松。
確定目標之後,接下來柯南.道爾要做的就是找一家能接納這想法的雜誌社。十年以來,幾乎所有街角的書報攤上都固定陳列著一本叫做《珍聞》(Tit-bits)的期刊。這本刊載著各類珍奇逸聞,充滿教育性題材、趣味和小故事的雜誌,為創刊人喬治.紐因斯(George Newnes)帶來可觀的財富,也讓他乘勝追擊推出大量各類型的期刊。其中最新的《史全德》(The
Strand)雜誌,是這年一月才創刊的,由H.格林豪.史密斯(H. Greenhough Smith)擔任主編。
連著好幾個星期,柯南.道爾把他最初寫的幾篇夏洛克.福爾摩斯探案的短篇故事寄給《史全德》雜誌。經過多年,格林豪.史密斯仍然時常談起那些稿子送到他桌上的情景:「對一個正苦於沒有好文章可採用的編輯來說,那實在是天賜的佳音!他的故事布局巧妙,風格明澈清新,敘事技巧無懈可擊!至於他的筆跡,更是個性鮮明,清秀得像印刷體。」 還有一些評語(或許會被華生醫生斥為陳腔濫調),已經成為歷史。
目前探案全集的編輯群,也許不至於太過關心筆跡,但對於布局、風格和敘事技巧的關注卻和史密斯先生並無二致。因此,我很高興有機會介紹由當今最傑出的十一位犯罪作家承襲夏洛克.福爾摩斯探案傳統而完成的一系列新小說,同時也很榮幸引介三篇討論這位大偵探及其世界的文章,包括一些柯南.道爾本人的回憶片段。
是的,遊戲已經開始了。
丹尼爾.史塔蕭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