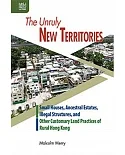前言
一再出現的慶典,一再逃避的理論
一九七零年代進入國小之後,儘管住在廟會熱絡的南瑤宮彰化媽信仰圈內,幼年期經常和家人去廟會看熱鬧的印象,像被絕緣體隔絕一般地消失了。戒嚴時期國家意識型態所打造的「慶典」,佔領了當時所有的新聞媒體和學校教育,一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師專畢業,這段期間我的學校教育裡,再也沒有台灣民間慶典的儀式、南北管音樂、廟會陣頭、勘輿、擇日、通靈者、命理學、農民曆…等等的接觸機會,這些民間慶典與相關知識體系,和台語一樣,消失在我的課本、課堂、校園裡。所有以母語為主的傳統民間信仰體系裡的知識信念與歷史記憶,被最制式化的知識控制─升學考試給排除了。我在不知不覺中離開了我所生長的民間生活作息,接受自一九七零到一九八零年代脫離台灣現實的學校教育,並沒有發現自己已成為在地信仰文化的異鄉人。一直到我接受長老教會的基督宗教信仰,成為基督徒後,才讓我真正遇到和台灣傳統信仰文化衝突的生命現場。
大半生奉獻給黨外政治運動的父親突然過世,父親的死讓我對於基督宗教和台灣民間信仰之間,對於喪禮以及喪禮所引發的死後靈魂安頓的問題,起了種種疑問。那時,發現到自己師專五年所接受的教育理論和美勞藝術的訓練,無法回應我對生死的困惑,經過天人交戰一年之後,賠了師專公費,辭去工作,到神學院研究神學,探索宗教如何解答生命價值的人生課題。
那時並沒有想到,我已經進入基督宗教所掀開的、非常切身的宗教衝突第一現場。在一九八零年代後期,對台灣現況、文化價值、台灣人前途甚為關心的長老教會,對於台灣民間信仰與台灣人的宗教觀,卻依然停留在表層的接觸與敵意的距離。一方面想建立定根於本土、關心母語與多元族群文化的信仰實踐,另一方面卻逃避面對信仰本土化的「神觀」重構,逃避探討不同神聖力量之間的差異性、以及自身被中產階級化後的信仰瓶頸。我承接了長老教會對台灣本土關心的神學實踐,繼續探索基督宗教與其他宗教的衝突與會通的問題,因為那不僅是長老教會在台灣根本的課題,也是我個人探索人生價值的所在。
從輔大的天主教武金正神父的解放神學、長老教會阮昭明老師的音樂靈修,與聖本篤隱修院靈修實踐的啟發,讓我在研究台灣民間信仰的儀式現象時,增加很多「宗教人」宗教體驗上對照的機會。尤其透過林美容老師宗教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訓練,與在輔大、芝加哥大學、與台大就學期間,對於Mircea Eliade
神聖觀的鑽研,讓我重新和被戒嚴時期學校教育封殺的台灣民間宇宙觀接觸,和母語的重新學習。更重要的,是接收到被從國小到研究所的教育遺忘多年的文化母體,再度向我發出前所未有的靈性信號。
有機會在碩士論文階段遇到深藏不露的高人,從中國大陸來台灣隱居彰化的勘輿高人吳忠信先生,和台北樹林雷晉壇黃清龍道長,他們讓我對於中國宇宙觀的形上體系,與具體道教科儀上的體現,有了可以和Mircea Eliade
的聖俗關係,互相對話的新座標,陰陽五行相生相剋的流變與相對的神聖觀,打開整體與無限的差異辯證。尤其從芝加哥大學一年半的異文化宗教學的研究環境,讓我看清被西方二手現代菁英教育支配下的台灣高等教育的貧困。對Mircea
Eliade理論的借用與理論限制的探索,讓我得以看到多少貿然套用理論對於宗教現象的扭曲。這幾十年來台灣的宗教現象研究,為何多數都只是拿來證明理論?為何現象不是挑戰理論,而只是幫理論抬轎的角色?於是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後,我選擇了藝術創作所展現出的生命意境,尤其在這個變化迅速的台灣社會,當代藝術創作如何透過民間信仰作為創作泉源,來探索「現象」和我學習過的「理論」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