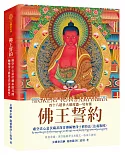序 我和我生長的地方
美麗的扎曲卡
我出生在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我的家鄉位於康巴地區的北部、安多的南部,屬於古代西藏東部六岡中的直雜岡區域,距離瑪雜岡很近。人們稱我的家鄉為扎曲卡或果洛扎曲卡,意思是「雅礱江的源頭」。
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我出生在扎曲卡一戶人家的黑帳篷裡。當時正在進行二次世界大戰,但由於我們居住的山溝清淨閉塞,所以,牧民們依然悠然自得,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戰亂紛飛。
在我的家鄉,牧民們過的是藏族人的普通遊牧生活,家家放養著犛牛、馬、騾子、綿羊和山羊等家畜。日常食物有牛奶、犛牛肉、羊肉和牧民自己加工的酥油、乳酪、優酪乳、酥酪糕、風乾肉,以及春秋兩季從地裡挖出的人參果(注:高原野生蕨麻塊根,俗稱人參果),還有從農區購買後用犛牛馱運到牧區的青稞和小麥等糧食,這些食物的營養都十分豐富。
牧民們的服裝中,冬裝通常是綿羊皮縫製的皮襖、羊羔皮縫製的皮袍、狐狸皮縫製的狐皮帽、單層或多層牛皮做靴底的牛皮藏靴,以及用氆氌做靴幫的長筒彩靴等。夏裝有比較單薄的羔羊皮袍、羊毛織品縫製的氆氌長袍、羊毛?成?子後縫製的?帽等。最讓我記憶猶新的是,那時候在我的家鄉,男人們喜歡戴一種高頂圓帽,形如倒置的蘑菇,外面套有白布,在圓柱形細帽頂上還裝飾著紅纓子或黑纓子;女人們則喜歡戴圓形羔皮帽,形狀猶如倒扣的盤子,帽檐四周採用兩種顏色的絲緞鑲邊。為了遮擋雨雪,牧民們還會用?子做成圓形的大披肩,披肩中間留有一個圓領口,上面鑲著黑布條拼成的吉祥條紋圖案,這種大披肩大多用作騎馬時的雨具。另外還有一種帶著帽子的氈衣,是女人們擠奶時穿的雨衣。
牧民們居住的黑帳篷是用粗犛牛毛織品縫製的。那些中間用木棍支撐、四周用牛毛繩牽引的黑帳篷,外型像烏龜樣子的被稱作帳房,帳房的牛毛織品是橫排拼縫的;外型是四方形的被稱作帳篷,帳篷的牛毛織品是豎排拼縫的;還有一種帳篷,兼具了上述帳房和帳篷的兩個特點。帳篷大小隨家境貧富而有不同,通常由二十根以上牛毛織品拼縫的帳篷,屬於大帳篷。牧民們遷居的時候,這種大帳篷需要用兩頭犛牛馱運。即使是小帳篷,用一頭犛牛也只能勉強馱運。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牧民們共要遷居四次。
家鄉的高山草地,四季風景如畫。每當夏季到來的時候,廣闊無邊的草原上開滿了五彩繽紛的野花,牛、羊、馬群和野犛牛、野驢互相追逐嬉戲,杜鵑鳥悠揚歡快的歌聲悅耳動聽,置身其中,彷彿來到了大自然精心造就的人間天堂。寒冷的冬天,江河湖泊都結上了堅硬的厚冰,在冰天雪地的銀色世界裡,有嬝嬝的青煙從帳篷上升起,那是牧民們正在生火化冰以獲取飲用水。就在這個外人看似艱苦的環境裡,我們牧民卻從來沒有感覺過痛苦和憂傷;相反的,我們眼望藍天淨土、呼吸清新空氣,心中總是充滿著滿足和一種莫名的興奮感。正是這種特有的生活和環境,造就了高原人與眾不同的高大身軀、一身大力氣和與生俱來的善良正直之心。
到了春天,家鄉的高山幽谷中雲霧繚繞,濛濛細雨滋養著大地萬物,成雙結對的白鶴在河邊飛舞嬉戲,一群群黃野鴨在水草地裡鳴唱不停……,這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大自然如詩美景,令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
從小到大,我最喜歡的就是家鄉草地中間那條蜿蜒流淌的小河,還有小時候我常去雅礱江邊尋找的各種各樣的小卵石……,直到今天,那段美夢般的童年生活還時常勾起我美好的回憶。
佐欽法脈
在我的記憶裡,當我三歲那年,佐欽貢珠活佛來到我家。他一進家門,爐子上的牛奶就冒了出來,這是一種吉祥的徵兆。當時他對我很好,顯出非常疼愛我的樣子,我的心中也突然產生了一種與他難捨難分的感覺,甚至緊緊抓住他的手不放。現在回想起來,這一切應該是我的前一世德秋多杰活佛與佐欽貢珠活佛同住一屋的緣分再現,也有可能是小孩子喜歡對他特別友好的新朋友。
佐欽貢珠活佛離開之後,被尊為多欽則再現化身的佐欽博珠活佛來到我家,他以讓我穿僧衣的名由,給了我一套袈裟法衣。在此之前,我與其他的牧區兒童沒有什麼差別,我們都會穿上羊皮做的小皮襖,頭上留著從一出生就沒有剪過的避邪髮。不知是受大人們的影響,還是天生具有佛緣,我喜歡和小夥伴們一起做造佛像、建廟宇、到佐欽學佛的遊戲。當我看見其他的小夥伴殺死地鼠和小鳥時,心裡就感到非常恐懼和悲傷。
七歲時,我到江瑪寺拜師學習藏文,在那裡住了整整兩年。當時,江瑪寺的名氣非常大,那裡有很多由帳篷組成的學僧營,住著許多修學造詣很高的得道高僧大德,僧人們都嚮往到那裡學佛求法。在我的家鄉,有五座寺廟是心髓派主寺佐欽寺的分支寺廟,其中包括江瑪寺。
西藏眾多大德公認為不共根本上師的土登曲培大師(注:亦被尊稱為「托嘎如意寶」,出生於扎曲卡,是一位極其偉大的上師),當時就住在江瑪寺。大師是佐欽心髓法脈的傳人,曾經做過穆日仁波切白瑪諾布的上師。大師很疼愛我這個穆日仁波切的小外甥。
我十歲的時候,舊密寧瑪派六大母寺之一的日當‧佐欽寺,派來三隊人馬接我回原寺。這三隊人馬個個都穿著華麗,就像是過大節。我們從家鄉到佐欽寺一共走了五天。當時,佐欽的百姓們都說:「這麼多年來,佐欽寺還沒有舉行過這麼大的慶祝活動呢!」
重建佐欽熙日森五明佛學院
一九八三年,當我為了佐欽寺的弘法事業而奔波時,在四川甘孜州的爐霍縣境內遭遇了車禍。當時我的傷勢非常嚴重,在長時間的昏迷中,我甚至感受到死亡次第的本覺光明展現了出來。最終,在上師本尊的加持下,我還是從死亡邊緣返回人間。儘管如此,我仍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的左腳粉碎性骨折,左臉多處被劃開了大口子,傷口流血不止,頭部左邊嚴重腦震盪,左眼從此失去視力,頃刻間我成了殘廢之人。
身體殘廢絲毫沒能改變我的心志,為了完成弘法利生大業,我拖著傷殘的軀體,依靠兩根拐杖遠赴印度。從印度回到佐欽寺後,我也沒有時間安心養傷,整天忙於處理各種繁雜的事務。不過,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車禍後,肇事者給了我一筆傷殘賠款。於是,我用這筆賠款作為基金,恢復重建了佐欽熙日森五明佛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