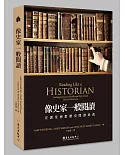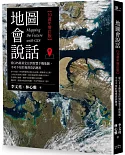作者序
民國十一年,沈曾植先生在京師溘然長逝。王國維先生曾在〈七十壽序〉中曾經如此感慨沈曾植先生之學問:「趣博而旨,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錄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而然將近一個世紀過去,王國維筆下這位繼往開來的學人,淹沒在浩瀚的歷史中,不復蹤跡。葛兆光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援引沈曾植先生生前寫下的自壽詩,感慨歷史本身驚人的遺忘:驀地黑風吹海去,世間原未有斯人。其間的悲涼,自不必言。
身為清末重臣,又是學界風雲人物,沈曾植的遺老色彩,在民國之前就以奠定,而其參與張勳復辟,乃是他一生最為人詬病之處。同樣的案例也不乏其人,諸如一向與其交往甚深的羅振玉,後來因為在抗戰中以身事敵,終致身敗名裂。而今人們提到羅振玉,也僅僅是在研究王國維時對其略作評述,其文章、其思想,已經不大有人去關注。這樣的悲劇,也只是革命時代諸多歷史悲劇中不甚引人注目的一環。
這樣的悲劇舉不勝舉。文字學大家,以《周易古史觀》開周易研究一代風氣的胡樸安先生,如今也極少有人提及。其績溪同鄉、與其交往數年的胡適先生,在近現代思想史上光芒萬丈,相較之下,胡樸安先生的名聲,極為黯淡。胡樸安先生于一九四七年去世,死在抗戰勝利之後內戰之前的淒風苦雨之中,在此之前的抗戰中,對其有知遇之恩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死在了那座孤島上,一代社會精英,在民族國家的巨大災難面前,帶著一腔的熱血與不甘,匆匆離世。
與此相隔二十餘年,一代詞學大師龍榆生先生在上海的家中離世。龍先生曾任汪偽政府治下的立法要員,又曾任偽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與周作人先生私交極為密切。一九四五年之後,還與周作人先生一起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被囚禁。這種在歷史變局中有著無數苦衷的文人學者,被後世之人唾棄為漢奸,而其學術遺產,卻極少有人問津,《龍榆生先生年譜》直到二十一世紀才姍姍來遲,得以出版,除此而外,再無其他的研究著作。龍榆生先生故去于一九六零年,斯時的政治喧囂接連不斷。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龍先生都難逃劫數,文革之後龍先生被平反,此時距離他去世,也已經過了二十餘年。
革命時代中的人物,便存在這樣或那樣一脈相承的悲劇感。而人物的隻言片語,呈現出歷史本身驚人的殘酷。一九一七年王國維致信羅振玉,說及其對於二月革命的洞見:「俄國革命事起,協商諸國內情可見。此事於東方內政外交影響甚大,以後各國國體政體均視同盟與協商之勝敗為轉移耳。」十月革命緊隨而至,王國維憂心忡忡,致信柯邵忞先生放言:「觀中國近況,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七年之後,王國維在致溥儀的〈論政學疏〉中,援引當年對柯邵忞的感慨,憤然痛陳: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思想中歷史本身的過程昭然若揭,得一斑以窺全豹。
一九四七年的胡樸安,已接近彌留之際。這位在訓詁、校勘、民俗等諸多領域都卓有建樹的學人,通常被人們認定為對社會政治歷史之演變茫茫然不知所以然的腐儒書生。然而今年來讀胡樸安先生遺著,瞭解其生平,我才恍然於此公晚年竟然如陳寅恪先生那樣滿腹心曲,難以為外人道。胡樸安一生七十年生涯,從一個傳統讀書人到一個報人,直至短期從政,最終以教育為職。而他早年參與同盟會,入南社而為中流砥柱,最終選擇金盆洗手,以著書立說了卻餘生,充分體現了其對於革命難以為繼的思慮。
一九六○年,已經走入生命晚冬的龍榆生,忽然想到要給遠在北京的老友周作人寫信。《龍榆生先生年譜》中記述:「年初,致信周作人,與知堂老人談及今年來生活之境遇,兼及思想改造之成績,二人皆以暗語示對方,頗有諷世之用意。」時隔五年,龍榆生便在文革的風暴中,猝然離世。據其生前日記所載,龍榆生先生對於紅衛兵抄家,表現一反常態,言語中之反諷躍然紙上:「紅衛兵抄家掠書,大為快事。」在日記中寫完這句話三天之後,龍榆生躺在病床上,突發心肌梗塞,與世長辭。而他在北京的故友周作人,在沒完沒了的批鬥中,在自家的小屋中,靜靜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
人物與歷史,就在這樣的順延中完成傳承。我寫下這些文字,意在反省中國百年以來悲劇種種之根源。人物在歷史中的浮沈,歷史在人物中的書寫,都是我對於歷史,尤其是這一段讓我痛感加身的中國晚近歷史,始終懷有崇敬之心和悲憫之心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