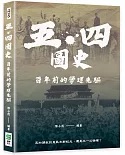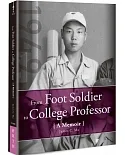推薦序
今年(2010)美東的初春雨水極多,我們驅車前往紐約,一陣陣的傾盆大雨使我們難以認路,但「交通定位器」的清晰聲音指引我們下一個路口要行駛的方向,就這樣我們來到了「漢藏學生友誼之橋」的會場。3月,我應邀在紐約參加了一次漢藏學生發起並組織的研討會;會上我認識了很多朋友,還認識了李江琳女士,李女士和我都是大會發言人。會上聽了各位發言者的精彩演講,使我非常感動,特別是李女士的發言使我意外,我原以為她作為一位漢族學者,自然會站在中國政府的立場上來談論西藏問題,而她的發言恰恰相反,沒想到她的發言會那麼條理分明、客觀事實,而且還引用了很多來自中國官方的資料,來說明西藏問題的來源和發展。看得出來她真是付出了心血,並擺脫了中國官方宣傳的枷鎖,進行認真的研究來闡述真實的歷史,這點讓我感到非常意外。
會後我主動找她,繼續交談,因而對李江琳女士有了更多的了解。得知她以前從事圖書館工作,近幾年來她研究西藏問題,特別是西藏三區1950-1959年的歷史,不難看出她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她告訴我,正在寫一本關於1959年「拉薩事件」的書,請我為這本書作序,我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
李江琳女士收集大量資料闡述50年代在三藏高原所發生事件,她的書裡也寫到了青海「平叛」的一些情況,青海是我的家鄉,是我理所應當要關心的地方。我最近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也寫了一些當時家鄉所發生的情況。我的書是根據我自己的經歷來寫的,也就是說真實地反映了親自耳聞目睹、親身經歷的情景。李女士書中是以史料為依據來證明事實的。
李江琳女士出生在共產黨的幹部家庭,從小接受共產黨的教育,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想她肯定自然而然的相信中國政府的宣傳,除了政府的宣傳,對西藏和達賴喇嘛,她可能一無所知。由於工作和生活環境的機緣,她對西藏問題產生了興趣,通過調查研究,對歷史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李女士多年的研究和確鑿的事實,使她做了一個90度的轉彎。這使我想到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先生─一個成長在國外的華僑,以愛國的熱誠跟隨毛澤東從事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他開始對毛澤東五體投地,敬佩之極,成為新中國的「御醫」他當然感到自豪。但是,多年親眼目睹毛澤東的私人生活和殘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他對毛澤東產生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並寫了那本馳名中外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一書,這本書使我們對毛澤東的生活和政治內幕有了更多的了解。在這點上李江琳女士在西藏問題上的深入研究、她所做的刻苦努力和最終產生的思想變化都有同樣的意義。
為了讓人們真正了解歷史和50年代在藏地發生的真實情況,這本書能提供來自中共官方出版的資料,以及漢藏雙方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其內容很有說服力。服務政權的宣傳和單一的紅色口號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需要面對歷史,尊重事實。真正了解西藏問題,才能知道應該怎樣解決西藏問題;中國政府如能真正反省歷史,才能癒合民族間的傷痕;真正的和諧來自於真誠。
李江琳女士的書讓我想起一件往事。80年代初,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許多冤假錯案得到平反,特赦國民黨將領,無罪釋放1958年「平叛擴大化」時被捕的藏人和蒙古人。就這樣,塔爾寺的很多高僧大德在獄中沒有圓寂的都平反回寺了,我們家族就有很多人同樣得益。我可憐的父親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和侮辱,老人往生的地點、時間我們至今也無法得知,但當時我還是感激共產黨的「平反昭雪」政策。
過了幾年後我有機會跟一位叫馬海霖的朋友(他的名字怎麼寫我記不清了)聊天,才得知這些所謂「平反昭雪」的來龍去脈,平反得來真是不易啊。馬海霖當時是青海省委統戰部的幹部,後來當過青海省伊斯蘭教協會秘書長。他告訴我,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扎喜旺徐多次到中央,要求對1958年青海地區的「平叛」平反。扎喜旺徐是藏人裡最早加入紅軍,跟紅軍長征的「紅小鬼」之一,也是第一批來青海的藏族領導之一,所以他親眼目睹了1958年青海「平叛」的情況,後來他常常要求中央對「平叛」徹底平反。馬海霖有機會跟扎喜旺徐去北京參加過一些高層級的會議。扎喜旺徐每次進京開會都會找一些中央領導人,要求他們對青海「平叛」徹底平反。扎喜旺徐每次都反映青海「平叛」的錯誤,「平叛」給當地少數民族帶來的災難,特別是對藏族同胞的摧殘傷害,「平叛」必須平反,否則黨的信譽無法恢復,工作也無法開展。馬海霖說,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對平反「平叛」都有非常大的阻力,特別是省一級領導,因為當時下命令鎮壓所謂叛亂,和參與槍戰的州縣一級領導,現在已經提升到省級了,平反「平叛」對他們的職務、利益和榮譽都有著直接的影響,所以他們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也不願意平反「平叛」。他們堅持說「平叛」是正確的,「擴大化」恐怕有過錯,最多只能承認這一點。
但扎喜旺徐堅持徹底平反「平叛」。
他下了九牛二虎之力,到處收集資料,尋找一切機會為徹底平反「平叛」做最後的努力。又有一次進京開會,一天傍晚,扎喜旺徐繞道而行,故意去「碰見」散步的鄧小平。鄧小平可能看在當年長征的藏族紅小鬼的情分上,給了他很大的面子,單獨召見談話,並點頭同意徹底平反「平叛」,以便開展民族區域落實政策的工作,恢復黨的榮譽。
扎喜旺徐回來之後,手捧鄧小平的「聖旨」,避開省裡的種種抗拒和干擾,並調來各州縣的檔案,在省委召開了一個特別的秘密會議。在戒備森嚴的情況下開啟了那些封存的檔案,馬海霖也有機會看到了這些文件,說這些檔案使他目瞪口呆,說當時的血腥鎮壓,真是對少數民族血債累累,言詞無法表達。就這樣才有了當時的平反昭雪,「平叛」被宣布無罪,一些家庭得到了一點經濟賠償,「反革命」亡靈也允許超度了。我問馬海霖那些檔案現在還能不能看到?他說除非太陽從西面出來,恐怕老百姓難能一見。馬海霖說,青海的「平叛」能夠得到平反,都是扎喜旺徐一個人的功勞。馬海霖作為我的一位回族朋友,對扎喜旺徐這位藏族老人他多麼敬佩啊!
看到李江琳女士書中提供的資料,我有同樣的感受。了解歷史不是為了增加仇恨,而是為了解真正的事實,掌握真實的歷史才能對西藏問題有正確的理解。服務政權的宣傳和無理的謾罵攻擊是站不住腳的,從50年代到現在,中國政府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口徑污蔑和謾罵達賴喇嘛,50年過去了,這未能使西藏問題得到解決,藏人心中的精神領袖也沒有被其他人來取代。我們必須了解歷史,了解在這半個多世紀在西藏三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真正了解藏人的感受,才能幫助我們跨越藏漢民族間仇視敵對的鴻溝,真正建立藏漢民族的和解和友誼。
阿嘉.洛桑圖旦
2010年3月
前言
(一)
2008年10月的一個夜晚,10點多的時候,我終於到了錫金首都崗托。
這天一大早,我從尼泊爾東南部,一個靠近邊境的小城出發,乘計程車去印度。汽車穿過平坦的山谷,翻過一道山梁,到了邊境才知道,那是個只供當地人來往的小關卡,外國人不准通行。汽車只好掉頭下山,返回山谷。到了另一處邊卡,我背著攝影包,拉著小行李箱,從一座破舊大門的這邊走到那邊,就從尼泊爾進入印度。一到那邊就遇到一輛錫金來的計程車,司機正要返回崗托。他先把我載到邊境辦公室。一名印度職員坐在老舊櫃檯後面,翻開笨重登記簿,抄下護照號碼等等,我簽上名,就算合法入境了。我走到等在樹下的計程車旁邊,把行李箱扔進車廂,裝著筆記本、答錄機、照相機、攝影機和護照的背包放在身邊,對司機說:「走吧。」那時已是下午4點多。
約兩小時後,汽車穿過印度平原邊緣,進入喜馬拉雅山區。天已全黑,車燈劃破濃濃的黑夜,照著彎曲狹窄的公路,黝黑的山上偶爾可見一簇簇燈火,或孤懸山側,或深藏谷底。天空藍得深邃,半輪月亮在山前山後忽隱忽現。我坐在司機旁邊,疲憊地望著濃黑的山影。那天我在路上顛簸了近14個小時。
錫金之行是我對西藏流亡史研究的一部分。近幾年來,每年我都從紐約飛到印度,從北方到南方,從德里到加德滿都,從達蘭薩拉到崗托,尋訪西藏難民定居點,傾聽和記錄第一代流亡藏人的人生故事。
就這樣,在喜馬拉雅山南青稞收穫的季節裡,崗托流亡藏人社區會議廳的二樓陽臺上,我這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成員的後代,坐在81歲的前僧人兼「康巴叛匪」洛桑老人面前,聽他回憶往昔。他對往事的敘述,使我對「拉薩事件」原有的認知產生了懷疑。這也是一種機緣吧,如果沒有錫金之行,就不會有這本書。
1959年3月10日,拉薩數萬民眾包圍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阻止他按照原定計畫前往西藏軍區司令部觀看文藝演出。隨後民眾集會遊行,喊出了要求解放軍撤出西藏,要求西藏獨立的口號。那天在拉薩發生的事,史稱「1959年拉薩事件」。此後,民眾與中共西藏工委、解放軍之間的敵意越來越強烈,戰爭一觸即發。在形勢高度緊張的情況下,未滿24歲的西藏政教領袖、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率家人,和噶廈政府部分主要官員,於17日深夜離開羅布林卡,經過兩周跋涉,翻越喜馬拉雅山,前往印度尋求政治庇護。
達賴喇嘛出走48小時後,駐藏解放軍和西藏工委領導下的機關民兵,出動了強大砲火,對甲波日(藥王山)、羅布林卡、布達拉宮、大昭寺、小昭寺等地點發動猛烈攻擊,將拉薩事件演變為「拉薩戰役」。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在拉薩的戰事一直被稱為「1959年西藏平叛」。
但是,無論是組織和下令「平叛」的中共和中國政府,還是後來官方或非官方的出版物,都沒有公開過1959年3月拉薩事件的詳情。3月10日那天,拉薩民眾為什麼包圍羅布林卡?噶廈政府和達賴喇嘛是否策劃了「拉薩事件」?藏人為什麼要集會抗議?在此以前發生了什麼,是什麼引發了藏人和西藏工委及解放軍的對立?解放軍又是如何「平叛」的?雙方各有多少傷亡?流血是不是真的無法避免?
「拉薩戰役」以後又發生了什麼?這些問題,中國官方或非官方的出版物從未正面回答。所謂「1959年西藏平叛」一直是只有宣傳,沒有史實;只有結論,沒有證據。
1959年3月達賴喇嘛出走事件,海內外有多個版本流傳。在中國有「民間版」和「官方版」兩個主要版本,稱之為「野史」和「正史」亦無不可。「民間版」即「讓路說」:當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是毛澤東放走的。「官方版」則是「劫持說」,這個說法首見於1959年3月28日發布的《新華社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的公報》:「這些反動分子……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儘管達賴喇嘛隨即發表聲明公開否認,但官方一直堅持這個說法。這兩個版本至今還在流傳。
我在中學就知道了「讓路說」。一位父親是「軍幹」的同學繪聲繪色地告訴我,當年,拉薩的解放軍將軍(他不知道將軍名叫譚冠三)得知達賴喇嘛「倉皇逃竄」,急電毛澤東,請示要不要把他抓回來,或者乾脆派飛機去把他炸死?同學模仿電影裡標準的「領袖姿勢」,左手叉腰,右臂豪邁地一揮:「毛主席說:『你把神抓來以後怎麼辦?讓他走吧!』」因此解放軍非但沒有追擊,而且還主動讓出一條路,達賴喇嘛因此得以順利進入印度。我似懂非懂,不明白「神」為什麼要出走,而且連毛主席都拿那位「神」沒轍,既不能抓,又不能打,只好給他讓路?但從未懷疑過這個說法。
在崗托,我把這個傳說告訴老游擊隊員洛桑。
「沒追?」洛桑老人挽起褲腿,指著膝蓋上的疤痕對我說:「當年我就是護送達賴喇嘛的後衛,跟解放軍打過好幾次仗,還受了傷。看,子彈從這邊打進來,從那邊穿出去!」 洛桑老人的敘述使我迷惑。難道達賴喇嘛的出走,是一次精心策劃的秘密行動,而非「正史」堅持的「劫持說」?我一直毫不懷疑的「讓路說」,難道只是民間傳說,而非史實?
(二)
回到紐約後,我找來各種中外資料,試圖弄清楚,1959年3月達賴喇嘛的出走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是,這些資料常常互相矛盾,有時候甚至自相矛盾。而且,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很快變成一連串問題:為什麼達賴喇嘛是1959年出走,而不是1951年或是1956年出走?為什麼拉薩民眾在1959年3月10日幾乎傾城而出,阻止達賴喇嘛去軍區司令部觀看演出,而在1954年,達賴喇嘛赴京訪問時,拉薩民眾並沒有採取如此激烈的行動?
本書試圖尋找答案的是,拉薩事件和拉薩戰役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我在研究中發現,拉薩藏人對西藏工委和解放軍的敵視,源自於1956-1958年中共在西藏周邊四省藏區的暴力土改,以及以「宗教改革」為名的宗教迫害活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早已對「總決戰」有所策劃,目標是掃除在西藏搞土改的障礙,從而找到藉口,打破「十七條協議」中「不改變西藏現狀」的約束,放手把在內地的土改等社會改造推行於西藏。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早就想「打」,而且想「大打」。
1959年3月的拉薩藏人集會抗議,給了中共西藏工委和軍區一個開打的理由。由於中共方面經過長期策劃,早已具備了「打」的條件,急欲「總決戰」,再加上當時在拉薩主持工委工作的譚冠三將軍先斬後奏,擅自下達開打命令,促使解放軍和民兵在拉薩狂轟濫炸,在藏人的聖城進行了一場慘烈大屠殺。
有關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五十年來的中外敘述,總體來說有兩個「藍本」。海外藍本主要是達賴喇嘛的兩部自傳,中國藍本主要是前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的一篇回憶文章,即1988年發表於《中國藏學》上的一篇短文,這篇短文後來擴展為〈談1959年「3月10日」事件真相〉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這兩個「藍本」都沒有講述「拉薩事件」的完整過程。1959年3月17日,達賴喇嘛離開夏宮羅布林卡之後,逃亡路上拉薩發生的事,他是後來才聽到報告的;那時他當然也不了解中共的意圖和部署,因此,達賴喇嘛自傳側重於「拉薩事件」中他所經歷的那部分。阿沛.阿旺晉美的回憶文章相當簡單,只談到3月10日那一天發生的事。但是,3月10日那天他先是在工委,後來直接去了軍區,並不了解羅布林卡裡面的情況。因此,那篇文章遠非完整的事件經過。
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比我原先想像的複雜得多。我原以為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是「西藏問題」的起點,研究之後才明白,它其實是一連串事件的終點。要理解1959年的「拉薩事件」,必須從1956年的四川藏區開始,循著事件發展的軌跡,到1957年的雲南藏區,再到1958年的甘肅和青海藏區,最後才是1959年的拉薩。只有了解了1956-1958年,周邊四省藏區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後,才能理解1959年3月10日拉薩市民的憤怒和恐慌。
為此,在講述1959年「拉薩事件」之前,本書用了相當篇幅,先對四川和青海「民主改革」的基本內容和方法,以及藏民暴動的原因,做了一些梳理。對這段歷史的研究,也使得我幾年來在印度和尼泊爾西藏難民定居點進行的許多採訪有了安放之處。當我把歷史的碎片盡可能拼成比較完整的畫面之後,那些故事就不再是支離破碎的個人回憶,它們構成了藏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那些小人物的命運,為大時代做了鮮明的注解。
他們的經歷,使得歷史不僅僅是一串事件和一堆資料的組合。
有一個使我長久迷惑的問題是,「拉薩事件」發生之前,1956-1958年,中共出動野戰軍在中國西南、西北鎮壓藏民暴動,為此不僅調動了步兵,還調動了空軍、騎兵、砲兵,事實上是一次相當規模的內戰,為什麼國際社會一無所知?直到近年來印度方面有些資料解密,才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1956年11月,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去印度參加釋迦牟尼2500年誕辰慶典,在此期間,周恩來與賀龍也訪問印度。在印度,周恩來、尼赫魯、達賴喇嘛之間分別進行了幾次會談。會談的內容一直沒有公開發表。
周恩來與尼赫魯數次秘密會談的內容,後來收錄在英文版《尼赫魯著作選輯》第二輯第36冊中。周恩來-尼赫魯1956年的會談,對1957-1959年西藏三區發生的事有很大的意義,因此,我把1956年新德里的幾方會談也作為拉薩事件的背景之一,在本書中略為講述。美國中央情報局對四水六崗衛教軍的秘密支持,已經是公開的史實,但是CIA對「拉薩事件」以及達賴喇嘛的出走是否有直接關係,本書根據最近幾年來出版的英文和藏文資料,做了一些說明。
(三)
1949年以來,中共軍隊進入城市鎮壓民眾抗爭的事件,迄今發生過兩次,一次是1959年的拉薩,另一次是1989年的北京。中共處理這兩個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處。到目前為止,對1959年拉薩事件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是因為資料有限,另一方面是因為「高度敏感」。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參考了中文、英文和藏文資料,除了很少部分的「內部資料」外,大多數中文資料是公開資料。對「拉薩戰役」的全過程,我對比了兩方參戰人員的回憶錄,盡可能對一些關鍵因素,如雙方的兵力和武器對比,兩方的決策過程,達賴喇嘛出走過程中「四水六崗衛教軍」,和CIA所起到的作用等做一些梳理。「拉薩戰役」中有多個作戰點,被砲轟的地點多達17處,但最主要的有5個,即甲波日(藥王山)、大昭寺、小昭寺、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有關這5個作戰點的具體情況,我採訪了當時在這幾個地點作戰的藏人,或者找到雙方的回憶錄加以比較,一方面是為了釐清史實,另一方面是為了對「拉薩戰役」有更全面的理解。
一個關鍵問題是,1959年的「拉薩事件」是不是「西藏上層反動分子有預謀、有計畫、有步驟」地進行的「叛亂」?迄今為止,公開和內部的資料都沒有提出支持這一結論的確鑿證據。公開資料中隱去了許多內部資料中提到的重要內容,而且不同時期的出版物中相互矛盾。各方面的資料表明,當時在拉薩發生的,是一個多種因素促成的突發事件,這個事件很快失控,在3月10日到17日這關鍵一周裡,噶廈政府基本已經癱瘓,拉薩陷於無政府狀態,達賴喇嘛也無法控制局面;一個由少數中下層官員和民眾組成的,類似於「協調小組」的臨時機構,取代了噶廈政府發布命令。在此期間,噶廈政府的三名噶倫、基巧堪布、達賴喇嘛的侍從長帕拉,以及警衛團長朋措扎西在秘密安排達賴喇嘛的逃亡,中方則秘密進行軍事部署,並且做出政治和宣傳上的安排,準備實施計畫已久的「總決戰」。
「劫持說」來源於1959年3月20日毛澤東給西藏工委的電報,指示工委對外宣傳達賴喇嘛是被劫持的;至於「讓路說」,到目前為止公開的資料中,並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證明達賴喇嘛一行是被有意放走的。《西藏平叛紀實》中對達賴喇嘛一行出走的判斷,關鍵細節與真實情況完全不符,本書對此有詳細說明。
(四)
在本書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我有幸得到多方協助和支持。在此,我謙卑地頂禮達賴喇嘛尊者,感謝尊者在周末的休息時間裡,用了近5小時的時間,對我詳細敘述那段往事。尊者的三位秘書─吉美仁增先生、才嘉先生,和丹增達拉先生,放棄了周末的休息來擔任翻譯。尊者的弟弟阿里仁波切,以及丹巴索巴先生和強巴丹增喇嘛,在訪談過程中提供了許多重要線索和細節。此後,阿里仁波切三次接受我的採訪,耐心回答了我提出的各種問題。丹巴索巴先生和西藏流亡政府前噶倫,達賴喇嘛尊者派往西藏的第一代表團成員居欽圖丹先生不在意我一次次打擾,有時只是為了核對和證實某些細節。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尊者的代表洛第嘉日先生百忙之中抽空回答了我的許多問題。
感謝阿嘉仁波切在旅行途中為本書作序。阿嘉仁波切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也是見證人。他的英文版自傳提供了重要史料,無論是對西藏歷史和西藏問題研究者,還是對西藏現代史有興趣的人來說,阿嘉仁波切的自傳都是一本不可不讀的書。
我特別感謝幾位漢藏朋友給我的幫助。格桑堅贊和帕巴次仁為我提供了許多資料。桑杰嘉在我研究的過程中,給了我不可缺少的幫助。大多數採訪由桑杰口譯,採訪之後,全部錄音必須重新翻譯整理成文字稿。有好幾個月的時間裡,桑杰一直協助我做這件繁瑣費時的工作。桑杰還為我翻譯了許多藏文資料。沒有桑杰的努力,一些歷史細節將會模糊不清。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的朋友丁一夫先生和唐丹鴻女士給了我許多建議。沒有他們的幫助,這本書會大為失色。
感謝以下受訪者告訴我他們的人生經歷:洛桑、赤列朋措、次仁卓嘎、次仁卓瑪、卓瑪諾布、格桑.嘉妥倉、洛桑貢保、洛桑益西、洛桑夏加、扎楚阿旺、東堯.嘉噶倉,還有一百多位散布在印度和尼泊爾各定居點的流亡藏人,他們的名字我無法在此一一列舉。
我知道,他們接受我的採訪,就要揭開十分沉重的回憶。講述的過程中,他們不得不再次經歷幾十年來深藏內心的痛苦。尼泊爾加瓦拉克爾西藏難民手工藝中心的扎央老人,用平靜的語氣告訴我,她和家鄉的幾個家庭怎樣從德格逃到拉薩,在拉薩無法停留,又逃往山南,在山南仍然無法安居,只好逃往尼泊爾。
每天,婦女和老弱在前面逃,青壯男子在後面掩護。夜晚降臨的時候,前面的婦女老弱停下來壘灶煮茶,等待後面掩護的男人歸來。每天,婦女們默默數著,歸來的男人少了幾個,哪家的男人沒能回來。直到最後逃入尼泊爾,只剩下了幾個男人。其他的男人都在路上被打死了。
在加德滿都大佛塔下面的一家甜茶館裡,1998年離開西藏的康巴人強巴對我講述了他的一生。從康巴暴動、大飢荒到文革,強巴經歷了在「民主改革」的名義下,一個普通藏人經歷過的所有苦難。我感謝他為我重新開啟這關閉多年的記憶大門,我能看出重新回憶和講述對他是何等痛苦。
80多歲的前僧人洛桑貢保始終無法對我詳述一個細節,即他的兩個同為僧侶的哥哥在逃亡路上被解放軍打死的經過。說到這些的時候,他眼睛泛紅,語不成聲,手裡的念珠簌簌顫抖。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我仍然能感受他的痛楚。當他把埋藏在心裡50多年的記憶交給我時,我深知這個交付的分量。
正是扎央、強巴、洛桑貢保,以及我在14個西藏難民定居點中採集的數百個普通人的故事,教會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那段歷史。對於藏民族來說,這段歷史依然活著,依然痛著。
就在我埋頭研究的時候,2008年3月,「拉薩事件」再次爆發。這是近50年來拉薩發生的第三次暴動。暴動的過程中,一名拉薩青年高喊:「我們是你們49年前殺死的人,我們又回來了!」這句話帶給我強烈的震撼。有多少中國人知道,這句話中隱含的痛楚?
這句話還告訴我們:我們不能迴避歷史。我們必須重新審視1959年的事件,換一個角度去考察,把宣傳和史實分開,弄清楚1959年3月,拉薩到底發生了什麼。否則我們永遠不會理解藏民族的傷痛,也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每隔20年左右,西藏就會出現暴動。
古人有言:「以史為鑒。」鑒,鏡也。站在歷史這面鏡子前,不僅可以看到過去和現在,也可以看到未來。我想,作為漢人,我們應該把歷史這面鏡子擦乾淨,把因宣傳、迴避、懦弱和虛幻的榮耀之需,塗抹在歷史這面鏡子上的污垢擦掉,把幾十年來沉積在史實真相之上的塵埃抹去,讓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都能看清楚,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只有做到了這些,我們才能說,我們想要辨善惡,我們能夠知對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直接面對我們內心向善的本性。
此書,就是我所做的一點小小的努力。我謙卑地以此求教於讀者,希望以此書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親歷者說出他們的經歷,留下他們的記憶,希望有更多的史實資料問世。我將非常高興地糾正此書中的錯漏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