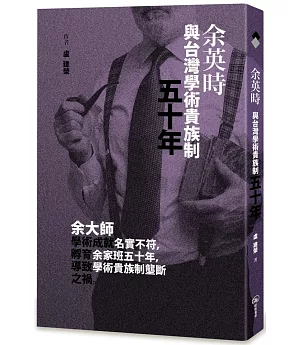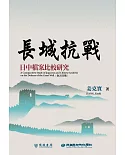增訂版序
學術自由與余英時死後地位升降
一、余大師與張友驊秘密協定破局
我從二○一○年年初開始寫批判余英時學行的文章,逐次刊於張友驊主辦的《社會/文化史集刊》上,一口氣連載六期之多吧?大至從第七期(二○一一年二月)刊到第十二期(二○一二年九月),綿延長達一年七個月。而結集成書,取名:《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四十年》,則出版於二○一二年六月,比最後一篇批文刊出,提早了三個月。每一期的出刊,都藉由聯經總經理林載爵先生寄往美國,供余英時閱讀。余先生於二○一四年,有赴台行程。事先他請台灣新聞界大老與張友驊談判。余的傳話人說,他(指余先生)晚年想清靜一點,能否請貴刊(張友驊主辦刊物)高抬貴手?張回以,只要余大師勒令門徒公開道歉,我這邊就收手如何?傳話人代傳余先生意思說,他只能管到自己,管不到門徒。張友驊說,那就是余先生不願罷戰,那請恕本刊繼續與余門玩下去囉。傳話人轉話題說,余先生今年欲回台,請問貴刊有何舉措?張友驊表示,本刊不擋人升官發財之路,余先生滯台期間本刊噤聲不語,請余先生安心返台領大獎可也。這是余門徒要頒學術大獎——「唐獎」——給其師尊前夕,兩邊人馬閉門談判的一段始末。如所周知,因為這次談判破裂,張友驊刊物從十三期起(二○一三年一月)批余聲音不斷至今,特別是前述二○一四年談判後出的第十五期(二○一五年二月)連刊八文批余,批余家班及其嘍囉,砲火益加猛烈。
二、門閥余大師孵育余家班五十年
余英時創派立宗,先後被張友驊和我定義學閥,自是要把余門家底公諸於世,以昭公信。這一學術門閥系統如下圖:
觀乎上圖,余英時生前已布局了兩代的人事,一共產生了學二代五人、學三代五人,均位據要津。余英時學派再生產能量之高,舉世無雙。這還是台灣一隅的實力,沒算上香港、大陸,以及北美的門生呢。說余英時學閥,可真是貨真價實、如假包換。余的一代弟子,佔位了中研院兩任副院長,兩任史語所所長,三任副所長,歷史學組主任一位;還外調國科會任人文處處長一位,教育部任歷史學門召集人一位,允晨出版社總編輯一位,還有,聯經出版社學術書委員會主席一位。以上全都控有學術資源分配大權。在未來的一個觀察指標是余門的學三代,是否囊括頂級權位和桂冠,便成了學術自由是否正向發展的風向標。我們且拭目以待。
三、大殺錢新祖 不理盧建榮
余死後,衣缽傳人大弟子王汎森能撐持得了門戶嗎?這是外界關心焦點。余晚年健康欠佳,二○一六和二○一八兩屆院士會議均未能出席,這兩屆史語所推薦的院士候選人,均破天荒一敗塗地,有人視之以為王汎森控制選務工作未若乃師的段數所致。其然?豈其然乎?如今大師棄世、留下眾弟子徬徨無計之中,王汎森能力挽狂瀾嗎?院士權力結構中,文學門和社會科學門逐漸崛起,史語所霸權的金字招牌還能燦爛如昔嗎?
二○一三年中國湖南長沙的《晨報周刊》記者孫魁,銜總編輯命,問我願否與余英時對談?我答以這樣的對談成局與否,須視余英時意願而定,但我估計余先生絕難紆尊降貴、願意與我平起平坐。他說,他的總編也做此推想。我這才說,我沒問題,但關鍵是余大師打死也沒有意願。此事終歸無疾而終,不出我的判斷。
想當年余英時寫了六、七萬字長稿要去痛批與其同輩知名學者錢新祖(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芝加哥大學副教授),他的博論:明代思想家焦竑。余大師依江湖規矩先禮後兵,派門下弟子陳弱水向錢某弟子江燦騰(時讀台大博士班,上錢新祖的課,江君日後會在中國明清佛教史,台灣佛道教史兩領域,名重一方)傳話,說要與錢氏論學。錢氏聞訊,不疑有他,表示歡迎。(難不成要反對不成?)果然余批錢長文不久便在美國某漢學雜誌刊出。余不與錢纏辯,直截了斷只明揭錢氏在引證資料上的犯錯,或抄錯,或誤解原文等等基礎工作。最後結論是,錢兄所營造的漂亮論點,乃建立在掌握不確的材料認知上。錢氏讀畢一時無法應答,過了若干年才回應,但因錯過時機,傷害已造成。錢氏在美國失業,最後流落到返台先後任職於清華、台大、以及文化大學。錢氏雖與余氏同輩,卻不足威脅余氏的學術霸業。
以上余先生設局讓錢新祖無還手之力、只能挨打。我著書批余,比之當年余批錢,規模還大,費時(在學報上連載年餘)更長,使余先生至死未有一字辯解。我讀余著《回憶錄》(台北:允晨,2018年11月),看到余言及其作,諸如漢晉新思潮(頁195-196)、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頁185-186)、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想(頁193)、東漢先死觀(頁196),以及漢代中國的貿易與擴張(頁108)等五種書文,這些在我批余書中分別出現在卷一、卷二、卷三,以及卷四,但余大師回憶起來,完全無動於衷,也不願趁機駁斥我一番。換言之,他當成不存在,或是不願再事面對,也是有可能。說起來,錢新祖有回應余先生之質疑,雖然遲了好多年。相形之下,余先生堅持不回應我的質疑和問難,明顯是高姿態,自持身份,卻毀了他身為大師應有的風度。以上兩場學術爭議事件,都未為華文世界的學術對話立下楷模。真是可惜。
其實,余英時絕不許人對他有異見。像清華大學中文系楊儒賓、林聰舜兩教授,都因發出異聲,被余在私底下叫去辱罵。汪榮祖原在《中國時報.副刊》有「學林漫步」專欄,只因發表與余不同看法,余立命《中國時報》關閉汪某專欄,否則概不供稿。這些都是余大師有欠風範的著例。
四、學術業績鴉鴉烏
十年前我與余先生論學觀人的書,如今讀來大抵多能成立。余英時終極關懷的兩說:其一,儒學的現代化,以及其二,中國文化宇宙無敵,如今看來愈發如昨日黃花,盡化為春泥矣。他倚為拿手好戲的鉅變時代及其新思潮,即漢晉之際的道家壓倒儒家風起、明清之際理學內部朱學勝王學,從而催生出智識主義的考據學盛,以及清末民初的引西學反中學傳統等,我評他因材料掌握失了分寸(即不知當下遺跡,高於後設史著),以及學術裝備落伍,以致所得觀點難有說服力。這使他一生致力所在的藩籬盡失、任對手長驅直入而全線潰敗。此其一。
第二,他自詡的獨特研究風格:會通中西上,犯了引用西方學術理念的誤用、濫用,甚至挪用的失格之舉。譬如對孔恩「典範」之說老是招式用老,胡攀亂引說自家紅學研究已至典範轉移的高度。再如為捧師門師長的顧頡剛和洪業,盛讚兩人業績臻至典範轉移。須知近代物理學從牛頓假說變成愛因斯坦假說,人類花了二百年,才產生典範轉移。而歷史學,在顧頡剛到余英時的兩次典範轉移,居然那麼頻密地發生在燕京大學一對師徒身上。世間有如此輕易的典範轉移?抑有進者,還比附顧氏史學達到傅柯(M.
Foucault)「知識考掘」的層級。又如他稱誦師兄嚴耕望一生成就堪比布勞岱(E. Braudel)於《菲力二世及其地中海世界》所治學。這些都暴露了余先生治學上的短板,以及對西方史壇認知有誤。人家是一門忠烈,然則余英時的師門,老師和師兄全位列當代史界百年萬神殿中人物。如此推崇自家師門其背後潛台辭,莫非在自高余家班了得?
第三,有三本西洋史學名著,余大師其理解有誤;其一,誇大了、且理論化了瑞士布克哈特《文藝復興史》中「自覺」一辭,在錯誤移植、並無限上綱到研治中國新思潮史上,徒然只有添堵的份,卻無助釐清問題。其二,法國布洛赫《奇異的戰敗》,主要在講法國一戰後文化上心靈結構有失、致為德國所乘,而不是從物質層面在談論德法勝敗之機的庸俗看法。其三,英國彼得.柏克(Peter
Burke)於《十六至十八世紀歐洲大眾文化》一書中,修正人類學大、小傳統之說,主張「文化下沉說,不能成立」,余氏理解錯誤,反主張用「文化下沉說」來詮釋兩漢循吏文化作為。
最後,在他留洋的五○、六○年代,以迄爾後滯留西方、出道四十年裡,他對西方史學不僅陌生,而且霧裡看花不知所以。他坐視哈佛歷史系思想史重鎮的斯圖亞特.休斯,以及任職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卡耳.蕭爾斯基,不予理會,浪費時間去唸克靈烏的歷史哲學,真荒天下之大唐。這錯失了寶貴提升自家思想史研究境界的機會。跟他同時且同事的史學大師他都擦身而過,殊為可惜。這點,他比起輩分略高的蕭公權和何炳棣來,遜色多矣。蕭何倆都在英文世界遺下鉅著或傑作,反觀余之英文博論迄未出版。更糟的是,博論後唯一英文專書的《漢代中外交通》(以後有所改名),論點是不成立的,即以它是為入職哈佛大學的一塊敲門磚而論,開了學術為取悅學閥的劣行,更是不能原諒,遑論學術業績了。
五、無知於當代百年唯有陳寅恪談得上典範轉移
虧得余先生將孔恩「典範轉移」之說老掛嘴邊,卻不知他所研究的陳寅恪,才是當代中國百年史學唯一做到「典範轉移」的實踐者與紀錄保持人。余氏不去探訪陳寅恪史學造詣之極致,卻汲汲營營陳寅恪是否有過起念赴台灣,以及他是否反共這麼不甚重要政治立場表白的鎖事。他不僅與西方史學大師錯失交臂,也未真正估值陳寅恪的無價之寶所在。一個民國陳寅恪晚年一件是否起心動念出亡台灣事的細節,如此癡迷不已,已夠嫌多了,想不到他更熱衷追索清初方以智晚節一次不夠,竟至四次之多,同一書名進行到四次改易的瘋狂地步。最後定版說此事真相難定。不過是方以智究竟有否降清這樣的政治立場問題,需要如此大動干戈?同時,他對號稱拿手的學術史和思想史絕活,卻在喪失作者原稿情況下,錯把抄稿手、雕版出版家和編輯的改編、甚或摻水的成書,當成作者原稿,在作解碼作者思想的工作。一個從西方七○年代始倡行的「文本」(text)(按:余大師最早引進台灣,譯成「文件」)理念和用辭,由於掌握失準,以致一著錯滿盤輸。假如用弈棋來比喻余先生所從事的研究活動的話,說余英時一生成就差陳寅恪一大截,還是抬舉他了,百年來史界餘子碌碌,余英時亦不過側身其中之一位,大家全輸給陳大師,其餘名家均屬差一大截的層級,彼此之間幾無高下可言。余大師也不用為此難過了。
六、在學術的社會實踐道路上敗下陣來
至如余英時一生行誼,可用以下十九個字形容:骨子裡追逐權與利,卻偽飾成「休休有容」的名士。這之中最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是一九九七年由他掛名的一家台灣高中歷史課本的「編審」,只為貪圖領取美金三千元。從一九七○年代到二○○○年代,他的五種論文集,不斷因增一兩文而易名,只為騙取消費者荷包中錢物,與出版商合謀並樂此不疲。光《歷史與思想》一書內中充斥錯誤資訊,死不修改,從一九七六年出版,到二○○○年,已賣出五萬餘冊,之後二十年,恐怕又多賣少說二萬冊吧。早已誤盡每代年輕人不知凡幾,卻置之不理。從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七年,余氏不當竊佔藝文人士表演舞台——即兩大報副刊——供其表演,不良媒體奉獨裁者諭,非把余氏捧成文化明星不可,致令副刊園地因登學術文章,使絕大多數讀者倒盡胃口,因此少看了許多美文妙詩。這是不正常威權時代,余先生與傳媒共謀污染副刊清純藝文天地。迨獨裁者斃命,副刊才恢復常態,不再任由余氏難懂的學術文章去虐待一般讀者的眼睛和心靈。余英時仗勢欺人夠夠如此,他不僅從未反省,還自以為打敗天下小說家、散文家,以及詩人,而暗自竊喜呢。他不知這是獨裁賞他的特權。反觀當代兩位學者之卓越演出如右:大思想家漢娜.鄂蘭應雜誌社之邀去以色列採訪納粹殺人魔受審,因而出版:《邪惡的凡庸》一書,大歷史家羅伯.達頓(Robert
Darton)採訪柏林牆倒事件、而出版《柏林牆倒紀實》,都為大時代留下啟人深省的作品。吾人倘將以上兩作置於他們學術著作堆中,一點都沒違和感。西方這兩位學者都無愧於他們的學術志業及社會實踐。相形之下,余大師利用台灣報媒刊載其學術作品,諸如陳寅恪晚年心曲、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以及東漢生死觀等等學術大文,徒留難登大雅之堂的劣作。這比起西方「志於道」的學者,相差何啻霄壤?
學術的終歸學術,政治的讓政客去忙去。余英時享大名於台灣不正常的強人政治時代,他扈從強人立下大功,強人報以供其文化舞台使盡情表演。余大師玩昏頭,把寶貴光陰浪擲、沒能遺下傳世作品,卻一直自我吹眠說我是最棒的,加上一眾弟子阿諛不斷,便誤以為自己是當世史壇一哥了。在時代逐漸恢復正軌,他的史著文本益發供人檢視,他一身油脂白粉終將卸下,而露出本然面貌來。之前,余家班視我的批評,為不入流的失心瘋、陰謀論,以及不順人生的報復等說,用以安慰師尊,確實收效一時。如今師尊駕鶴西歸,還妄想用此等話語騙盡學界同行,在邊際效用遞減情勢下,應可休矣。
盧建榮序於景美寓所
二○二一年八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