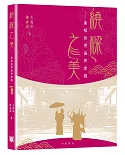歷史像一堆灰燼
但灰燼深處還有餘溫
我們不是翻扒已經冷靜的灰燼
而是手伸進灰燼
去觸摸那個餘溫。。。。。。
世界上很多偉大的民族都有一種高雅精緻的表演藝術,深刻地表現出那個民族的精神與心聲。希臘人有悲劇,義大利人有歌劇,俄國人有芭蕾,英國人有莎士比亞戲劇。這些雅樂往往是他們民族的驕傲與自信的源泉。
我們中國人的雅樂又是什麼呢?
借助歷史鏡頭,我們可以記錄發生的事情。但我們能否知道,在數百年以前,我們的祖先曾經看到過什麼,聽到過什麼?我們能否走進他們的精神世界。
中國國家博物館曾舉行過一場特殊的展覽,這次展覽的主角並不是參與展出的兩千多件珍貴文物。它們看不見、摸不著。但它們曾經是我們祖先生活的一部分,並經歷時間和社會轉折的洗禮,保存了下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它命名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就在6年以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全世界範圍遴選第一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來自中國的一種傳統戲曲——昆曲,出人意料地全票當選。
從2001年開始,沉寂已久的昆曲慢慢進入了大眾的視野。
2004年冬天,新版全本《長生殿》,由江蘇省蘇州昆劇院排演的這部《長生殿》,總投資將近800萬元,同時請來了獲得過奧斯卡獎的葉錦添擔任美術設計。臺灣儒商陳啟德的巨額投資,以及昆曲界以外的頂尖藝術家的加盟,這一切,在2001年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江蘇省昆劇院排演的新版《桃花扇》,創作陣容同樣十分強大,由中國話劇界新銳女導演田沁鑫執導,同時吸引了中日韓三方眾多的藝術界頂尖級人物。
《1699.桃花扇》,這樣一種命名方式,顯示出演創人員重新回到歷史現場的企圖;而對於普通觀眾來說,突然在他們眼前亮相的昆曲,也仿佛來自一個古老的夢境。
2006年,白先勇帶著他的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國西海岸連演12場,場場爆滿。美國觀眾驚歎于昆曲不可思議的優雅和美麗。戲劇評論家,甚至把這次巡演和1930年梅蘭芳轟動美國東西兩岸的巡演相提並論。
人們忍不住驚歎,又解不開心中的謎團,為什麼在21世紀的今天,古老的昆曲依然能有這麼大的魅力?
余秋雨:(昆曲)它是一種美麗的輝煌,它是一種讓人懷念的過去,懷念它的時候,讓我們感到一種充實和驕傲。
昆曲究竟是什麼?六百年的昆曲史又經歷了怎樣的百轉千回?是什麼賦予它穿越時間的力量?昆曲又沉澱著我們怎樣的民族審美文化?
這是一個有著兩千五百年歷史的古城---蘇州,600多年前,昆曲就誕生在蘇州的昆山地區,並因此而得名。
蘇州的七里山塘街,是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在做蘇州刺史時主持修建的,千百年來一直是姑蘇繁華的縮影。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話褒揚的,顯然不只是蘇州的美麗景色。古往今來,蘇州人的生活,似乎已經超出了普通中國人的想像。如果非要找一個地方來比擬的話,那麼只有天堂了。
明朝中後期,蘇州是中國東南首屈一指的大都會。這裡交通發達,商旅往來頻繁,其繁華程度超過了當時的兩個都城北京和南京。這裡的地價是全國最高的,這裡向中央政府交納的糧食和稅銀,居然占到了全國的十分之一。不僅如此,皇帝的吃、穿、用,幾乎都由這裡提供。蘇州,給出了當年中國人生活的最高標準。
鄭培凱:明朝中葉之後,沿著中國的長江中下游跟大運河,這麼一個十字架構,還有中國東南沿海經濟發展得很快,經濟發展很快,社會也發生了變化,所以商品經濟的蓬勃使得商人階層,整個非常地蓬勃起來,這個造就了許多民間的藝術,跟上層的精英藝術有一個交流,這個交流的最有趣的場域就是戲曲。
那時,聽昆曲、唱昆曲是中國人最時尚、最風靡的生活方式。每到中秋,當一年一度的虎丘山曲會舉行的時候,整個蘇州城都會陷入狂歡的海洋。
余秋雨:當年在虎丘山曲會,萬人空巷地去看昆曲,我說只有古希臘的大元劇場的悲劇演出,才曾經出現過這種景象,否則我很難比較哪個民族的戲劇演出,曾經出現過如此如火如荼的狂熱場面。
虎丘山曲會,不過是明清兩百多年間昆曲流行的一個縮影。這迤邐悠揚的曲聲從江南發端,傳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從威嚴高聳的紫禁城,到雲南、廣西的邊陲小鎮。
歐洲傳教士利瑪竇,在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利瑪竇身後是正在崛起的歐洲大陸,不過,中國才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在利瑪竇眼中:凡是人們為了維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東西,無論是衣食用品還是奇巧物與奢侈品,這個王國的境內都有豐富的出產。
比財富更令利瑪竇驚奇的,是中國人對於財富的態度。財富似乎沒有給中國人帶來擴張和征服的野心。他們彬彬有禮,富於文化修養,懂得享受生活,並把生活的每個細節都提升到藝術的高度。
《利瑪竇中國劄記》一書中有著這樣的記載:“我相信,這個民族是太愛好戲曲表演了。這個國家有很多年輕人從事這種活動。戲班的旅程遍佈全國各地,他們忙於公眾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會都要雇傭這些戲班。客人們一邊吃喝一邊看戲,十分愜意,以致宴會有時要長達十個小時,戲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會結束。”
利瑪竇看到的正是昆曲,他強烈感受到了中國人對這種舞臺藝術的熱愛。
利瑪竇來自歌劇的故鄉義大利,巧合的是,此時歌劇也正在義大利興起,不過和昆曲相比,它的黃金時代要滯後差不多兩百年。
那是一段遙遠而輝煌的歷史,也是一段幾乎被人遺忘的歷史。
和昆曲一起被遺忘的,是一種曾經屬於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一種精神世界的滿足與安寧。
時間進入21世紀,古老的戲劇文化是否已經喪失了生命力?作為一種傳統文化,昆曲還能否融入現代人的生活?
陳丹青:我在倫敦的郊外挺遠的一個地方,是一個老的貴族的莊園,我親眼看到戲劇學院的學生在排練莎士比亞(戲劇),就穿牛仔褲,平常的衣服,在一個湖邊,在排練,一句一句在對臺詞。所以我發現他們的傳統戲劇,它可能地盤縮小了,但是它絕對在,還有活力,一代一代年輕人還在演,還在看。這是歐洲的情況。中國是這樣子,中國一路唐宋元明清下來,文脈沒有段,但是到了19世紀中期,中國經歷一個文化的斷層,這個斷層到了20世紀就完全裂開了,中國開始了一個非常急驟的、西化的、現代化的一個過程。
陳丹青,畫家,1980年,陳丹青便以油畫《西藏組畫》蜚聲海內外。他長期身處西方當代藝術中心紐約,並於2000年回國定居。近年來,陳丹青發表了大量關於中西文化環境比較的文章和言論。
陳丹青:我是一個上海的孩子,上海是一個被殖民了上百年的一個城市,有很多租界,所以我小時候的一個景觀,我一睜開眼睛,開始有記憶的時候,這個景觀其實就是一個西化的景觀,西式的弄堂,西式的洋房,小孩子第一印象非常重要,那麼,到了真的西方以後,第一我就失落了,我就發現我們中國那點西化是非常表層的,非常有限的。所以你在失落當中,你立刻會尋找自己,無論是自尊,還是自卑,你會尋找自己。
樓宇烈:在過去所謂落後的東方世界的民族,在經濟、政治上面獲得獨立以後,都開始有一個文化上面的自覺,所以從80年代開始,在中國其實也出現了一種文化的自覺,就是我們的文化是不是一無是處,在世界的這樣的一個文化的大家庭裡邊,是不是它只能被淘汰,還是它也是這個大家庭裡面一個燦爛的成果。
樓宇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與昆曲結緣已近半個世紀。1961年,剛剛大學畢業的樓宇烈就加入了北京昆曲研習社。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長期擔任研習社的負責人。2003年,樓宇烈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京昆古琴研究所”。
就在一百年前,當昆曲最為衰弱的時候,正是蔡元培、吳梅這樣的大教育家和國學大師,把戲曲教育引入北京大學,在大學講堂裡唱起了昆曲,維繫著昆曲的一線生機。
昆曲似乎總是受到文化人的偏愛,他們敏銳地關注著昆曲的興衰,並以自己的身體力行守護著這支文化血脈。
周秦,蘇州大學教授,自幼學習昆曲,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下鄉插隊期間,仍然是曲不離口笛不離手。每年秋天,周秦為本科四年級的學生開設昆曲藝術選修課,一大批昆曲愛好者慕名而來。
周秦:(昆曲)就像蘇州園林裡的那個池塘那樣,看起來是一潭死水,但是裡面魚能活,荷花能長出來,為什麼呢,這裡面有一個結構,在水池的裡面有很深的井,這個井一直通著地下水,這個池塘的水通著太湖,通著長江和大海。昆曲還靠著自己的文化的因素支撐著,還綿綿若存。
今天的蘇州,是一座散發著時代氣息的現代都市,它是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一個縮影。但同時,蘇州仍然完好地保存著幾百年以前的古樸風貌,城內是不許造六層以上建築的,城中最高的還是始建於三國時期的北寺塔。傳統與現代,和諧共存於這座千年的古城。
2002年,蘇州著名的古典園林網師園附近,多出了一個叫“南石皮記”的私家園林。
南石皮記的主人是蘇州國畫院高級畫師葉放。葉放的童年是在外曾祖父家的畢園裡度過的。在那裡,他有了對昆曲的最初記憶。
現在,葉放時常會邀請三五好友在南石皮記小聚,今天的客人是蘇州大學的周秦老師和蘇州昆劇院的毛偉志。
葉放:我們現在讓文化回歸到我們生活中來,跟著我們的生活走,這是一個多麼好的想法。
周秦:只能在高強封閉的園林裡面這樣做。
葉放:我們這個音樂是可以大家分享的,飄過去飄過牆的,雖然說沒有張生來翻牆,但是音樂是可以翻牆的。
一處精緻的園林,三五個知己,幾杯清茶,從容而悠閒。
悠揚的笛聲穿越了百年的時光,早已遠去的歲月又近在眼前,觸手可及。
明清兩朝,中國先後出了204個狀元,其中有34個是蘇州人。無論是蘇州園林,還是誕生在園林之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地刻上了文人的烙印。
當年,園林的主人很會享受生活。他們從官場上退下來,在最好的地方買一塊地,砌一道高牆,把塵世隔開,在裡面經營自己的園林。
朱棟霖:從明朝開始,由於江南文化的崛起,由於蘇州、杭州地位的攀升,江南文化領導中國文化潮流,無論在書法方面在繪畫方面,在文學方面戲曲方面,就是明清兩代,蘇州和蘇州周圍的文人的文化和審美趣味,成為領導中國文化的潮流。
周育德:昆山腔後來它能發展成昆曲,它那種優雅的品格,和它的原生地的這種文化氛圍有關。
廖奔:要有文化品位,它就像當時的文人去琢磨,去經營一座蘇州園林,經營一個庭院那樣子,它需要一種錦心繡口的東西,比如說,他經營一個庭院,他會去琢磨,這個地方我是不是掛一幅字比較好,這個地方放一塊奇石比較好,這個地方放一個盆景比較好,他要不斷地琢磨。對昆曲他也是這麼琢磨的。
昆山腔形成後不久,一些民間的音樂家就應邀來到園林的主人家,擔當曲師。他們陪同主人和他們的賓客,在園林中吟詩、作畫、度曲。
昆山腔的音樂主要以宋詞的音樂為基礎,同時融合了江南的民歌小調。昆曲運用的曲牌達到兩千多種,十分豐富、富於變化。唱詞則主要來自當時文人的創作。同樣也沿襲了唐詩宋詞的創作傳統,用詩一樣的語言去抒發情感。
文人們生活的園林,自然也就成為眾多昆曲作品的故事場景。
這是昆曲的代表作《牡丹亭》中的一折“遊園”。《牡丹亭》講述的不朽愛情故事正是從女主人公杜麗娘春日遊園開始的。
“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劇作家們用飽含深情的筆觸寫下了這些將園林景致與人物情感融為一體的詩句。幾百年來,不知多少人為此神傷,為此落淚。
在昆曲《長生殿》中,最能體現唐明皇和楊貴妃恩愛的一場戲也發生在皇家園林。
蔡正仁:《長生殿》驚變(一折)裡,它前半段是描寫唐明皇和楊貴妃在御花園當中兩個人遊覽,咱們來一邊喝酒一邊欣賞御花園的風景,然後皇帝今天他有個意思,我今天要把楊貴妃灌醉,我要看看她的醉態是什麼樣的,那麼皇帝就發現,就是楊貴妃喝著喝著有點醉態了,越看越是覺得,越是醉越是美,越漂亮。
王芳:在這個《長生殿》故事中,唐明皇跟楊貴妃的愛情是純真的,(楊貴妃有)天生的一種散發出來的,一種靚麗的美麗的東西,在所愛的人的身邊,她是想把自己最美的東西展現出來的。
蔡正仁:唐明皇唱了一個石榴花這個曲牌,(唱:不勞你玉纖纖,高捧禮儀煩),你想這個曲子多美啊。
樓宇烈:(昆曲)它已經把以前我們文化發展,文學發展中的積澱起來的詩詞裡面的精華,都吸引進去了。它的曲譜那是反復地磨練,它的音樂性,也可以用一個最優美吧。
園林中的春夏秋冬、風花雪月,一一化入曲中,由此導演出許多悲歡離合的人生故事。難怪蘇州人常說,園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聽的園林。
園林和昆曲,一起構成了中國人幾百年來共同擁有的一處精神家園。
劉歡:我們現在接受的(昆曲)面比較窄的原因,實在是因為整體的社會節奏與它脫節得太厲害了。首先一點,我們現在要聽一首流行歌,三分鐘到五分鐘解決問題,我怎麼會還想有時間坐下來三個小時去看一個東西,現代的人沒有這樣的時間。
田沁鑫:我們這次提倡一種生活方式叫使生活節奏慢下來,是不是我們文明程度高了之後。比如說我們欣賞昆曲,比如說我們欣賞到了一種活著的博物館藝術,我們欣賞到了我們嚮往著的屬於我們這個民族身上,本來漢民族身上,應該有的這樣一種從容,應該有的這樣一種滋味。就是比較從容,比較優雅,談個情說個愛什麼的,很人性化。
田沁鑫:如果說這個國家整體的文明程度高,實際上是反映在這個國家的人臉上的精神氣質。
劉歡:只能是現在把這個東西擺在這裡讓還欣賞這部分人,或可以領略這部分魅力的這些人去欣賞它。
陳丹青:我有興趣瞭解,今天的年輕人,他在戀愛中,他在青春期,他在看《桃花扇》,在看《西廂記》的時候,他在內容上,他有沒有可以分享的東西?關於(昆曲)這個話題,不要完全停留在這是傳統,這是經典,這是文化,我覺得這還不夠。
2006年4月,昆劇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大學的百年講堂,上演了三天九個小時的全本大戲。青年學子趨之若鶩。
白先勇,著名華裔作家。2002年起,他作為青春版《牡丹亭》的製作人,竭力在全國各地高校推廣昆曲,被人們稱作昆曲義工。今天,白先勇講座的主題是“古典美學與現代意識”。
學生:感覺舞臺的設計,我看到舞臺的設計給我的感覺就是一種現代藝術作品,我覺得在簡潔方面和古典融合了。但是不是精神內核還是一樣呢?
白先勇:所以說我們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們利用現代,但決不濫用現代。這是我們一個大原則。
白先勇定義的青春版《牡丹亭》,是一場文化行動,它重新培養起了一批熱愛昆曲的年輕演員和年輕觀眾。
400多年前的故事正在今天的舞臺上上演。對今天的觀眾來說,這樣的演出也許是雙重意義的。一場是柳夢梅和杜麗娘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而另一場,則是一個民族對於美的忠誠守護。
2004年秋天,蘇州的南石皮記曾經雲集過全球30多個國家美術館的館長。他們剛剛參加完第5屆上海雙年展,希望實地感受一下中國傳統文人的生活,主辦方就選擇了南石皮記,並在這裡上演了《牡丹亭》裡的“驚夢”。
陳丹青:就是夢遊的感覺。因為文化需要親歷,所謂親歷就是你必須在那個情境當中,你必須在庭園裡,你在湖邊,在樓榭回廊當中走。你會有想像力,一個回顧性的想像力,
廖奔:我走到那個小小庭園的亭子上,邊上的曲巷欄杆啊,小橋流水啊,各種盆景點綴著,浮想聯翩,我會想到,這裡會不會有幾個文人在這裡一邊品茶,一邊拍曲,昆曲的聲腔就會響起來。在那個氛圍裡面,它這種曲調就恰是當時可以感覺到的一種天籟。
樓宇烈:因為我們有這樣一種生活的樣式,這種生活的情趣,生活的追求、理念,所以才形成我們這樣一些文化,那麼反過來這些文化又會影響我們生活的情趣,生活的樣式,我們的價值的觀念。
余秋雨:我們在看這種中國文化史的每一部分史的時候,看著看著最後要解的謎是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這個群體是誰,我們為什麼愛這些東西愛了這麼久,愛它實際上也是自我實現,為什麼是自我實現,這個原因就是昆曲一定有我們是誰的秘密所在。
幾百年的時光,就這樣凝固在園林的一磚一瓦上。幾百年的時光,就這樣流動在昆曲的一唱一和中。
歷史,就是過去和未來無窮盡的對話。
讓我們一起去追溯昆曲六百年的發展歷程,去追溯那些日漸遙遠的人和事,去追溯一個民族對美的夢想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