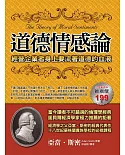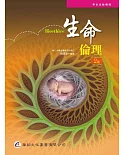導讀
王超華老師(中研院近史所)
一、生平簡介
蔡元培於晚清甲午之年(一八九四)點翰林院編修,戊戌變法(一八九八)失敗後返鄉辦學,並轉赴上海參加反滿革命,一九○七年赴德國留學,至辛亥革命後回國,充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此後數年間再次三次出國,留德、留法,直至一九一六年底應教育部之邀就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在校期間力行改革,延聘陳獨秀與胡適等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又積極推動學生社團活動,終至發生一九一九年北大學生領導的五四抗議遊行。此後因與北洋軍閥「不合作」,他再度長期滯留國外。一九二六年年底返國後,積極參與國民黨北伐(後期)、清黨、建立南京國民政府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此後致力於建立中央研究院等學術機構,並曾參與建立「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等組織。抗戰期間移居香港,於一九四○年年初在香港因病辭世,享年七十二歲。
長期以來,中國現代史研究領域將蔡元培歸於五四一代,而忽略他在民國以前的學術思想貢獻。其實,習慣上視為晚清思想重鎮的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比蔡元培還小一歲。戊戌變法前後叱風雲的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更是晚蔡元培五年才出生。這種忽略,毋寧說是出於那時政治形勢左右士人輿論的遺緒。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融貫中西,於一九一○年四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多次重印再版,對青年學子有長期潛移默化的作用。書中所據以品藻評價古人、梳理學術淵源的獨立眼光與立場,既屬當時首開風氣之舉,也是蔡元培此後擔任民國教育總長、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學術要職時,戮力變革之所據。這是中國現代知識轉型過程中的一本經典著作。五南決定再版此書,實為有益讀者、有益社會之善舉。
二、身世背景
蔡元培出生於清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十一日,西曆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其祖上係明末自諸暨移居山陰,後定居於紹興府城內筆飛巷。這裡錢莊當鋪密集,並設有紹興錢業公會。蔡氏子弟世代服務於商界,多為店鋪經理、副理,姻親也多居此處並從事相似行業,其中包括蔡元培的外祖和他第一次婚姻的岳家。蔡元培出生前,其家世正上升至小康。祖父購置並擴建住屋,買進陰宅祭田,元培的六叔且補廩生,成為蔡氏門下第一位考取功名者。元培四週歲(一八七二年,按農曆計為六歲)時入家塾開蒙,但祖父、父親不久先後過世,家道中落,元培和弟弟只得出外附讀,兩年換了三位塾師,之後才較長期地追隨紹興城內頗有口碑的設館秀才王懋脩先生,並於十五週歲(一八八三年,農曆十七歲)中秀才,得以自己授徒為業。兩年後,蔡元培經推薦為本縣鄉紳徐樹蘭之子陪讀並為之校對藏書,得以博覽群書並結交書友,學業突飛猛進。此後,一八八九年中舉,一八九○年中貢士,一八九二年中進士並點翰林院庶吉士,一八九四年二十六週歲(農曆二十八歲)時升任翰林院編修,科舉之途可謂一帆風順,與嚴復(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等人幾十年科舉不得意的經歷相當不同。
蔡元培無疑天資過人,但家世經歷也在很重要的方面決定了他的學術思想品格。即以儒家道德來說,仁義固然滲透於整個社會,但士人必須忠君,否則將治罪,而平民百姓則只需日常服從,蔡氏家庭的忠君意識因此相當薄弱。中下階層市民的蔡氏也很重孝道,蔡元培兄弟及其叔父都曾在母病時刲臂肉進藥,但他們行孝卻並不看重儒家視為根本的禮儀。相反,紹興久遠的商業傳統賦予他們較強的平等意識和人際關係中既互助又自強的精神。此外,蔡氏父兄沒有納妾歷史,也顯示出性別平等意識的浸染。不妨說,在宗教、國家、社會、個體等方面,康有為、梁啟超偏重於國家;譚嗣同、章太炎偏重於個人;王國維偏重於個體與超越;而蔡元培的思想進路,則常常偏重於社會與倫理。日後蔡元培參加革命,持一種反對帝制但不主張排滿的折衷立場,應該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缺少士人的家庭背景和社會交往也使蔡氏弟子保持了謙卑而開放的學習態度。紹興作為江南文化重鎮,清代主要學術思潮在這裡都有根基和影響。從入縣學到進士及第,蔡元培曾先後偏重於不同學理:性理天命的宋明理學,尋章摘句的漢學訓詁,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以及浙東獨特的史學方志傳統。但其主旨始終傾向於不分漢宋,兼容今古,略疏於經義,重在綜合。究其實,在並無家學淵源可仰賴,缺少耆碩大儒指教,同齡學友又無人與之同時中舉的情況下,蔡元培不凡的科舉業績,不可能循清儒津津樂道的家法門戶,而必須基於他思維上出眾的綜合平衡能力。我們或可於此了解他寫作《中國倫理學史》的動機。
三、時代思潮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轉折。這一年蔡元培點翰林編修,首次進入京師官場,就遇到這千年未有之變局,思想與閱歷均無準備。他舉人和進士時的同年梁啟超、汪康年、張元濟等人立時成為變法運動中的弄潮兒,而他本人則主要以讀書來回應,無任天文地理、聲光化電,亦或各國史、日本語,都勤勤懇懇學習。同鄉先輩徐樹蘭和同年胡道南參與創辦《農學報》、《經世報》,他也在京師幫助售賣散發。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期間,雖然關切時事,令他最為興奮的卻是嚴復的演講。變法的慘敗,迫使他將知識關懷轉化為道義立場,攜全家離京,返鄉任紹興中西學堂總理。一九○○年義和團庚子之變,滿清朝廷鼓譟在前,潛逃在後;八國聯軍攻入京師,南方重鎮都督卻保持中立。腐敗亂象更堅定了蔡元培與滿清決裂、追求平等和民權的信念。一九○二年任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他支持學生退學抵制堂規,並由此創辦愛國學社。舉凡一九○二至一九○六年間上海的激進教育界或革命黨活動,幾乎都有蔡元培參與領導。一九○六年秋,蔡元培返京申請出國深造,於京師大學堂譯文館代課半年後,自費隨駐德公使赴德國留學。
這十幾年裡,無論是政壇學界還是蔡元培本人的生活,似乎都忙亂得令人眼花繚亂。其中是否有內在理路?蔡元培又為甚麼要在各地立憲熱潮漸起、學部新立且教育改革提上日程之時堅持出國深造?
五四以後的梁啟超曾總結近代中國學習西洋,說是洋務時代船堅炮利,甲午之後政治革命,到五四才注重文化思想。這一說法十分流行,但其實並不準確。不錯,甲午戰爭之前確實是「中體西用」,中西學判分兩轍。抨擊時政者或以西人為例,但必以聖人之言為據,即使聲言要改創新制的康有為也不例外。但甲午戰後情況則有所不同,特別是嚴復翻譯赫胥黎《天演論》出版,大大衝擊文化思想界。以往論者多談及這部著作介紹達爾文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對中國影響巨大。其實,赫胥黎梳理古希臘學術史和印度佛教哲理的部分同樣帶來巨大震撼。學者受其影響而重新審視學術史和國粹者,多有人在。
即以梁啟超本人為例,戊戌後流亡日本辦《清議》、《新民》等報,一九○二年初〈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續以全年連載之長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格局頗似蔡元培八年後出版的《中國倫理學史》,而其中先秦部分陳述概貌和佛教部分贊其深邃,又隱約可見嚴復《天演論》痕跡。文中更反覆徵引章炳麟(太炎),而章太炎這年正在修改《訄書》,其中同樣論述了從先秦至近代的學術史,「觀省社會因其政俗」,「知古今進化之跡」。一九○三年《蘇報》案發,章太炎入獄,蔡元培赴青島暫避,並翻譯德國科培爾在日本演講之《哲學要領》。和當時其他活躍的思想家一樣,蔡元培投身革命活動的同時,也在持續探討中國傳統學術在西方思想激盪下的新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清廷正在各方壓力下被迫改良,這些激盪孳乳的新思潮,卻很難進入官方視野。西學對既有傳統的挑戰及其在士人中的影響,官方早有憂慮,但身處其位,不得不謀維持滿清統治之政,學術思想也因之受到束縛。高官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一八九八年發表其著名的《勸學篇》,強調忠君、尊聖、尊經為體,西學為用,經遂被架空為僵死教條,道也因之萎縮成由三綱五常等固定標準統領的個人修身問題。清學部於一九○五年十二月建立後,張之洞仍懼新思想如畏虎,如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於一九○六年初評論所說,學部新定大學章程的根本之誤在缺哲學一科。「必以哲學為有害之學」,「必以哲學為無用之學」,且「必以外國之哲學與中國古來之學術不相容也。」王國維閱讀叔本華、康德,也正是在一九○二—一九○四年間。他一九○三年作為入門閱讀的巴爾善(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9)的《哲學概論》,蔡元培在德國期間也曾研習,是為當時文化思想變遷深流之一支。
四、原著研讀
蔡元培近四十歲隻身自費赴德留學,為貼補家用,與上海商務印書館簽約,譯述著文。寫作《中國倫理學史》之前,已於一九○九年翻譯出版《倫理學原理》,原著者「泡爾生」與王國維所說《哲學概論》作者「巴爾善」實為同一人。蔡元培在德國時出版的這兩部書,都有日文底本,他在寫作序言或緒論時都有切實說明。這並不意味他無力閱讀德文原著,也不是說他的寫作無甚新意。一方面,雖然當時以西學眼光重新審視中國學術史的學者都注意到中國傳統給予倫理以極重要地位,但多半隨之轉向哲學、文學、政治、法學等領域。蔡元培在萊比錫選修課程也集中在哲學、心理學、文學和倫理學,可是在認識中國學術傳統時,他仍堅持其倫理學的認識進路。這兩部書都是他有意選擇的題目。另一方面,那時翻譯出版界競爭頗為激烈,尤其從日文翻譯的書目繁多。原始資料顯示,兩書完稿前,都曾有時間壓力。《中國倫理學史》所據兩本日文書及其他參考資料,即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從上海寄給蔡元培,乞其務必早日完成計畫中的寫作。
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與其所據之日本木村鷹太郎《東西洋倫理學史》東洋部分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強烈的學術史意識。蔡元培從本書序例就強調學術史之重要,又在緒論中反覆申說倫理學與修身書之區別,倫理學與倫理學史之區別。內容排列上,先秦部分將木村依時序羅列諸子改為以學派傳承梳理;全書更平衡先秦與後續時代,與木村將四分之三篇幅用於討論先秦截然有別。木村解釋其裁度時以佛教進入中國為災難,蔡元培則用心辨識從三教並存到儒教終為倫理學之正宗的軌跡。蔡元培書一出,木村之說不再於中國流傳,蔡著此後且譯為日文,亦可見其創制之價值。
事實上,蔡元培的學術史自覺,突出表現在其解釋主要歷史分期之間起承轉合的關係上。他在每一時期後做「結論」,評點此期內各主要學說及其互相關係乃至與此前此後各流變發展之關係,於一冊內貫通學術思想史之全貌概況,實為當時之罕有。
例如,此前已有學者論及先秦南北學風之異同,蔡氏承此說,認儒法起於北方偏於實際,老莊則為南人偏於理想,並將介於其間者依此分說,同時考量南北思潮歷史上之漸進調和。再如,楊朱者,其何人耶,其說為何耶,學者至今爭之不絕。蔡氏視其為「莊周」之同名異音,雖未必服人,但將今日歸於其名下之文字做為六朝間清談家代表,卻不失為一家之言,頗能展示時代特質與風氣,合於學術史之標的。不過最重要的,恐怕還是蔡氏正面討論並評價了朱熹。晚清學者,無論高官布衣,保皇革命,談經說道論儒講諸子都可以,對朱熹卻一概諱莫如深,視論朱學者為學識上等而下之。宋明大家,王安石、周敦頤、王守仁都有人分別討論,只有蔡元培此書以學貫中西之企圖,將朱熹置於學術史長河中,試圖予其以公允品評。
蔡氏《中國倫理學史》之另一大特點,是以西方現代觀點權衡中國歷代哲人,為久困於經學解說之學界開啟一新視角。他於學理上深受巴爾善新康德主義影響,但其根柢又為純中國學統,故並無西方學者觀察中國常有之膠著,而能發前人所未發。即使在結論漢唐宋明時多有負面評價,也因分別觀察各家時頗能體會若問題若立場之特定歷史,並無促迫讀者接受武斷評價之印象,而多有陳寅恪後來所提倡「同情的理解」之風,與「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啟超文體相比,較為傳統溫厚。
例如,第一期先秦創始時代總論伊始,蔡元培即比擬中國之《易》、《書》、《詩》三經於康德哲學之道德理想、知識、感情──善真美者是也。書末附錄於有清一代獨取戴震之分析心理情欲,並索解至善、黃遵憲之民先君後、俞正燮之男女平等,亦以西方現代學理出之。最後餘論從自然科學、論理學、政治宗教學問方面提出尖銳評斷,卻同時能肯定宋明清之大儒。蓋蔡氏此類評斷皆出於一種信心,認定學術之進步,有賴於與異國學說相比較。
草創襤褸之作,難免疏漏;哲學類著作,概念分殊尤難。蔡氏此書也會給今日讀者帶來一定困難。即如他討論先秦諸子時使用的「消極」、「積極」概念,需耐心體會方能了解前者懲戒後者發揚的不同含義。他所謂莊子乃立「純粹之動機論」,又謂宋儒所公認者為「極端之動機論」,二者應用似有概念上之偏差,前者偏於超越之彼界,而後者斤斤致意於此界之滅人欲。其中消息,尚有待就教於方家。
緒論
倫理學與修身書之別
修身書,示人以實行道德之規範者也。民族之道德,本於其特具之性質、固有之條教,而成為習慣。雖有時亦為新學殊俗所轉移,而非得主持風化者之承認,或多數人之信用,則不能驟入於修身書之中,此修身書之範圍也。倫理學則不然,以研究學理為的。各民族之特性及條教,皆為研究之資料,參伍而貫通之,以歸納於最高之觀念,乃復由是而演繹之,以為種種之科條。其於一時之利害,多數人之向背,皆不必顧。蓋倫理學者,知識之徑途;而修身書者,則行為之標準也。持修身書之見解以治倫理學,常足為學識進步之障礙。故不可不區別之。
倫理學史與倫理學根本觀念之別
倫理學以倫理之科條為綱,倫理學史以倫理學家之派別為敘。其體例之不同,不待言矣。而其根本觀念,亦有主觀、客觀之別。倫理學者,主觀也,所以發明一家之主義者也。各家學說,有與其主義不合者,或駁詰之,或棄置之。倫理學史者,客觀也。在抉發各家學說之要點,而推暨其源流,證明其迭相乘除之跡象。各家學說,與作者主義有違合之點,雖可參以評判,而不可以意取去,湮沒其真相。此則倫理學史根本觀念之異於倫理學者也。
我國之倫理學
我國以儒家為倫理學之大宗。而儒家,則一切精神界科學,悉以倫理為範圍。哲學、心理學,本與倫理有密切之關係。我國學者僅以是為倫理學之前提。其他曰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學範圍於倫理也;曰國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撻堅甲利兵,是軍學範圍於倫理也;攻擊異教,恆以無父無君為辭,是宗教學範圍於倫理也;評定詩古文辭,恆以載道述德眷懷君父為優點,是美學亦範圍於倫理也。我國倫理學之範圍,其廣如此,則倫理學宜若為我國唯一發達之學術矣。然以範圍太廣,而我國倫理學者之著述,多雜糅他科學說。其尤甚者為哲學及政治學。欲得一純粹倫理學之著作,殆不可得。此為述倫理學史者之第一畏途矣。
我國倫理學說之沿革
我國倫理學說,發軔於周季。其時儒墨道法,眾家並興。及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儒家言始為我國唯一之倫理學。魏晉以還,佛教輸入,哲學界頗受其影響,而不足以震撼倫理學。近二十年間,斯賓塞爾之進化功利論,盧梭之天賦人權論,尼采之主人道德論,輸入我國學界。青年社會,以新奇之嗜好歡迎之,頗若有新舊學說互相衝突之狀態。然此等學說,不特深研而發揮之者尚無其人,即斯、盧諸氏之著作,亦尚未有完全移譯者。所謂新舊衝突云云,僅為倫理界至小之變象,而於倫理學說無與也。
我國之倫理學史
我國既未有純粹之倫理學,因而無純粹之倫理學史。各史所載之《儒林傳》、《道學傳》,及孤行之《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皆哲學史,而非倫理學史也。日本木村鷹太郎氏,述東洋倫理學史(其全書名《東西洋倫理學史》,玆僅就其東洋一部分言之。)始以西洋學術史之規則,整理吾國倫理學說,創通大義,甚裨學子。而其間頗有依據偽書之失,其批評亦間失之武斷。其後又有久保得二氏,述東洋倫理史要,則考證較詳,評斷較慎。而其間尚有蹈木村氏之覆轍者。木材氏之言曰:「西洋倫理學史,西洋學者名著甚多,因而為之,其事不難;東洋倫理學史,則昔所未有。若博讀東洋學說而未諗西洋哲學科學之律貫,或僅治西洋倫理學而未通東方學派者,皆不足以勝創始之任。」諒哉言也。鄙人於東西倫理學,所涉均淺,而勉承玆乏,則以木村、久保二氏之作為本。而於所不安,則以記憶所及,參考所得,刪補而訂正之。正恐疏略謬誤,所在多有。幸讀者注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