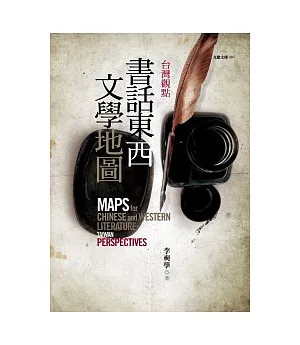打開書寫的記憶體
讀者眼前這本小書,乃拙作《台灣觀點:書話中國與世界小說》(九歌,二○○八年)的兄弟檔。我寫過的文學評論不少,書評更多,而且寫得早,早到九歌出版公司的蔡文甫先生還在主持《中華日報.副刊》的時代。但是我開始用電腦寫作的時間很晚,晚到我都已經寫而且譯了幾本書的一九九一年。那年以來,除了少數例外,各種拙文我總算電子檔在手,是「有檔可查」了。因此之故,一九九一年就常常變成我各種書寫記憶的開端,許多拙著都以這個時間為起點,讀者眼前這本小書自然也不例外。
《台灣觀點:書話中國與世界小說》談的是小說或一般性的虛構之作,本書處理的則絕大多數屬常言所謂「非小說」,其中又以傳記與各類評論書籍為大宗,我分之為「文學因緣」、「回顧前塵」與「雜議東西」三輯。人類的知識何其繁雜,分門別類乃大學問。宗品固有顯隱之異,性質重疊者也不乏見,亞里士多德因而有《範疇論》(Categories)之述,而中國詞章與文化的傳統中亦可見《文心雕龍》或各種「類書」的編纂。我的「非小說」指「非虛構」(non-fiction)書寫,但是不談同質性;論其內裡,即使「傳記」這種「非虛構」的「虛構性」還真強,往往假手修辭而隱藏在字裡行間。修辭可以弄拙成巧,也可以搬弄是非,顛倒真假,讓文學和真實人生串連為一。評論文字看似理性,對我來講,卻也難以完全置身於寫作者的視∕世界之外。所以修辭既不可免,當然會讓評論變成充滿主觀的個人實傳。當中之別,唯名目耳。修辭一旦可以除魅,「傳記」和「評論」則一,都是「虛構」,也都是「非虛構」。悼紅軒主說得好:「假作真時真亦假」,文字世界都在「無為有處有還無」!
果然如此,那麼眼前這本《台灣觀點:書話東西文學地圖》不也是假名他人,實則借屍還魂,是巧用名目與修辭在偽裝自己?是,也不是。「是」,是因為我的修辭就算騙得了人,也騙不了自己。「不是」,是因為我提筆為文,一向態度嚴肅,從來不敢以「遊戲筆墨」唐突他人的心血。一九九一年以前如此,一九九一年以後依然如是。書評者,飣餖也。但區區千百字就得道人長短,議論是非,並不比所評之書的倚馬萬言容易。評者既無研究時間上的優勢,講的當然是自己最直接的感想;縱有修辭,也已降到最低的程度。書評之所以重要,重要在原創性最強:一般來講,也最「誠實」。讀者眼前這本小書,不是在描畫一九九一年以來台灣以外舉世的文學圖貌,然而若視之為管見所知的文學價值的取向之一,我也不敢矯情否認。區區以為對熱愛或研究文學的人,或許尚有助益。
從短文到成書,過程複雜。我逐篇從頭爬梳不說,更受益於不少友生與知己。刊用拙文的金蓮、開平、偉貞、楊澤、義芝、素芬、恆煒、悔之與曼麗等諸兄姊,曾經賜正不少,扶我於敧斜。有幾篇蕪文承余國藩、齊邦媛、孫康宜諸教授及王德威兄鼓勵,併記於此。如玫代校本書,淑慧又刪冗汰繁,逐句修訂,不是我能感謝得了!我受知於蔡文甫先生甚早,數年來,他又不吝支持區區斗方微業,本書面世,他和九歌的素芳、敏菁出力尤多,我的感謝自是筆墨難罄。早在一九九一年之前,內人嘉彤就是我論人議事時的一面明鏡,偏頗處她會指出,而且非要我「改過自新」不可。沒有她把關,拙作不可能通得過眾報刊老編嚴格的「審查」。
李奭學二○○九年春.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