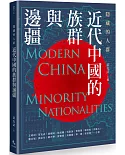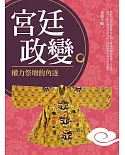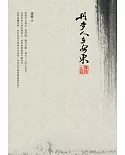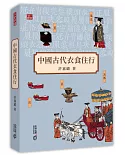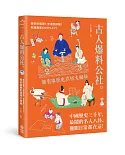總序
幾年前,史語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語所創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點事情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日子,幾經商議,我們決定編纂幾種書作為慶賀,其中之一便是《中國史新論》。
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思潮有重大的變化,史語所同仁在開展新課題、新領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我們覺得應該結合史學界的同道,做一點「集眾式」(傅斯年語)的工作,將這方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
我們以每一種專史為一本分冊的方式展開,然後在各個歷史時期中選擇比較重要的問題撰寫論文。當然對問題的選擇往往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且總是牽就執筆人的興趣,這是不能不先作說明的。
「集眾式」的工作並不容易做。隨著整個計畫的進行,我們面臨了許多困難:內容未必符合原初的構想、集稿屢有拖延,不過這多少是原先料想得到的。朱子曾說「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我們正抱著這樣的心情,期待這套叢書的完成。
最後,我要在此感謝各冊主編、參與撰稿的海內外學者,以及中研院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汎森 謹誌
2008年10月22日
史語所八十周年所慶日
導言
一
什麼是「基層社會」?對於這個問題,歷史學研究者向來都各有不同的觀察角度與解釋──有從人倫關係的親疏遠近闡述之,有從行政與社會關係來探討,亦有將社會群體區分出高低階層,以底層人物與其生活方式為基層,以著手討論者──由於觀察角度不同,所得之結論自然有別。本論文集對基層社會的探討,主要偏重於觀察行政體制中的基層組織,分別由八位主筆者撰文,探討中國自秦漢至清代,縣級以下的政治結構和發展運作型態,以及與各種社會群體間的互動關係。
不過,即便以行政體制中的基層組織為對象討論,學界對於基層社會的內涵,看法仍舊相當分歧──有基於行政組織性質之不同,主張基層社會的研究對象應有鄉村、村里或縣鎮之別,或分別以地域社會、地方社會與基層社會等不同名詞加以區隔。這些歧異多半源於現存史料詳略不同,如討論近代以降的基層社會,研究者多以村里為主要對象;明清時代的研究,則以鄉村、城鎮為重。相對來說,建構宋代之前的鄉、村、里之社會型態與整體面貌,更加受到史料局限的影響,而僅能藉助特定地區、時段較豐富的傳世文獻或出土資料,方能重建局部鄉里社會的形貌。
為避免史料限制影響討論,本論文集決定對基層社會的內涵,採取較為寬泛的定義,將觀察範圍設定在縣以下的各層行政組織。如此界定,是考慮到縣為中國歷代行政組織中,設官任職、執行政策、維護治安、司法裁判和財稅稽徵的基本單位,縣衙既是國家在地方社會行使統治力的中心,亦是民眾和官府交涉互動的場所,更是中央政治力與民間社會力接觸的介面,史料較為豐富,易於對傳統中國的基層社會,有更整體性的討論。此一做法,較之於學界素來對基層社會的定義,可能有所出入,但或許更有助於擴大對基層社會的觀察。
然而,基層社會研究相關研究議題涵蓋廣泛,除了行政組織與國家控制之外,也包括如地方性差異:宗族、非宗族、自然地理開發階段;住民認同與共同團體組織:村廟、廟會、共同信仰、祭祀、生活、生產;活動空間:聚落地理、居住空間,以及商業、生產、文教、祭祀、信仰等活動空間;以及基層社會自律性:共同體內部的懲戒、制裁與調解等多樣而龐雜的問題,實難在短時間、小篇幅的研究中全面地探討,這也是本論文集無法達成的任務。但是,這樣的困難也充分說明基層社會研究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值得關心中國傳統社會發展的研究者,共同投入這個亟待開展的新領域。
本論文集的題名雖經諸位主筆者多次討論而定,但各篇的題目、內容與研究取徑,則尊重主筆者個人興趣、專長,對史料的詮釋方式,也視各篇主筆而有不同。對讀者而言,此一安排構想乍看之下可能有內容聚焦不足、缺乏共同主軸之類的質疑。但實際上,本論文集仍集中於三項基層社會的主要課題:第一,是中國基層社會的鄉、村、里等組織發展之延續性。相關文章包括邢義田〈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型態和鄉里行政〉、侯旭東〈漢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論「?」「村」關係與「村」的通稱化〉、張國剛〈唐代鄉村基層組織及其演變〉。第二,是基層社會的行政結構,特別是透過對政治運作與官民關係的觀察,討論政治力與社會力的互動。包括黃寬重〈宋代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運作──以縣為主的考察〉、林麗月〈俎豆宮牆──鄉賢祠與明清的基層社會〉、劉錚雲〈鄉地保甲與州縣科派──清代的基層社會治理〉,以及巫仁恕〈官與民之間──清代的基層社會與國家控制〉。第三,是基層社會中的民間組織,即劉淑芬〈香火因緣──北朝的佛教結社〉。
上述三個主題共同關注的焦點,是基層的行政組織與社會群體多樣的互動關係。三項課題乍看之下分散獨立,實則打破了政治史、社會史之間既有的樊籬,體現出「縣級以下政治結構與社會群體的互動關係」的一貫主題。更具體地說,本論文集在某一程度上,通過基層行政組織與社會群體的實際運作與互動的討論,呈現出基層社會力並非全然與國家行政權力對立的歷史面向,復原中國基層社會史更加豐富多樣的面貌。
二
為了幫助讀者大體掌握各篇論文的主要內容,茲簡單介紹如下:
邢義田〈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一文,嘗試在目前學界對秦漢時期基層社會組織、制度、權力關係、經濟問題、庶民文化、聚落形態等問題的豐富研究成果上,藉由新近出土的考古遺跡、墓葬與簡牘資料,勾勒秦漢聚落應有的空間景貌,並探討秦漢帝國在縣級以下地方社會所進行之戶口、賦役等基層行政工作。
該文利用漢代官員墓葬中陪葬的行政地圖,說明當時聚落多依河流自然形成。這些聚落被納入「里」行政組織時,人數多寡不一,顯示人口數並非當時行政編組的唯一標準,而諸聚落被納入帝國基層行政體系與否,亦可能為地圖中里行政區劃合併、更動的可能因素。漢代農村聚落遺址的出土,則顯示傳世文獻中描述的「室居櫛比,門巷修直」,有一定代表性,但此類整齊修整的里,應較有可能出現在城邑之「里」、遷徙富民之「帝陵邑」,或邊塞屯墾區等處。
新
近出土的簡牘資料,也提供了秦漢時期鄉里戶口、賦役等行政事務具體運作的大致輪廓,不僅說明當時鄉里簿籍登記和呈報郡縣內容的多樣性,亦呈現了賦稅繳納計算方式,與里、戶、口之間的比例關係。各縣於每年八月派員,與各鄉嗇夫、各里里正共同執行「案比」、審定戶籍的工作,充分表現出秦漢政府控制力深入縣級以下基層行政組織的現象。不過,原有聚落之三老、父老即使在新里制取代舊有聚落之際,並未實際介入徭役、賦稅徵集等行政事務,但憑藉來自血緣、家族的既有權威,仍舊在新鄉里制度中佔有領導地位,並成為爭取地方利益的代表。
過去學界常將唐代地方基層行政制度中,以「村」代「里」的轉變,視為古代帝國崩潰、城市與村落對立,以及中國自上古邁向中世紀的劃時代標誌。侯旭東〈漢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論「?」「村」關係與「村」的通稱化〉一文,則著眼於歷史發展的延續性,並以自然聚落形態與鄉里行政體系的對應關係,作為討論框架。該文認為漢代聚落大致分為城居、散居兩類,前者較易符合鄉里行政體系,「里」即是聚落;散居聚落則較為複雜,既有居民所賦予的聚落名稱,又有官方鄉里編制的鄉、里名稱。當鄉里編制規範或區劃改變,或實際聚落人口移動、增長時,新生的自然聚落勢必與官方鄉里行政制度造成對應上的落差,亦提供新聚落名稱(如?、村、浦、洲、渚)的發展空間。
該文透過「?」與「村」音義由獨立到合流的發展、官方文書普遍使用「村」字指稱聚落的兩個觀察點,勾勒出「村」字如何成為城鎮之外散居聚落通稱的過程:「村」字雖然始自西晉已有泛指聚落之意,但此時「屯落」的稱呼似仍較「村落」更為通行;南朝劉宋時,官方文書已有「聚落+村」的表示法,民間亦有以「同村」顯示共居的認同關係;南朝齊雖仍有鄉里編制,但已出現「村司」、「村長」等職稱,用以指涉基層聚落管理人員,完成「村」字成為聚落通稱的過程。
作者延續上述自然聚落與行政聚落對應的框架脈絡,認為「村」字成為聚落通稱過程的基本因素,與南方聚落分散、居民遷移頻繁、傳統里制難以維持有關,但聚落形態本身並未出現實質的根本變化,因此「村」字成為聚落通稱的情況,或許未必如部分學者所強調的,具有社會結構、居住形態方面的變革意義。
相較於侯旭東以稱謂變化重新檢討唐代以「村」代「里」的說法,張國剛〈唐代鄉村基層組織及其演變〉一文,由處理唐代鄉制特色的諸多爭議及說法切入,試圖對唐代鄉村基層組織(鄉、里、村、鄰、保)的功能與運作,提出更全面的解釋。
該文指出,唐代鄉制「有鄉無長」,以五百戶之鄉為最基層的實體政務組織,承接縣政土地、戶口、賦役等鄉務的申報。鄉下設有五里,五位「里正」以鄉為操作平臺,共管鄉務,實際主持土地、戶口、賦役等工作。此外,另有以居住地域劃分的村坊,設有村(坊)正,下有鄰保組織,五家為一保,與里制、村坊制互相配合:由里正、村(坊)擔任鄰保的「主司」,共同維護治安;鄰保組織亦具有賦役連帶互保、分攤逃戶租稅的責任,以配合里正的賦役徵收工作。
里制與村坊相較,里正人選條件,比由「白丁」充的村正更為嚴謹;里名多是人為命名、整齊劃定,村名則是十分多樣;里正核心職責是「催驅賦役」,村(坊)正則為「督察奸非」、維護治安。更重要的是,里正是縣司的吏職,需輪流到縣衙當差,尤其在進行土地還授、編造戶籍等工作時,各鄉里正都必須至縣衙協助處理。然而,到了唐中後期,由於里正承擔了「鄉」級事務,百戶之「里」的事務反而被「村」取代,與基層相關的國家政令、公共活動規範,多以「村」為單位,處分對象亦以村正為主,而非里正。到五代,鄉、村遂成為縣司下屬基層組織。
在唐代,國家雖賦予基層行政單位徵收賦稅的責任,卻又剝奪了鄉村長正差派賦役的權力。為因應豪強之家拒絕當差應役所造成的困擾,官員只能親自掌握賦役板簿,並由民眾輪流應役。不過,唐代後期,政府控制能力下降,社會財富、民戶土地轉換加速,為了確保賦役徵收,遂發展出以豪富之家擔任村官、耆長的鄉村基層組織,鄉治責任又再度落在豪民身上。
到了宋代,在「鄉里虛級化」的趨勢下,「縣」成為國家控制基層社會最重要的的行政單位。黃寬重在〈宋代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運作——以縣為主的考察〉一文中,由縣政事務管理與權力運作等面向著手,觀察宋代鄉里虛級化趨勢之下,地方社會的官民關係變化,以及縣級組織重要性逐步提升的動態發展過程。
受限於官員輪調制度,宋代縣級官員多來自外地,必須借重當地胥吏、基層武力與縉紳豪右的社會資源與人脈,方能順利應付複雜的縣政事務。三者中,由當地人士出任的胥吏,由於瞭解地方生態,熟悉簿書法條,到南宋逐漸有世襲化傾向,是縣級政務運作不可或缺的角色。巡檢率領的土兵與縣尉率領的弓手,則是維護基層社會秩序的重要警備武力。弓手、土兵與自發性民間自衛團體,在北宋晚期宋廷無力維護地方秩序時,負擔起保衛鄉里的責任,使地方武力有了發展的空間。
當宋廷為因應龐大財政需求,將原供地方自行運用的稅收,收歸中央,導致地方財政惡化,建設經費不足,地方士人、富民遂自發性地鳩合人力、物力,承擔起硬體建設與文化傳承的責任。在此過程中,兼具天下觀與地方意識的士人,既憑藉個人聲望,跨越官民藩籬,取得地方意見領袖的地位,亦經由人際網絡的串聯,參與地方事務,履踐價值理念,成為基層社會中具影響力的優勢群體。
代表中央權威之親民官,與胥吏、基層武力、鄉里菁英豪強等地方勢力間,形成了緊密的權力互動關係,而縣政良窳往往取決其中,也正是在此一摶合的權力架構與局勢轉移下,地方官員、地方精英豪強、基層武力與胥吏,共同構成了宋代以降基層社會運作的基礎。
明清兩朝雖然沿續宋代基層社會的基本形態,但就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而言,仍有強弱消長的發展現象。林麗月〈俎豆宮牆——鄉賢祠與明清的基層社會〉一文,旨在考察明清鄉賢祠制度與其變遷、冒濫情況,並由地方祀典與鄉里官紳間之攀援與拒斥,探究明清儒學教化與基層社會互動的樣貌。
作者認為明代正德、嘉靖年間,州縣學宮內分立「鄉賢」與「名宦」二祠,形成地方廟學常制。鄉評與方志的記載,是士人亡故後能否入祀鄉賢祠的重要審核依據,而將鄉賢具體界定為「生於其地者」,排除「名宦」、「寓賢」,成為明清廟學「鄉賢祠」與宋元「先賢祠」最大的區隔。
新的定義使鄉賢祠祀與基層社會人際網絡,關係更為緊密,但營求入祀的風氣亦隨之冒濫。此現象既呈現出晚明由鄉宦、生員、鄉保與耆老所交織成的社會人際網絡,也反映出鄉紳勢要在其中的活躍,以及「士民公議」的影響力。相較於此,清代先賢入祀改由督撫學政具題推薦、禮部決定核可,官方甚至有撤祀權力的情況,顯見清初中央有意強化、增進對於基層社會的控制力度。
在清代如何強化控制基層社會的課題上,劉錚雲〈鄉地保甲與州縣科派──清代的基層社會治理〉一文,則進一步分析清代鄉地保甲的角色。該文指出受到各地風俗習慣與徭役工作的差異,清初保甲組織有由「甲總─甲長」之二級「總甲制」,朝向「保長─甲頭─牌頭」三級制發展的趨勢。不過,里甲、保甲、地方等徭役制度,看似條文明確、等級森然,實際執行時仍會因人制宜,新舊雜陳,里甲組織與保甲組織實無分別。
保甲制度的實際編排,相當有彈性,不限以村為單位。保長往往是一鄉之長,鄉約與地方亦可能身兼村長或莊頭;負責宣諭勸民的鄉約,則早在順治初年,便與保甲、地方一同承擔公務。因此,清人普遍認為鄉約與保甲互為表裡,即便州縣以下無正式行政組織,州縣官員、胥吏仍可利用點卯等機制,掌握基層社會秩序,鄉地保甲亦隱然成為州縣政府在地方上的代理人。
不過,雖然清廷一再推行均役改革,對基層社會的里甲、保甲、鄉約與地方而言,州縣科派仍是他們共同的難題。州縣官員在督糧與維繫地方治安之外,更利用里保、鄉約制度,剝削地方資源,非但州縣公務花耗遭轉嫁至地方里甲的現象,始終無法禁絕,擔任鄉約者也不時遭巡檢、書辦需索財物,喪失作為原本禮帽冠帶、宣講聖訓的尊嚴。有心謀取私利者也利用擔任鄉約、地保的機會,向民眾違法徵收門牌錢等規費,或在官司、辦賑等場合,謀取個人私利。在此情勢下,「忠實者」多半無法勝任鄉保一職,「狡黠者」卻能在奉承官員、應付土棍的夾縫中,榨取利益而生存。
巫仁恕〈官與民之間——清代的基層社會與國家控制〉一文除了整合前人研究成果之外,也嘗試釐清清代基層社會組織,將基層組織區分為由官方設立的里甲、保甲、鄉約等「基層控制組織」,以及民間自發形成的地緣或血緣組織「基層社會組織」,並討論兩者在基層社會中的互動與分合。
作者指出,康熙以來,清廷為禁革里甲正役負擔過重、里書上下其手等等徭役弊端,並提高戶口田糧調查的準確性,遂不斷改革基層控制組織,一方面推動役法革新,一方面將原負責催督賦稅的里甲組織,轉化為維護治安、清查戶口田糧的保甲組織。至乾隆朝後期為止,保甲長承擔催徵錢糧、差派雜役等地方公務,甚至與專司教化的鄉約產生聯繫,合稱「鄉保」或「鄉地」,在官員與村民之間扮演溝通協調的角色。城市地區亦有相應的坊甲組織,如客商有「舖戶冊」、乞丐有「丐頭循環冊」,將城市大量流動人口,納入保甲制中管理,成為清代保甲制度的一大特色。
為避免地方豪紳地主操縱里甲組織,清廷規定保甲長雖由地方人士推舉,仍須由州縣官員發給「執照」,形成由官方政治力直接控制鄉保基層組織,以鞏固從中央到地方的統一局面,有效減少官民勾結、鄉保濫權等弊端。由官方設置的基層控制組織,不僅利於國家統治,對維護百姓安全與社會秩序,亦有積極意義。
相對於基層控制組織,在宗族勢力強大的江南地區,也不時可見徵收賦稅、維護秩序的控制組織與宗族組織的合併,由基層社會組織執行原本屬於基層控制組織的功能。在宗族力量相對薄弱的華北地區,由村廟會社發展的「青苗會」等村莊自治組織,則逐漸承擔較重的差役攤派。當基層控制組織與社會組織結合運作之勢逐漸形成,清代鄉村社會遂發展出不同於現代地方自治的自律機制。在官民互利的情況下,民間社會組織接受官方基層控制組織的管轄,同時也提供協助,甚至逐步形成自律機制。這些現象都說明,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並非過去研究者所強調的二元對立。
在基層社會的民間組織方面,劉淑芬〈香火因緣──北朝的佛教結社〉一文,由北朝造像記的文本性質、迴向文中的佛教思想、信仰組織成員的共修性質切入,辨析、探討北朝佛教信仰組織,及其成員名稱與區域差異。
南北朝時期,佛教徒為表彰對教理的信奉,維繫組織成員之關係,乃在造像、供養等活動時,舉行以香爐供養佛之儀式,「香火因緣」一詞因而被賦予共同供佛侍僧,乃至因佛教行事而結識之意,其信仰組織亦有「香火主」、「登明主」之職事名稱。其中,北朝佛教信仰組織,多由僧俗共同組成,也有官民共同參與的現象,而共同造像行為的出現,或許與當時北方流傳的「獨行布施,其福甚少」之福田思想有關。反觀南朝無造像記或集體造像紀錄,乃受東晉以來禁碑令的影響,而未必如日本學者所認為,來自社會階層或修行方法差異。迴向文所出現之「為皇帝敬造」、「為國敬造」,則源於大乘佛教之報恩、普度眾生思想,是為「報國主恩」、「報國土恩」,與一般理解之皇帝崇拜與忠孝觀念不同。
作者認為,佛教傳入中國後,崇祀對象、方法與區域,雖與中國固有私社傳統有所差異,但就結社活動所使用之名詞觀之,仍不免受到其影響,而有如「邑老」、「邑正」之執事名稱、造像碑刻成員「邑子」畫像等。在其結社活動使用的詞彙中,「義」具佛教意涵,可作為社邑名稱,也可指其成員;而「邑義」在造像記文中,多指社邑成員,「義邑」則指佛教社邑。不同區域的結社活動與名詞,亦各具特色,如山東地區佛教社邑組織與成員,除了「義邑」、「邑義」之外,亦可統稱「法義」,且成員或因《像法決疑經》流行之故,多以兄弟姐妹互稱。關隴地區則受道教影響,出現「佛道混合造像碑」、少數僧人仍冠俗家姓氏、義邑成員有「邑生」、「邑子」別稱等現象。
三
基層社會研究是瞭解中國傳統歷史演變的重要基礎,也是社會史研究的重點,以往卻鮮為兩岸學界所重視,這一方面乃受限於史料不足,另方面則與外在環境的政治制約有關。
中國歷史資料極為豐富,但由於長期動亂,文獻、史料分散,蒐集、整理及出版均不易,早期除了政治史,特別是與王朝興亡或典章制度相關的史料外,多不易取得,研究難免受限;復以資料分散,更難以深入探究。其次,基層社會研究涉及人類學、民族學等社會科學領域,而兩岸長期受到外在環境政治氛圍的制約,學者為避免觸及政治敏感議題,鮮少涉及基層社會相關研究,遂使此領域發展較慢,方法、理論均有不足。中共建政後,基層社會研究在中國大陸又受到有計畫的壓抑,成果更為有限。對此,我在1992年撰寫〈海峽兩岸宋史研究動向〉一文時已有深刻體認,並提出應加強對基層社會研究的呼籲。然而,當時史料刊布既仍匱乏,政治框架亦難突破,以致學術研究仍十分不足;類似情況在宋史研究以外的領域,也同樣明顯。
近年來,兩岸學術研究風氣轉變甚劇,歷史學走過偏重典章制度與人物的政治史、強調量化統計與理論的社會經濟史、以個別人物為研究中心的學術思想史、著眼於庶民生活的文化史,乃至結合制度規範與運作過程的「新政治史」等學術風潮,逐步豐厚了觀察基層社會內涵的基礎;而今,更得力於大量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的刊布、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引入,以及日本學界對地域社會共同體的討論,相關研究不僅有了新的發展空間,也累積了相當的具體成績。在研究條件與外在環境成熟之後,研究者總算能走出往昔著眼中央政權、忽視地方社會的偏頗,開始發展基層社會此一深具研究意義的重要議題。
社會史研究在國際學界傳統悠久且成果豐碩,其中日本學界對基層社會的討論最為詳盡,涉及層面最為廣泛而深入。特別是日本學者在探討中國地方社會時,尤其是明清時期,多憑藉早年在中國的田野調查成果,又投射其日本自身經驗,結合了村落共同體、地域社會論、鄉紳論等觀念,對傳統中國進行觀察與闡述。日本學界將傳統中國基層社會的歷史發展與理論架構結合的討論方式,能幫助研究者敏銳地捕捉地方社會發展的斷裂與延續,以及中央與地方離合關係的不同樣貌,對研究長時段的中國基層社會演變,無疑極有助益。
不過,對生活在中華文化圈的史學研究者而言,源於自身受傳統文化的長期浸潤,與對所處環境的切身體會,在借重美、日學界理論觀點與研究成果之餘,關懷重心和研究焦點更著眼於對資料的掌握,以及對大歷史變化脈絡的理解。從而,華人研究者在看待中央與地方關係時,雖不忽略其對立面,卻更重視其協合面;在處理基層組織的歷史演變時,既留意其變遷斷裂,也看重其延續發展;在討論官民互動關係時,非但關注各方立場、地位的差異,與其中的社會控制問題,也注意到士人階層的出現,使基層社會的發展更具彈性,而非僅有社會力與國家政權對立的一面而已。因之,在兩岸研究者描繪的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發展中,更重視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離合相維,及彼此關係的互動。這樣的觀察是否切合歷史發展,並貼近真實的社會樣貌,還請學界同道多所指教。
黃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