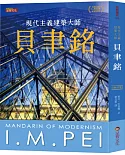序 「你知道為什麼寫詩嗎?」
與革命性建築的遭遇
選擇建築作為職業,是在讀高三的時候,但並不是因為對建築有什麼特別的瞭解,或是出於某種動機。我從小就很喜歡繪畫,因此對美術有些執著,但是從一開始父母就極力反對我以此為業;我當時正處在彷徨不定的少年時期,又掀起了對神學的熱情,甚至曾考慮過踏上聖職之路。但父母總是在強調我的長子身分,我又不能違背父母的意願,因此總是猶豫不定。
正當彷徨無助的時候,給我指出建築之路的人,是我的姐姐。或許當時她以為可以繼續將繪畫作為職業的就是建築;或許認為建築就是技術和藝術結合的產物。事實上,從我考取了大學的建築專業之後,因為擅長繪畫,經常被大家稱為有才華的建築系學生,而我自己也覺得比其他同學更有優越感。
大學還沒畢業,我就拜「空間事務所」的金壽根先生為師,沉溺於先生的建築當中。也許在我的人生中從未有過像當時那麼徹底與世隔絕,深深沉迷於建築的時期。連續幾天、幾星期、幾個月不分晝夜面對繪圖板,我不知不覺已經變成金壽根建築的狂熱信徒。那時的成績是馬山聖堂、京東教堂和國立青州博物館等建築。我相信這些作品在金壽根建築當中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關於自己對這些建築做出的極大貢獻備感驕傲,這種自滿或許說明我面臨著建築的某種局限。
由於當時國內黑暗的政治形勢,建築成了我唯一的希望,我所面對的建築的局限亦是我人生的界限,每日只有狂飲爛醉才是擺脫現實的唯一途徑。過了維新末期,新軍部的登場,致使社會狀況更讓人窒息,最終我只能以留學的名義逃避現實,在奧地利維也納開始我的新生活。那是1980年,我二十八歲。
維也納自由的氣氛使我整天無暇學習,只是沉浸在音樂和葡萄酒當中,好像要補償被壓抑的所有過去一樣,自在地生活著。就在那個時候,我和一位建築師相遇了,是通過學校老師送給我的一本叫《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的書。慚愧的是,我在韓國從未聽說過這位建築師,當然,也沒聽說過他的建築。
於是,令人驚訝的現實展開了。在書中,路斯與其說是建築師,不如稱之為革命家。他並非是我所學和熟知的建築師那樣,是沉溺於想像中優美的建築,並將其描繪出來、以匠人姿態出現的所謂藝術家,而是面對時代,不斷與惰性和慣習抗爭的、夢想新時代的實踐性知識分子。
為了瀏覽他的建築,我重新仔細地在維也納尋找他的作品,並不斷地歎息,懊悔之前的虛度光陰,埋怨自己這麼晚才遭遇到路斯。建築是技術和藝術的一部分,這一荒謬和無意義的假設,正在我腦中被徹底的擦掉。我開始反問:所謂擅長美術,豈不是妨礙做建築?
建築,造就我們的生活
我相信建築能夠改變我們的生活。我們常說的夫妻相,也是因為夫妻在同一空間內度過漫長的歲月,受到了這個空間的支配,因此逐漸改變彼此的習慣,最終連長相也變得相似的結果。修道者尋找小而簡樸的空間也是希望受到空間的控制。英國政治家邱吉爾曾在1960年會見《時代》週刊的記者時就說過這樣的話,“We shape our buildings; thereafter they shape
us.”意思是「我們雖然在營造建築,但建築也會重新塑造我們。」換句話說,好的建築將塑造好的生活,壞的建築只能塑造壞的生活。當然,好與壞不在於它的華麗或是儉樸。倒是華麗建築中的生活十之八九會失去生活的真實性而變得虛假,而簡樸的建築中容易滋生出正直而真實的心性。雖然建築的效果並不是直接的,我們對它的感受也是相對滯後的,但建築確實在改變我們的生活,並且對我們的人格產生絕對性的影響,所以建築對於我們實在是太重要了。那什麼樣的建築才是好建築?並且建築到底是什麼?
日本人所造的「建築」這個用詞並不能確切地用來說明建築,它只是強調了「蓋」與「砌」的物理運動,並不能說明支配我們生活的建築的奧妙之處。英文中的“architecture”比「建築」一詞略好:詞源“arch”表示第一或是大的意義;“tect”為希臘語,表示技術或學問之意。這個單詞直譯出來就是「元學」或是「大技術」。建築若不是如此博大而重要,怎能用這個詞來表達?甚至在基督教中表明天主的單詞,是在建築前面加上了一個定冠詞,即“The
Architect”,這在英文《聖經》裡是有記載的,可見建築這一職業的重要性。用這個詞來強調建築的重要性是再合適不過的,但這並不能說明建築的本質。
在我們的語言中曾經有比建築更好的詞,就是「營造」這個漢語辭彙。用我們的語言來解釋的話,它具有「做出」的意思。是的,房子不是蓋起來的,而是做出來,就像做飯、做農活兒、作詩一樣。什麼是做?就是利用材料通過想法、意願和心智來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與單純的物理運動的結果相比,其方法和過程是不同的,從根本上講是思想的不同。
如果不是物理行為的話,造房子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先推想在房間裡可發生的行為,決定收容其行為的空間,來預測使用人數,再決定大小,之後規定順序,重新組織起來就構成平面圖。在這平面裡生活的我們不管喜歡不喜歡,都要學習和適應其平面組織的規律。廁所作為解決生理現象的空間,以前被認為是不乾淨的地方,放在房子後面,叫「後間」,但現在的住宅平面上被放在中心位置,名字也變成「洗手間」。雖是同樣功能,利用平面圖上所處的空間,我們已含糊其名字,變得適應了。
這種平面圖不是看,準確地說叫「讀平面圖」,因為平面圖不光視為由線條形成的一個圖,而是要讀出其中建築師的想法,才能理解平面圖中的生活組織。建築師的圖,他的價值在於是否表現出他的思維。因擅長繪畫而做建築的話,繪畫只能妨礙他的思考過程,渾濁濃度。換句話說,將建築師思維的記錄,用普通語言來表示的,就是建築師的圖。因此,建築師應該擅長繪畫是沒有道理的,他只要把自己的想法就像寫文章一樣,用規定的符號和線條記錄下來就是了。某種意義上說,他所需要的是文化素質,並不是藝術技巧。就是創造生活的系統,即創造生活的方式,這才是我所指的建築。
將建築分為工學或是藝術的一部分,我認為是不對的,這只是誤解了建築所具有的某一小部分屬性。當然,技術是建築中重要的部分。事實上進入20世紀,在無限發展的技術時代,對於技術的表現也曾是建築的重要目標,而且我們的生活通過技術的發展得到了巨大的改變。技術常常以發展和進步為目標,問題是我們在技術發達的建築中是否更加幸福,這是個複雜的問題。
如果我們對比古埃及為工人設計的集合住宅和資訊時代可操縱所有設備的現代智慧型公寓的平面結構,就會驚訝於兩者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我從不懷疑如果能研究朝鮮時代儒生們所居住的房子的平面,就能做出使我們現時生活更加潤澤的現代住宅。這意味著技術的進步與我們生活的進步並不成正比。反而我們的生活經常發生退步,今天的技術進步帶來的家庭與社會的紛爭和矛盾等諸多病理現象就證明這一切。技術不同於建築,它只是將我們生活的系統變得更加便利和穩健的手段,是最基本的概念。
其實並不存在「建築藝術」這一說法。在奧地利維也納,一位畫家百水先生(Hundertwasser)曾設計了一棟公寓並成為議論的話題,建成十幾年後的今天依然引來很多觀光客人,但是它是否真的具有作為建築的意義?被稱作藝術作品的這個建築物可能從藝術角度來講是有意義的,但是從建築角度來看它卻是不值一提的。因為它沒有為集合住宅的居民提供任何特別的提案,住宅的內部結構也沒有表現出建築師本人對於生活的組織。它只是在與周邊住宅幾乎類似的形式上用各種混亂的色彩裝飾了外牆面,因此吸引了人們的視線。這些裝飾和色彩並沒能給住在其中的居民提供新的生活系統,裝飾牆面只是成為城市裡的宣傳畫,使暗淡的維也納街道變得華麗。這並不是建築。
建築的外形是包含內部生存系統的狀態,所以其外觀和外形最好直接反映內在的系統。在今天,建築作為環境的意義大於其作為單體的意義,它的外觀是次要的,是從屬於平面組織的附屬而已。但是至今還有不計其數的例子是將立面作為建築的目標,將建築作為象徵和符號,甚至錯誤地將建築作為一種造型藝術。在這類建築裡幾乎不可能產生美好的生活。
可笑的是由基於技術和藝術的各類錯誤觀點所組成的教育制度,在成功培養出正確的建築師這件事情上,從來都是以失敗告終的。現在也開始產生一些建築大學,但在兩三年前多數還是從屬於工科大學和藝術大學。在工科大學的專業裡放入建築或在藝術大學裡勉強塞入建築學,作為學徒或藝術家來提升其素質培養成正確的建築師,這只能是妄想。
如果一定要將建築放入其他學科,則人文學比較接近。因為人文學科的想像力和邏輯能力、對於歷史的洞察力,還有對事物的思考能力,這些正是必須在對鄰里生活的熱愛和尊敬中工作的建築師不可或缺的工具。
那麼究竟如何做好的建築?我對此有三個原則:
第一,關於目的性的問題。即建築能否充分表現預期的目的和功能,學校要像學校,教堂要像教堂,住宅要像住宅。模仿曾經用來作為墳墓的金字塔來當餐飲店,或是以民主議事為目標的議事堂成為封建時期的建築樣式,這些都是背叛了建築目的的結果。這些建築所要運營的功能被其他形式所偽裝,常常招致誤讀。換句話說,越可能是好的建築,就越應該正確表現出其所應具有的功能。只有這些建築在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後,其中的生活本身才會具有考古學上的意義。
第二,與時代有關。建築是重要的記憶裝置,常被稱作時代的鏡子。我們經常通過建築來得知建造它的時代的社會風俗與文化。考古學者發現古建築遺址歡呼的原因,也是因為獲得了可以正確復原當時社會狀況的機會。即作為時代的文化產物的建築,應採用其所處時代最合適的建造方法、材料與樣式。我們生活在高速資訊時代,如果再來建茅草屋或是土瓦房,只能是作為對古代建築的學習或是作為展示對象,這些只能算是對先祖們創作的複製。19世紀末,處在世紀末的歐洲建築與藝術知識分子展開了一場分離派(Sezession)運動,旨在挽救所謂充滿危機的時代。不僅有奧圖.華格納(Otto
Wagner)等建築師,還有克林姆(Gustav Klimt)、馬勒(Gustav Mahler)等主導時代文化的知識分子,他們預感到新時代的來臨,紛紛與舊時代訣別,開展新藝術運動。他們在維也納建造一個用於展示他們作品的展館來將他們的理念付諸實踐。奧布里希(Joseph Maria Olbrich)設計的這個分離派館的入口刻著如下的一段文字:“Der Zeit Ihre
Kunst,Der Kunst Ihre Freiheit.”(「給每個時代以它的藝術,給每種藝術以它的自由。」)
第三,建築和場所的關係。建築必須以根基於場地為前提,這一點是建築與其他造型藝術區分的重要因素。比如雕塑和繪畫是在工作室製作後移到展廳或其他空間設置,也可在各處輾轉。當然有時雕塑與地面的關係也很重要,但是此時的雕塑與其說是雕塑,更多的是作為建築身分而出現。建築總是與現實的場地密不可分,這個事實是確定建築的最重要的核心。這個現實的場地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與其他場地相連並有著特殊的關係,因此每塊基地都有其固有的特性。並且,這些基地因長期固守此處,記錄著久遠的歷史痕跡。這種空間性、時間性成為一塊基地的特殊條件,這種具有地理性、歷史性文脈的地段叫做「場所」。準確反映場所性的建築是正確的建築,這是理所當然的,這類建築的集合將創造一個地域的傳統文化。所以美國和韓國的房子應該不同,首爾和釜山的房子也應有不同形式。
從某種角度考慮,建築不僅僅是蓋房子,房子只是基礎,房子裡蘊涵的我們的生活與房子一起構成建築,也就是說,造就我們的生活就是建築最明確的含義。
這種好建築的目標是什麼?當然就是對我們人生價值的確認。不容置疑,每天都能讓我們發現自己的善良、真實和美麗的建築,就是好建築。《聖經》的「箴言」裡有這樣一段話:「房屋因智慧而建,因聰明立穩,其中因知識充滿各樣美好寶貴的財物。」 建築是我們在生活中通過智慧建造起來的,單單用手是絕對不能建起來的。
這時代我們的建築
阿道夫.路斯顛覆了我對建築的認識。我覺悟到變得熟悉的維也納生活的鬆散,開始急於準備回國。對於在韓國的建築工作,我想重新修正。但是回國後的條件並不樂觀。金壽根老師的罹病和去世,還有那期間只能接受的現實問題,使我將建築推在背後,我在那七年的時間只能遠離阿道夫.路斯。
1989年的冬天,我終於獨立出來。對於阿道夫.路斯的革命的記憶還是不允許我對自己的建築躊躇不前。
到了該做「承孝相建築」的時候了。當時成立的「4.3集團」的成員都是我的老師。大夥夜夜展開激烈的討論,確定了具體的學習方向後出發的建築旅行,對我來說是極大的刺激,以此為基礎,我開始航向建築的海洋。1992年,由十四人組成的「4.3集團」通過建築展覽,向著冰凍了的韓國建築界?喊,表明了具有新價值的時代建築的想法。
在當時以「這時代我們的建築」為主題的展覽中,好友金光賢教授在專刊的序言裡寫了這樣的忠告:「從閨房的建築中解脫。」但是他所指的閨房是西歐建築的形式,而我被監禁的閨房卻是金壽根老師。像後來在「4.3集團」其他刊物中所提到的那樣,我必須成為只能以夜空的星星作為唯一座標而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船員。
為此,重新翻檢對不朽的建築師們的航海記錄,是個有效的方法。在新時代,用新建築實現新生活的他們的建築對我來說是珍貴的教導,也是安慰孤獨航行的同行的記錄。他們是只依靠夜空的星星,向著自己追求的宇宙法則與洶湧澎湃的波濤進行鬥爭的革命家。是什麼讓他們永遠保持年輕的面貌?他們有著共同的原則。
你知道為什麼做建築嗎?
波蘭女導演阿茲尼卡.賀蘭德(Agnieszka Holland)1995年拍攝的電影《全蝕狂愛》(Total Eclipse),講的是法國的兩位天才詩人魏倫(Paul Verlaine)和韓波(Arthur Rimbaud)的故事。眾所周知,魏倫是19世紀末象徵主義詩壇的代表人物,三十七歲病逝的韓波則被稱為「現代詩之父」。
相差十歲的這兩人處於三角關係,又是互相欣賞的同性戀者,但是在詩的世界裡卻是互不相讓的對手。由李奧納多.迪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扮演的年輕的韓波是具有攻擊性、破壞性,無法壓抑熱情的人物,不停地陷害當時在巴黎詩壇已有地位的魏倫,以至最終中彈。
沉浸於電影中這兩位詩人的對話的我,聽到一句韓波在與魏倫舌戰時脫口而出的話,不禁感到如同直面刀刃似的不寒而慄。我記得當時韓波是這樣說的:
「你是知道怎樣寫詩,但我知道為何寫詩。」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是面對象徵主義詩壇巨匠魏倫,告訴他丟失本質而只依靠戲弄語言的方法來寫的詩是空殼,只有對本質徹底性的質疑,徹底地否定自己,能夠創造出新精神的態度,才是這個時代所需的真正詩篇。
聽到這句話的瞬間,我在想我自己。我是否在對建築提出根本的疑問?是不是只依靠惰性在畫建築?對我來說,建築是什麼?我對自己的拷問難以終止。就好像韓波的質問不是對魏倫,而是針對我。
建築設計是不斷與不同的事物相遇的工作。每次做新的設計,都能遇到不同的基地和人。新蓋的房子就應該是新的,但我們的城市有很多房子是用舊的精神蓋起來的。為了那些用盡自己所有的財產,夢想嶄新又幸福生活的人們,假如建築師沒有更新鮮更幸福的夢想,那些房子就是死的房子,也將背叛他們。話雖如此,就因建築是非常艱辛的工作,當偶爾自己也原諒自己的懶惰和膽怯的時候,韓波總是向著我質問:「你知道為什麼做建築嗎?」
恰好這些疑問就是上個時代不朽的建築師們共同的話題,也就是這種力量形成了革命性建築,改變了我們的人生,開創了新的時代。他們不應只是存在於歷史中的記錄,更應成為今天有效的教科書。特別是對被拋棄在夜色茫茫的海洋中的我,更是不可替代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