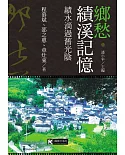總序
馳感入幻的世紀末書寫∕柯慶明
當所瞻望的父親,並不是買了橘子在月台間爬上爬下的,「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卻是:
那具血肉是我所熟悉的。雖然他手上的刀斧是我感官範疇以外的事物;他操斧往背部砍去的動作,更是我思維系統難以接收的景象。刀斧和血肉碰撞,鮮紅的液體從黝黑的脊背上滑落。
因而正如「火一旦碰觸鞭炮的軀體,貯藏在內裡的巨大聲響就會衝出,敲打人們的耳膜與心神」,「刀斧一旦和血肉碰觸,撼人的景象」,就不免使瞻顧者的「鼻梁上的眼鏡變得沉重起來」。
當騎乘的並不是自轉車,逍遙於風光明媚的康橋,「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著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卻是:
跨上摩托車,向東疾馳。我緊緊握住兩邊的把手,左手反覆前轉,催動油門:火熱的汽油在機械狼的內部流轉、燃燒、消磨,終於鼓盪而為強悍的速度,衝向去路。天空如飛毯掠過頭頂,青翠的檳榔樹、茶圃與蔗園、金黃纍纍的橘柚,都拔足奔跑過去過去了。鳥,倉皇地飛,風,倉皇地吹。大地流轉不息。我懷疑也有一種汽油在發動這一切,啊也有,一股汽油在發動我的身體,濃稠熱烈,飽含莫名的情緒和思維,由心臟傳向雙臂,由掌心輸入電路、油門,毅然發動引擎,催動車輪。
於是我們就不只看到了南台灣的殊異景光,而且進一步見到了「人機一體」的現代神話:
緊緊抱著機械狼,靜靜體會天地的流動。左轉,加速,超車。當右手催動油門,意志早已滲入機械,血管漸漸與油管接通。車與人融為一體,同時產生一種劇烈的亢奮,疾馳向前向前。速度越快,胯部與坐墊貼得越緊密,身體開始一吋吋淪陷。血由心臟注入油缸,火熱的油也灌滿急速膨脹的血管。我感覺得到狼的飢餓,牠不斷地以舌代足,舔食熱騰騰的道路。
這兩種境況交織在一起,似乎形成的不僅是唐捐個人的,甚至是九○年代台灣的「後現代」與「世紀末」景象:(唐捐的屢屢得到各種文學創作獎,是不是不僅由於他的才華;或者也因為他的種種描繪,反映了時代的特殊感性與趣味?)本土的景觀,鄉野的信仰,感官的沉溺,消費的熱潮,擁擠的群眾,快捷的運輸,環境的破壞,媒體的污染,地獄的想像......。
散文的文體形態,總是或多或少的帶點自傳的色彩,因此在本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唐捐的種種個人經歷:被水庫淹沒的童年與舊居,溪埔平原的故鄉,與父兄家人一起割筍砍柴,斬藤採石,獵鼠養螺,以至販煮山產等種種的生活經驗,以及前往東部擔任教員時的孤寂的感思。但是最重要的似乎是父親的死亡與追思。雖然,直到一九九九年五月,本書中書寫的最後一篇〈有人被家門吐出〉,唐捐方才正面的寫作這一題旨,但其實自一九九二年十月最早書寫的〈大規模的沉默〉起,他已默立在墓碑前,等待父親的咳嗽聲,破他的沉默了,以後幾乎篇篇有父親的影像。父親的去世,不但使得唐捐體驗到了「死生亦大矣」的鉅變與深痛;而父子之間愛惡糾結,既想從父親的生活世界「脫身」,又難忘懷其中種種的悲歡;而且通過了「神明附身」的特殊的民俗信仰,就進一步的轉化更為難解的人神糾葛,以至萬物有靈的因果報應等等,近乎夢魘的奇詭想像──但所有的「記敘兼抒情」,其實是無法自父親的亡逝裡平復,於是:「天空」,「像墓室一樣牢牢地籠罩下來」,「母性的大地是日夜張開的子宮」;「棺中生子」,竟然就成為宇宙萬物的本質與宿命的象徵了。尤其在成長的過程中有過「剋父」的意念與「瀆神」的經驗:當初次的性醒覺,在「神明」前發生;卻在父親死後,找到年輕父親和陌生女子的裸照,似乎使得整個靈異想像,更都沾染上了泛性慾化的色彩:少年裸遊孕魚;螢與鬼火交配......。於是自傳的事跡就轉化為種種怪異通靈的想像,讓我們不知要相信好,還是不相信好。
這裡我們當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搜神」、「誌異」等筆記小說的傳承。唐捐原來選擇了〈魚語搜異誌〉的篇名,作為涵蓋全書的書名,顯然不僅是該篇獲得聯合報文學獎,事實也多少標誌了全書的某種精神。這種精神一方面也反映了此類「論說兼記敘兼抒情」的特殊寫作,既超越了五四初期所建立的文體功能區隔的規範,一方面也為「後現代」的散文寫作,標誌了精神上的系譜。中古文人,首度對「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呼喚出:「豈不痛哉!」,卻也作為補償似的,以說神道鬼來構設了種種靈異的,後世統稱為「志怪」的想像世界,那正是小說要自散文中萌芽,卻又尚未完全脫離的階段。五四時代,不管徐志摩與朱自清之間,有多少風格的差異,他們仍然都分享了那股啟蒙的樂觀積極,劃分清明的精神。但首先鉤沉這些古小說,撰寫了《中國小說史略》的魯迅,卻在《野草》中,回歸到小說散文甚至詩境不分的寫作,影子,墓碣,死屍,魔鬼成為主角或訴說者;而學過人體解剖的經驗,亦顯現在設想裸體擁抱或殺戮之「大歡喜」所構成的〈復讎〉的僵局中:身體成了描寫與體驗的中心。這些風格特質,似乎或多或少為唐捐所承襲,雖然唐捐的身體描寫,主要來自各種費力的勞動與活動經驗,對於喧囂與擁擠環境的不耐,耽溺在黑暗,沉默以及形神分離的觀想中,以至於「馳感入幻」(假如我們可以仿照方東美先生以「馳情入幻」來形容現代的浮士德精神的先例,另撰新詞)。繁複的比喻,奇詭的設想,逆反的思維,以至少年Q的反覆出現,都讓我們看到唐捐的「後現代」風格,如何與《野草》的「現代主義」風格的承轉關連。
對於這樣的作品,我一方面讚歎唐捐的才華之高,感受之深;設想之奇,描摹之詭;一方面卻不免想提醒他:或許在思考告子的「食,色:性也」之餘,也可以考慮孟子的知言養氣,體會一下「浩然之氣」的宇宙境界;或許在沉思「萬物相制迭相食」的事實之際,亦當注意其中「物類平等」的襟懷,不妨於「不敖倪於萬物」之餘,「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在觀想因果循環的無休無止之時,亦當「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照見五蘊皆空」,以「度一切苦厄」,而能「心無罣礙」,「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世紀末的更進一步,就是世紀之初,是為序。
柯慶明謹序於台大中文系221研究室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日